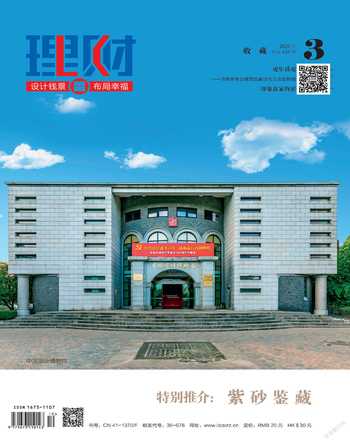癡壺雅流:奧蘭田的紫砂情結(jié)
郭占華
奧玄寶(1836—1897),原名奧三郎兵衛(wèi),字素養(yǎng),號(hào)蘭田、獨(dú)飛,日本明治時(shí)期的著名實(shí)業(yè)家,經(jīng)營和轉(zhuǎn)運(yùn)大米、干魚、油類商品,是東京商法會(huì)所創(chuàng)始人之一,后任東京商業(yè)會(huì)議所副會(huì)長,為當(dāng)時(shí)日本十分活躍的商界名人。他與日本文化界交往甚多,身邊聚集了很多當(dāng)時(shí)著名的漢學(xué)家、收藏家、古董商、畫家等,如女畫家野口小蘋,收藏家千原花溪,靜嘉堂第一代文庫長、東京帝國大學(xué)教授重野成齋等。奧玄寶本人酷愛收藏,61歲時(shí)于歐美視察旅行中因病猝死,他的藏品遂轉(zhuǎn)移給了巖崎彌之助。
奧玄寶熱愛中國文化,精通漢學(xué)。他不僅喜愛雅玩、書畫,更喜歡收藏中國的飲茶茗器,尤以紫砂壺為最愛,且撰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紫砂壺的著作《茗壺圖錄》。《茗壺圖錄》成書于明治甲戌年(1874年),是第一部圖文并茂的紫砂茗壺專著。此書自序中把嗜好、情趣、心結(jié),坦然地歸附為人之本性。內(nèi)文部分包括凡例、源流、式樣、形狀、流鋬、泥色、品匯、大小、理趣、款識(shí)、真贗、無款、銜捏、別種、用意、注春師傳,并對(duì)書中32把壺的身份資料做了詳盡的刻畫。從中,我們可以透析一個(gè)癡愛茗壺且成癖者對(duì)紫砂壺傾注的情感和認(rèn)知觀點(diǎn),感受精神與物質(zhì)的依存關(guān)系,以及對(duì)紫砂壺藏玩之士不同境界、不同層面的深度理解。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jìn)愈難,而其見愈奇。”奧玄寶對(duì)紫砂茗壺的觀點(diǎn)和認(rèn)識(shí),也許正是取決于其傾愛紫砂壺的深度。
奧玄寶在其著作《茗壺圖錄》自序中這樣寫道:“人非圣,熟能無癖?王濟(jì)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元?jiǎng)P有《左傳》癖。老杜云:‘從來性癖耽佳句。白樂天云:‘人皆有一癖。則人之不能無癖也,舊矣!蓋癖者,嗜好之病,而發(fā)于性情之不得已耳!故靈均(屈原)之于蘭,淵明之于菊,茂叔(周敦頤)之于蓮,和靖之于梅,太白(李白)鴻漸(陸羽)之于酒與茶,同不免為癖也。然而天下后世,因其癖而足以知其人,則癖者亦未必可棄也。”開篇即說明,人各有所好,愛好之極就成了癖,且視所癖之物如同揮之不去的第二生命,伴隨生活的左右,以至于后人往往因癖好而知道其人。奧玄寶本人所癖好的是中國的紫砂壺,他在《茗壺圖錄》中寫道:“予于茗壺嗜好成癖焉。”只要是茗壺,“不論狀之大小,不問流之曲直,不計(jì)制之古今,不說泥之精粗、款之有無,茍有適于意者,輒購焉﹑藏焉,把玩不置。”又怕這些壺玩時(shí)間長了,“毀滅難保”,于是作圖記之“以垂于后而未果”。并以文字將自己和諸友藏的32把茗壺作詳細(xì)描摹記載,這就是《茗壺圖錄》的由來。由于《茗壺圖錄》寫于注春居,因此書中32把茗壺亦稱“注春三十二式”,其中16件是奧玄寶本人收藏的,其余16件分別藏于各家。奇怪的是他寫此書時(shí)正養(yǎng)病于注春居,待書寫完“頓忘病之在體也”,病體竟突然痊愈了。可見,其嗜壺之好是如此之透骨。

《茗壺圖錄》自“凡例”入正文,以九個(gè)標(biāo)題來詮釋該書的典故、格式、詞匯、度量的表達(dá)、形式和存在問題的因由。其開篇提到該書是以中國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和吳騫的《陽羨茗陶錄》為“粉本”。自明代以來,不斷有人記述紫砂壺藝的歷史,并闡釋和挖掘紫砂壺的文化內(nèi)涵。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dòng)了紫砂文化的發(fā)展和傳承。書中“源流”依據(jù)《陽羨茗壺系》中記述的一些制壺名人和大家。“式樣”概括了不同壺的形式,乃“皆變體也”以合意者擇之。對(duì)于壺的“形狀”、紫砂壺的欣賞,可謂經(jīng)典獨(dú)到。他形容不同造型、風(fēng)格的茗壺:“溫潤如君子者有之,豪邁如丈夫者有之,風(fēng)流如詞客、麗嫻如佳人、葆光如隱士、瀟灑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樸訥如仁人、飄逸如仙子、廉潔如高士、脫塵如訥子者有之……”而且難說孰優(yōu)孰劣,因?yàn)楦魅诵蕾p角度不一樣,只有對(duì)茗壺“深愛篤好”的人“然后始可與言斯趣也已”。他認(rèn)為“流(嘴)鋬(把)”的曲、直、長、短、粗、細(xì)、彎、聳、俯的表現(xiàn),形異性同,前人自有用意和度數(shù),不必牽強(qiáng),符合賞玩者自身的要求即可。壺之“泥色”,“每壺各異,譬猶天文之燦然”妙不可言。
在“品匯”中,奧玄寶提到:“茗注不獨(dú)紫砂,古用金、銀、錫、瓷,近時(shí)又或用玉,然皆不及于砂壺。蓋玉與金銀雖可貴,雅韻不足;如錫則不侈不麗。”談到品茗用杯,奧玄寶引用《陽羨茗壺系》曰“品茶用甌,白瓷為良”。對(duì)茗壺的“大小”奧玄寶也有不同的看法,通俗的說法是“賤大如奴隸,愛小似妻妾”,但他并不附庸這些時(shí)尚看法,他的見解是通過“理”和“趣”的辯證看法來體現(xiàn)的。他指出,茶壺本是玩具,“玩具之可愛在趣不在理”,茶壺的大小,壺嘴的直曲并不是固定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遵循“理”(即壺的實(shí)用性)、“趣”(即壺的藝術(shù)性),兩者不可偏廢,他提到“知理而不知趣者為下乘,知理知趣是為上乘”。顯然他認(rèn)為實(shí)用和藝術(shù)的結(jié)合才是“上乘”。對(duì)于真假的分辨,他認(rèn)為不可不辨,但關(guān)鍵要有鑒賞力,“具眼者能辨之,若伯樂之于馬,卞和之于璞是也”。要“善用意”即用心觀察來掌握分辨能力。對(duì)“有款和無款”雖也有“壺或有無款而優(yōu)于有款者”“無款者,無他慮,有款之真?zhèn)坞y辨也”,但“無款而良者總不及有款而良者”。他打比方說“聘美人而不知其姓名,雖姿色可見,而不知何等人種,何等血脈”總不放心吧!對(duì)于壺的使用,奧玄寶在“用意”中講道:“壺質(zhì)成于泥砂,動(dòng)輒有札差之患,大異于鼎彝之堅(jiān)牢耐久。”意思是,壺質(zhì)脆弱,不如鼎彝之堅(jiān)固,稍不小心就會(huì)毀壞它,故好壺的人“不可不鄭重愛護(hù)也”。
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奧玄寶愛壺如人,在他眼中,每一把壺都是一個(gè)鮮活的生命,因而他用擬人的方法給《茗壺圖錄》中的32把壺都取了喻人的稱號(hào),并稱之為“注春三十二先生且附姓、名、字、號(hào)”(如:姓,壺;名,壽;字,昌齡;號(hào),梁園遺老……)。其32把茶壺分別是“梁園遺老、蕭山市隱、鶴氅神人、漁童、樵青、獨(dú)樂園丁、臥龍先生、出離頭陀、傾心佳侶、趺坐逃禪、藏六居士、凌波仙子、方山逸士、陶家佳友、儷蘭女史、帝鄉(xiāng)仙馭、儒雅宗伯、鐵石丈夫、銀臺(tái)醉客、繡衣御史、一枝棲隱、老樗散人、浴后妃子、臥輪禪師、紅顏少年、采薇山樵、連城封侯、壽陽公主、用拙迂生、風(fēng)流宰相、逍遙公子、斷腸少婦”。這一連串的擬人稱謂是中國文學(xué)作品中常用來形容人物風(fēng)格的,也許奧玄寶正是從各種不同形狀的茗壺中找到了一個(gè)個(gè)鮮活的生命,姑且不論其命名是否恰當(dāng)并為世人所接受,但至少奧玄寶本人是頗費(fèi)心思的。
《茗壺圖錄》中對(duì)于每把壺都有詳盡記錄,每把壺都列出泥色、收藏者、印款,并準(zhǔn)確地寫出通高、腹徑、壺深、重量、容積及流、腹、底、蓋等,可謂“描摹詳細(xì),尺寸精準(zhǔn)”。以“梁園遺老”壺為例,書中講道:“通蓋高二寸五厘,口徑一寸五分七厘,腹徑二寸八分二厘,深一寸六分。重四十二錢弱,容一合強(qiáng),流直而仰,鋬環(huán)而纖,腹圓而豐。底著(《博古圖錄》有著尊,謂底著地?zé)o足,壺又類之者,曰底著,下從之)。而凹。口內(nèi)設(shè)堰圈,蓋之如合符。紐呈乳形。流下鐫行書三字,曰“陳和之”,字法晉唐之遺風(fēng)。泥色濃紫或曰豬肝色。試以指搖蓋,鏗作金石之聲,滌拭之久,自發(fā)黯然之光,非所謂和尚之光可比也。通體氣格高古,韻致清絕,令予心醉忘餐,可稱茶寮之珍玩也。”書中還記述壺的作者陳和之是天啟、崇禎間人,距奧玄寶著此書時(shí)已達(dá)250年之久,明朝已故,但“茲壺壽于今,可不貴重耶!?故號(hào)曰‘梨園遺老。儲(chǔ)光羲詩曰:‘楚山有高士,梁園有遺老”。可見作者對(duì)其癖物情結(jié)表述之真切,癖物理趣見解之獨(dú)到,癖物優(yōu)劣觀點(diǎn)之明晰,癖物范樣記錄之精細(xì)……
奧玄寶,這位日本收藏家對(duì)中國的歷史文化了解得相當(dāng)透徹,在其作品《茗壺圖錄》中處處引經(jīng)據(jù)典,事事旁征博引,足見其知識(shí)之淵博,學(xué)問之深厚,以至于將人生精深的文化內(nèi)涵滲透到每一把紫砂壺中。《禮記·樂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dòng),物使之然也。”從其文章的敘述里我們看到了人與物之間割舍不斷的紐帶關(guān)系,而紫砂壺獨(dú)具的實(shí)用功能和藝術(shù)魅力貫穿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zhì)生活。其形式是通過人們對(duì)其使用、意象、藝境的欣賞和感知來實(shí)現(xiàn)的,包括認(rèn)識(shí)、審美、娛樂、消遣、人文、道德、思想啟迪、平衡心理等多元功能。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奧玄寶浸淫于茗壺,不僅僅是閑時(shí)的賞玩和愉悅,更是釋放自己生活背后的精神情感,或借物喻事,或借物喻理,或借物喻人,從中尋求某種智慧的隱語和內(nèi)心深處的愜意。林語堂曾經(jīng)說過:“捧著一把茶壺,可以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質(zhì)的精髓。”奧玄寶從紫砂茗壺中,似乎發(fā)現(xiàn)了本真之上的“凈土”,找到了靈魂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