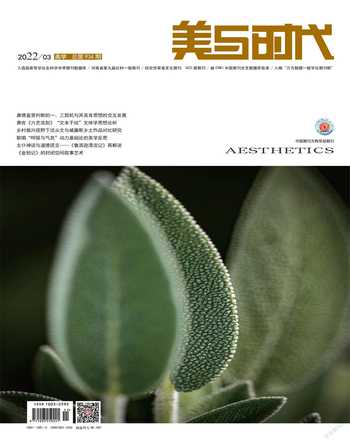論《文化苦旅》中的非虛構(gòu)特征
摘? 要:20世紀(jì)9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揭開(kāi)了當(dāng)代文化散文的序幕。當(dāng)幾十年后的今天非虛構(gòu)寫作浪潮在國(guó)內(nèi)興起之時(shí),回望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本書在創(chuàng)作方式、敘事角度以及主題思想等方面都顯示出了非虛構(gòu)的特征。他走出書齋,行走在中國(guó)的大地上,用在場(chǎng)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所見(jiàn)、所聞、所思、所感。通過(guò)從下到上的敘事視角來(lái)表達(dá)個(gè)人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走向失落的思考,同時(shí)在字里行間寄寓了他對(duì)文化保護(hù)、文化復(fù)興的深切憂思。
關(guān)鍵詞:余秋雨;文化苦旅;非虛構(gòu)特征
非虛構(gòu)寫作近年來(lái)日趨火熱,在諸多領(lǐng)域引起了研究者們的重視和討論。對(duì)于非虛構(gòu)寫作的興起,有研究者認(rèn)為,“非虛構(gòu)寫作并非始于今日。縱觀古今中外文學(xué)史,這一寫作模式早已存在。我國(guó)古代的史傳、游記、紀(jì)實(shí)、書信,現(xiàn)代的日記、口述史等,其實(shí)均可視為非虛構(gòu)寫作,只不過(guò)古人未使用這一概念”[1]20。這種將中國(guó)古代的一些文體視為非虛構(gòu)的界定主要是對(duì)廣義上的非虛構(gòu)而言。目前學(xué)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當(dāng)下所流行的非虛構(gòu)寫作主要是由20世紀(jì)60年代的美國(guó)所興起的一種文體演變而來(lái)。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處于一種新舊交替的激變時(shí)期,這種激變之下的社會(huì)氛圍催生出了一種以“非虛構(gòu)小說(shuō)”和“新新聞報(bào)道”為代表的非虛構(gòu)創(chuàng)作。其中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軍》、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等都被視為“非虛構(gòu)小說(shuō)”的代表作,這些作品采用“非虛構(gòu)小說(shuō)”的文體形式,將傳統(tǒng)小說(shuō)的虛構(gòu)和想象與新聞報(bào)道的寫實(shí)方法結(jié)合起來(lái),開(kāi)創(chuàng)了美國(guó)小說(shuō)新的寫作方式,這種獨(dú)特的寫作理念很快在西方國(guó)家掀起了非虛構(gòu)寫作的浪潮。非虛構(gòu)寫作真正開(kāi)始進(jìn)入國(guó)內(nèi)視野是在上世紀(jì)80年代,最開(kāi)始只有部分學(xué)者發(fā)表文章進(jìn)行討論,并未引起太大關(guān)注。直到2010年《人民文學(xué)》開(kāi)創(chuàng)了“非虛構(gòu)寫作”專欄,非虛構(gòu)寫作才開(kāi)始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一批作家開(kāi)始了非虛構(gòu)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經(jīng)過(guò)十年的發(fā)展,逐漸形成一股非虛構(gòu)寫作的潮流。目前學(xué)界對(duì)于“非虛構(gòu)寫作”的定義依舊處于討論之中,但是“非虛構(gòu)”所共同具有的一些特征已經(jīng)得到了廣泛的認(rèn)同。
首先就是強(qiáng)調(diào)它是作者“在場(chǎng)”的寫作。“它特別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踐或行動(dòng)寫作,即寫作者必須行動(dòng)起來(lái)……與其說(shuō)非虛構(gòu)寫作是一個(gè)文體概念,不如說(shuō)它是一種寫作立場(chǎng)和寫作態(tài)度,一種敘述方法和介入現(xiàn)實(shí)的路徑。”[1]這種“在場(chǎng)”不只是強(qiáng)調(diào)寫作者身體的在場(chǎng),更重要的是寫作者的寫作立場(chǎng)和寫作態(tài)度。非虛構(gòu)寫作者通過(guò)在場(chǎng)的方式“以鮮明的介入性姿態(tài)直面現(xiàn)實(shí)塵世、重返歷史現(xiàn)場(chǎng)或?qū)ぴL文化足跡,……同時(shí)具有作者獨(dú)立價(jià)值向度的一種書寫樣式”[2]。《文化苦旅》就是余秋雨走出書齋,行走在祖國(guó)的大地上,不管是重返歷史現(xiàn)場(chǎng)還是游覽自然山水,都體現(xiàn)著作者介入現(xiàn)實(shí)的一種姿態(tài)。余秋雨邊走邊寫,這種“在場(chǎng)”的苦旅的寫作方式使文本呈現(xiàn)出一種真實(shí)的特質(zhì)。
其次,從敘事角度來(lái)看,非虛構(gòu)寫作不同于報(bào)告文學(xué)所追求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guò)敘事視角的下移,通過(guò)描寫底層的普通人和微小的事件來(lái)呈現(xiàn)一種宏觀的歷史走向,是一種由微觀到宏觀的敘事視角。正如有研究者所說(shuō)的那樣,“非虛構(gòu)更多地從個(gè)人性出發(fā),它更注重微觀視角和底層敘事。……在敘事上不渴望宏大,不追求主旋律,卻關(guān)注人性,重視日常生活的書寫”[1]24。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通過(guò)對(duì)歷史進(jìn)程中的普通人的描寫表達(dá)自己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走向失落的憂思。這種由小到大的敘事視角與非虛構(gòu)寫作所追求的敘事角度是一致的。
最后就是非虛構(gòu)寫作中所凸顯的問(wèn)題意識(shí),“非虛構(gòu)寫作者要有強(qiáng)烈的中國(guó)問(wèn)題意識(shí)。它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書寫必須具有反思和質(zhì)疑社會(huì)的品格,也即知識(shí)人言說(shuō)和闡釋當(dāng)下生活的能力”[1]23。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在游歷文化古跡和自然山水時(shí)不禁慨嘆歷史文化的輝煌,而反觀現(xiàn)實(shí)更多地感受到的卻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在日漸走向失落,中國(guó)文人精神正在逐漸消逝。因此,《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余秋雨個(gè)人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問(wèn)題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具有以下非虛構(gòu)的特征:首先是余秋雨一邊行走一邊寫作的“在場(chǎng)”性;其次是余秋雨所采取的由微觀到宏觀的敘事角度;最后就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寫作中所流露出的中國(guó)問(wèn)題意識(shí),即對(duì)文化走向失落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注。
一、“在場(chǎng)”的苦旅
1988年,文學(xué)期刊《收獲》以整年專欄的的形式連載發(fā)表余秋雨的歷史文化散文《文化苦旅》系列,1992年3月,《文化苦旅》系列作品結(jié)集出版,包括《自序》與36篇散文。
余秋雨在《自序》中就已經(jīng)闡明了自己寫作這本散文集的初衷,“連續(xù)幾個(gè)月埋首于磚瓦般的典籍中之后,從小就習(xí)慣于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huì)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lái),滿心滿眼滿耳都會(huì)突涌起向長(zhǎng)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3]1長(zhǎng)時(shí)間沉浸于書籍之中讓余秋雨覺(jué)得與現(xiàn)實(shí)生活有所脫離,他開(kāi)始懷念在土地上行走、在山間奔跑的感覺(jué)。更確切地說(shuō),這是一種精神的覺(jué)醒所帶來(lái)的身體的反抗。這種久困于書齋脫離現(xiàn)實(shí)的感覺(jué)也同樣是當(dāng)下許多非虛構(gòu)創(chuàng)作者進(jìn)入到非虛構(gòu)寫作領(lǐng)域的一個(gè)動(dòng)因。于是,余秋雨就借著受邀去各地參加研討會(huì)的機(jī)會(huì),開(kāi)始了自己有意識(shí)的行走旅途,企圖在行路中找尋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探尋內(nèi)心文化的需求。“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shí)在不少。旅途中的經(jīng)歷感受,無(wú)法細(xì)說(shuō),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gè)旅舍里,我已覺(jué)得非寫一點(diǎn)文章不可了。”[3]3走出書齋,行走在路上的余秋雨將自己在現(xiàn)實(shí)和歷史的沖擊下所涌現(xiàn)出的感悟動(dòng)筆寫下來(lái),邊走邊想,邊想邊寫,走一程寄一篇,這些余秋雨個(gè)人的鮮活的在場(chǎng)體驗(yàn)形成了《收獲》上的專欄,然后匯聚成了散文集《文化苦旅》。
《道士塔》《莫高窟》《陽(yáng)關(guān)雪》《沙原隱泉》《柳侯祠》《白蓮洞》《都江堰》《貴州儺》《白發(fā)蘇州》《江南小鎮(zhèn)》《寂寞天柱山》《風(fēng)雨天一閣》……余秋雨行走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從西北到江南,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旅途中的一個(gè)腳印。他徜徉在山水之間,流連于古跡之旁,“站在古人站過(guò)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huì)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tīng)著與千百年前沒(méi)有絲毫差異的風(fēng)聲鳥聲”[3]3。這種近距離與文化的接觸是生活在大城市所感受不到的,從圖書館和書本中所感受到和獲取的文化終究不如行走在大地上更為貼切和真實(shí)。他在行走中用其獨(dú)特的視角和洞察力去深思這古老民族的深層文化。5C182B28-95CB-4A42-A834-CFE1A1F0560F
二、敘事的下移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通過(guò)實(shí)地的走訪表達(dá)了對(duì)現(xiàn)代文化失落的憂思,但是他并沒(méi)有采取高大宏偉的視角進(jìn)行書寫,更多的是一種由小到大的視角,通過(guò)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中表現(xiàn)歷史進(jìn)程中的大事。
在開(kāi)篇的散文《道士塔》中,余秋雨通過(guò)王圓箓這樣一個(gè)在歷史洪流中毫不起眼的人物,敘述了莫高窟燦爛文化曾經(jīng)流向外國(guó)的失落和現(xiàn)在敦煌文化的研究者們內(nèi)心的悲憤之情。“我見(jiàn)過(guò)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gè)時(shí)代到處可以遇見(jiàn)的一個(gè)中國(guó)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nóng)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jīng)轉(zhuǎn)折,不幸由他當(dāng)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guó)古代最燦爛的文化。”[3]1王圓箓原本只是那個(gè)時(shí)代隨處可見(jiàn)的普通平民,因?yàn)樨毟F饑餓讓他流落到甘肅。彼時(shí),燦爛輝煌的敦煌文化還處于無(wú)人問(wèn)津的狀態(tài),王圓箓就以極低的價(jià)格讓俄國(guó)人、匈牙利人和法國(guó)人帶走了大量的文書經(jīng)卷和繪畫。正如作者所說(shuō),我們“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duì)牛彈琴,換得一個(gè)默然的表情”[3]2。在這個(gè)巨大的民族悲劇面前,逃荒而來(lái)的道士王圓箓只是一個(gè)讓人無(wú)法去怪罪的普通人,在那個(gè)時(shí)代,即使不是王圓箓也會(huì)是其他人。
余秋雨在參觀完都江堰之后,對(duì)都江堰這項(xiàng)工程極力稱贊,他認(rèn)為“中國(guó)歷史上最激動(dòng)人心的工程不是長(zhǎng)城而是都江堰”[3]41。都江堰歷經(jīng)幾千年時(shí)間的洗禮依舊為四川的民眾輸送清流,造福于川中的百姓。而這個(gè)偉大的工程不過(guò)來(lái)自于在歷史上一個(gè)并不起眼的人物,那就是李冰。李冰擔(dān)任蜀郡守也同樣是幾千年前的一個(gè)普通任職,但是正是這項(xiàng)毫不引人注目的任命,為四川和中國(guó)留下了都江堰。都江堰讓旱澇無(wú)常的四川平原變成了天府之國(guó)。“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資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壩一座,讓人們?nèi)ゲ略敗!盵3]45在浩瀚長(zhǎng)河的幾千年歷史中,中國(guó)出現(xiàn)了無(wú)數(shù)的地方官員,他們大多被時(shí)間所湮沒(méi),李冰也正是這無(wú)數(shù)的官員之一,但是都江堰這項(xiàng)工程卻使他跨越了千年的時(shí)間被后人所銘記。
儺是指人們?cè)谔囟竟?jié)驅(qū)逐疫鬼的祭儀,也是中國(guó)古代文化的一種體現(xiàn)。在《貴池儺》中,余秋雨為了去看這種從古代流傳下來(lái)的儺儀活動(dòng),特地在春節(jié)時(shí)期擠上擁擠的長(zhǎng)途汽車,奔赴安徽貴池山區(qū)。這種流傳已久的盛大儀式歷經(jīng)千年的時(shí)間而沒(méi)有消亡,也得益于一個(gè)普通人,一個(gè)小學(xué)的校長(zhǎng)。這位校長(zhǎng)在完成自己的校園內(nèi)的本職工作之后,開(kāi)始記錄當(dāng)?shù)剞r(nóng)民所唱的田歌俗諺,在記錄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這些不被重視的民間文化的重要價(jià)值,于是他“聽(tīng)了又聽(tīng),選了又選,然后走進(jìn)政府機(jī)關(guān)大門,對(duì)驚訝萬(wàn)分的干部們申述一條條理由,要求保存儺文明”。[3]77正是當(dāng)?shù)剡@位普通小學(xué)校長(zhǎng)的努力,讓貴州的儺文化得以保存。今天的我們除了知道他是當(dāng)?shù)氐囊晃恍W(xué)校長(zhǎng)之外,其余的一概不知,但是他極力挽救的、極力保存的儺文化卻依舊盛行著,流傳著。
余秋雨的散文中通過(guò)下移的敘事視角寫了很多如上所述的歷史長(zhǎng)河中的普通人,像《沙原隱泉》中的老尼、《風(fēng)雨天一閣》中的范欽、《上海人》中的上海普通市民、《牌坊》中尼姑庵的女教師、《信客》中不知姓名的信客等,正是這些普通的民眾讓我們對(duì)歷史的走向、文化的思考有了新的認(rèn)識(shí)。這種由下到上、由微觀到宏觀的敘事視角與非虛構(gòu)寫作是不謀而合的。
三、文化的關(guān)注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內(nèi)容主要圍繞文化而展開(kāi),其中有敦煌文化、洞穴文化、祭祀文化、繪畫文化、書法文化等,字里行間都寄托了他個(gè)人濃烈的憂患意識(shí)和深刻的文化反思,這種憂思與非虛構(gòu)寫作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中國(guó)問(wèn)題意識(shí)不謀而合。
在《廢墟》這篇散文中,余秋雨坦承中國(guó)缺少對(duì)廢墟的保存,也缺少真正的廢墟文化。當(dāng)面對(duì)廢墟的時(shí)候,“或者冬烘氣十足地懷古,或者實(shí)用主義地趨時(shí)。懷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趨時(shí)者只想以今滅古。”[3]255人們對(duì)于廢墟缺乏重視,對(duì)于廢墟之中所承載的文化更是視而不見(jiàn),“圓明園廢墟是北京城最有歷史感的文化遺跡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鏟平,造一座嶄新的圓明園,多么得不償失。大清王朝不見(jiàn)了,熊熊火光不見(jiàn)了,民族的郁忿不見(jiàn)了……”[3]255廢墟的推倒或者重建是在城鎮(zhèn)化、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不可避免會(huì)涉及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因此,面對(duì)廢墟,我們需要意識(shí)到廢墟之中所蘊(yùn)藏著的歷史,更應(yīng)明白“廢墟的留存,是現(xiàn)代人文明的象征”[3]256。
在《筆墨祭》中,余秋雨表達(dá)了對(duì)于書法被邊緣化、逐漸被新的書寫方式所取代的擔(dān)憂。“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shù),而是烘托書法藝術(shù)的社會(huì)氣氛和人文趨向。”[3]268正如余秋雨所說(shuō),比書法藝術(shù)邊緣化更讓人擔(dān)憂的應(yīng)該是社會(huì)氛圍、社會(huì)導(dǎo)向的改變,這是一種更為廣泛、更為持久的影響。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是迅速的也是喧囂的,我們身處其中更應(yīng)該親近書法藝術(shù),以此讓我們的心靈獲得審美撫慰。余秋雨也在這篇文章里寄寓了自己的希望,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傳承書法藝術(shù),希望人們?cè)谛[的社會(huì)中從筆墨中收獲心靈的寧?kù)o。
在《莫高窟》中,余秋雨站在精美輝煌的壁畫面前,不僅僅贊嘆其佛教故事和繪畫技法,也不僅僅感受到了歷史和文化,而是領(lǐng)悟到一種單純的美,這種美超越一切形式。這些壁畫不僅蘊(yùn)含了遙遠(yuǎn)的佛教故事、繪畫技法,更為重要的是“它似乎還要深得多,復(fù)雜得多,也神奇得多。”[3]14這些深刻而復(fù)雜的東西就是人們常常所忽略的美。余秋雨借此表達(dá)了自己的擔(dān)憂,“我真怕,怕這塊土地到處是善的堆砌,擠走了美的蹤影。”[3]16步履匆匆的行人對(duì)于美總是忽略的,站在千年的壁畫面前,余秋雨發(fā)出了對(duì)美的藝術(shù)的一種呼喚。
在《青云譜隨想》中,余秋雨看著來(lái)來(lái)往往參觀的人群,“面對(duì)著各色不太懂畫、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癥結(jié)還在于我們沒(méi)有很多強(qiáng)健的現(xiàn)代畫家去震撼這些游人”[3]89。這些游人行走在朱耷創(chuàng)作的庭院,對(duì)于近在眼前的書畫視而不見(jiàn)。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不僅僅是游人們對(duì)于傳統(tǒng)書畫藝術(shù)缺乏研究,不能夠欣賞到其中的美,更多地,還有現(xiàn)代書畫藝術(shù)已經(jīng)開(kāi)始走向衰落,沒(méi)有可以與古人相比肩的書畫大家,因此,現(xiàn)代書畫藝術(shù)的振興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除此之外,在《白發(fā)蘇州》《江南小鎮(zhèn)》《風(fēng)雨天一閣》《藏書憂》等一篇篇文章中都流露出作者對(duì)文化失落的憂思,對(duì)文化保護(hù)、文化拯救的愿景。
四、結(jié)語(yǔ)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20世紀(jì)90年代的中國(guó)掀起了一股文化散文熱潮,當(dāng)我們站在21世紀(jì)初的非虛構(gòu)浪潮中回望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顯現(xiàn)著非虛構(gòu)寫作的特征。他走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用堅(jiān)實(shí)的步伐丈量著中國(guó)的每一寸土地,用微觀的視角描繪著千年的文化故事,用獨(dú)特的文化內(nèi)容與文化反思引起了國(guó)人對(duì)于民族文化的關(guān)注,這些都與非虛構(gòu)寫作的特征是相對(duì)應(yīng)的。余秋雨所開(kāi)啟的文化散文時(shí)代與當(dāng)下非虛構(gòu)寫作的盛行之間是否有更深層次聯(lián)系,還值得進(jìn)一步深思。
參考文獻(xiàn):
[1]陳劍暉.“非虛構(gòu)寫作”概念之辨及相關(guān)問(wèn)題[J].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2021(5):20-27.
[2]晏杰雄.雙重文化視閾下的微觀痛感敘述——丁燕非虛構(gòu)寫作論[J].中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1(4):180-192.
[3]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
作者簡(jiǎn)介:徐磊,天水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與文化傳播學(xué)院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碩士研究生。5C182B28-95CB-4A42-A834-CFE1A1F056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