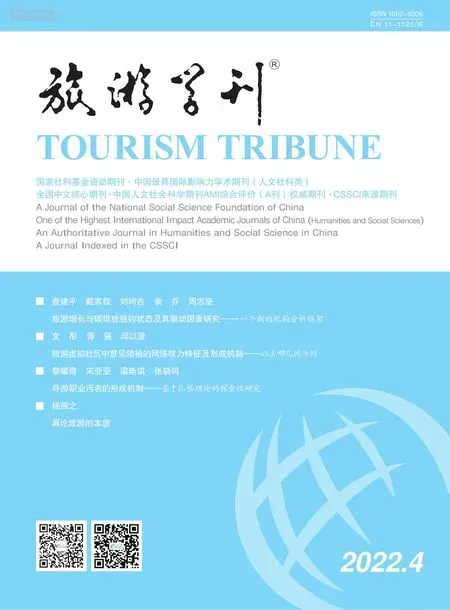再論旅游的本質

[摘 ? ?要]文章通過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深入地探討旅游的本質問題。從發生學、源動力上探討旅游的源起、發生、生成機制和目標。讓旅游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認識旅游的本質;讓旅游回到人的存在性,從生活世界“煩”的生存機制中探討旅游的源起和動力;旅游是去遠,去遠本質上不是空間的移動,是因去遠而獲得詩意地棲居,去遠是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本質,從而揭示了去遠與詩意地棲居的關系;旅游的終極目標是尋找到本真的自我,在旅游中,人顯現自身,澄明自身,獲得自我的覺悟,認識到自我存在于世的價值。該文提出旅游的世界人詩意地棲居模型,將旅游的目標分成3個層級,即詩意的生活、詩意的人生和詩意的存在,最終追問到了旅游的價值,旅游的價值已超越了旅游本身,關系到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價值,從而成就了旅游的社會價值。
[關鍵詞]旅游的本質;詩意地棲居;煩;去遠;生活世界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22)04-0140-13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15
引言
旅游的本質是什么?這是一個至今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本質的認識,將決定著構建有關該事物的一整套知識體系的基本綱領,知識的整體化和自洽性無不建立在對事物本質認識的基礎之上。對旅游而言,沒有對旅游本質的清晰認識將導致旅游學科構建的步履維艱和缺乏方向[1]。研究本質的方法很多,各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思考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事物本質也不一樣。比如柏拉圖認為,“理念”是萬事萬物的共相,是對事物抽象形成的普遍共相,是事物的本質[2];而亞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說”來解釋事物的本質[3]。鄧勇勇通過梳理西方哲學視野下旅游本質的研究,發現目前兩個典型的研究結論分別為“體驗”與“人詩意地棲居”[4]。謝彥君認為旅游的本質是“體驗”[1],筆者則認為是“詩意地棲居”[5],筆者和謝輝基還認為“旅是去遠,游是游戲”,體驗即是對藝術的經驗,并嚴格區別了體驗與經驗、經歷的不同,重新定義旅游體驗,意圖將旅游體驗、藝術經驗與“詩意地棲居”的關系打通[6]。筆者與謝彥君觀點不同,認為體驗是許多事物的共有屬性,不是本質屬性,本質屬性是事物“是其所是”的規定性,即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特有屬性,正因為事物的這一本性,讓它與另一事物區別開來[5]。而體驗,無論如何探討“具身性”[7],體驗本身就是人的意識對于某種經歷感知的共有屬性,不獨旅游具有體驗的屬性。將體驗作為旅游的本質和旅游研究的基本理論,不利于旅游理論的發展和旅游學科的建設。陳海波認為,謝彥君對旅游本質的追問是建立在其促進“旅游成學”這種始終不渝的學科情懷之上,楊振之則聚焦于本質概念的歷史脈絡、內涵以及旅游本質的單純界說,并不論及其他,隨后,他綜合辯證法與現象學的觀點,從不同側面將旅游抽象為一種移動、一種體驗和一種位勢[8]。自20世紀70年代Toffler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提出體驗業[9],Gilmore和Pine提出體驗經濟時代來臨以來[10],西方文獻主要研究體驗經濟,以及從身體、情感、內心、行為視角研究人的體驗經歷[11]。眾多旅游界學者研究了旅游活動過程中游客的體驗動機[12]和體驗的效果等[13],也探討了旅游體驗中的“身體”現象[14]。其實,旅游作為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有意義的一種活動,對旅游本質的探討,還是要回到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意義本身。人存在于世的意義與旅游究竟有什么關系,旅游對于人的存在究竟有何價值?旅游對于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究竟意味著什么?旅游的源動力來自何處?“詩意地棲居”與“去遠”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其實已超越了人們對旅游的理解,這正是胡塞爾所倡導的現象學方法“回到事物本身”(Zurück zu den Sachen selbst / 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15]。鄧勇勇回顧了學界有關旅游本質的研究后,提出了在現象學領域內,生活世界是旅游本質研究視角的觀點[4]。我們不僅要回到旅游本身,同時還要回到生活世界,回到旅游對于人存在于世間的意義本身來考察旅游,先懸置這些問題,再還原事實的真相,以期更深入地認識旅游的本質。
1 旅游的本質:回到生活世界
學術界對于日常生活世界與旅游世界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其主要問題是將日常生活世界與旅游世界看作是分離的二元世界。Jafari認為,旅游是人們離開世俗世界到神圣世界,又從神圣世界回到世俗世界的過程[16],將旅游世界譽為神圣世界,從而把旅游世界與生活世界分離開來。張凌云認為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環境總和叫慣常環境,旅游即是人們從慣常環境到達非慣常環境的過程[17]。龍江智和盧昌崇將旅游世界定義為“另一種生存空間”,生活世界與旅游世界是兩個世界[18]。謝彥君和謝中田也把生活世界和旅游世界看作兩個世界[19]。實際上,旅游仍然屬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與旅游世界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只有回到生活世界,才能找到旅游真正的意義和本質。
“生活世界”是胡塞爾現象學的核心概念,胡塞爾晚年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反對歐洲科學危機時,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認為自然科學已造成人與科學的分離,我們應回到生活世界來認識自身,認識人的生存危機,他的現象學的目標就是要為人類找回生活世界。他在該著作中說道:“我們所發現的這個世界是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實在的東西的世界。時空形式以及一切以這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物體的形狀,都屬于這個實際的經驗直覺的世界。我們本身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我們的人的身體的存在方式是與這個世界相適應的。”[20]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是自然形成的、我們身處于其中的日常周圍世界”,從重新出版的胡塞爾遺稿可知,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論述可謂卷帙浩繁,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將可能的、實際的、想象的、當下的、過去的、未來的生活世界都納入自己的分析、研究中[21]。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既是先驗的、自明的、敞開的、本原的,又是主體性的、境遇的、相對的、匿名的,還是奠基的、構造的,與先驗意識處于同等地位,從而是超歷史的、永恒在場的結構[22]。在胡塞爾那里,生活世界最終還是成為認識論。既然生活世界是一個認識論的概念,是對周圍世界的反思,顯然,它并不等同于生活本身。所以,胡塞爾的生活世界并沒有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本身,是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認識論。
歐洲傳統哲學,尤其是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在認識世界的時候,現象是相對于本質而存在的,人們預設了一個二元世界,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所謂之現象,則不是古典哲學之現象,而是通過“回到事物本身”,直接揭示事物本質。胡塞爾在《第六邏輯研究》中提出的所謂“明見性”(Evidenz)[23],即意識所意向的東西的自身顯現或自身給予。胡塞爾認為,人對世界存在的信任感是一種自然態度,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把對世界的哲學思考認為是探尋世界存在的內在本源或終極根據,與現象學“無前提性”或“明見性”原則背道而馳。同時,對自然態度的反思和批判,胡塞爾將其稱作“先驗懸置”[15],對世界之存在進行懷疑,繼承了笛卡爾對世界懷疑的態度,同時進行現象學的先驗還原。笛卡爾的懷疑論,一方面確立了個人作為主體的哲學思考,確立了近代哲學的主體精神;另一方面將世界作為意識的對象,促進了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哲學的發展,促進了科學的誕生。但同時又造成了人與世界的對立,導致了世界本身的喪失,人們對世界的懷疑和不信任。海德格爾雖然與胡塞爾一樣,其哲學的任務都是拋棄一切前提和先入之見,回到事實本身,但海德格爾認為,世界不是意識的對象,把世界作為意識的對象,是笛卡爾和胡塞爾的錯誤[24]。胡塞爾力圖回到生活世界,但他的生活世界其實是意識的意向性,世界本身變成了意識的意向之物,意識成了“事實本身”[15],而不是生活世界成了“事實本身”。這正是海德格爾與胡塞爾的重大分歧。海德格爾認為,世界先于意識,是預設的存在境域,胡塞爾將世界作為意識的對象實際上是將人與世界對立起來,與笛卡爾走上了同一條道路,最終,胡塞爾也沒有回到生活世界。所以,海德格爾立志要構建真正意義上的生活世界,從生存論和存在論上來分析人(此在,Da-Sein)“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的生存、存在狀態,人已源始在世界之中存在,本就被拋入世界,生活于世界之中[24]。
梅洛-龐蒂曾認為,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實際上是對胡塞爾的“自然的世界概念或生活世界的一種釋義”[25],在后面的論述中,我們會看到,盡管海德格爾是對胡塞爾思想的展開,但明顯地,海德格爾彌補了胡塞爾的不足,并真正回到了生活本身,回到了實際的生活、活生生的生活世界。
海德格爾是把人拋于生活世界中去尋找人存在的意義,這是他的終極之問。他摒棄了傳統哲學對人的先在性規定,直接將人回到原初的生存狀態中,考察人(即此在)的生存狀態,通過此在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狀態去領會人存在的意義。在生活世界中,海德格爾區分了人的非本真存在(常人、沉淪)與本真存在(良心、領會、籌劃等),認為只有在本真存在狀態下,人才能獲得存在的意義[24]。本真的存在狀態,與中國古代哲學中莊子的“逍遙”[26]、王陽明的“致良知”[27]、佛教的“自性”[28]其實一也,東西方哲學殊途同歸。
薩特寫《存在與虛無》時,他的存在主義現象學摒棄了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許多思考,直接進入生活世界對人的存在環境的現象進行研究,直入人的生存處境,探討人生的意義[29]。而梅洛-龐蒂更是進入對人的“身體”意義的探討。現象學越來越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世界,這是海德格爾的功勞。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胡塞爾系統地研究了“日常生活世界”,并把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存在方式都歸結于生活世界,還試圖回到生活世界探討人的生存和存在的意義,以此讓人類擺脫科學的危機。他的學生海德格爾批判地繼承發展了他的哲學,并真正還原到生活世界去探討人的存在方式,繼而開拓出一個世紀以來的現象學研究的繁榮,名家輩出,對世界的詮釋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于是,我們發現了生活世界的豐富多彩,旅游不過也是人的身體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旅游活動不可能獨立于日常生活世界,與日常生活世界形成一個獨立的二元的旅游世界。這是我們學術界所犯的一個認識論的錯誤。所以,對旅游本質的認識,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旅游就是人的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這便于我們探討旅游的發生、旅游的動力、旅游的源始究竟發端于何處,如此,旅游的本質才能顯明。
2 旅游的本質,回到人的存在性
先回顧一下筆者以前對旅游本質的觀點。首先,否定了體驗是旅游的本質,從海德格爾哲學引出體驗的認知,認為體驗不是旅游的本質[5]。其次,筆者又提出旅游的本質是“詩意地棲居”,這是筆者從海德格爾的哲學體系下得出的結論[5],還需要去不斷地豐富和完善它。其三,在此基礎上,筆者和謝輝基又提出,“旅是去遠,游是游戲”,旅游的體驗是“藝術的經驗”[6]。那么,“詩意地棲居”和“去遠”是什么關系呢?本文將旅游拋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到人的存在性作論述探討。
海德格爾哲學體系的核心是研究人的生存狀態和存在價值,也是西方哲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即“我是誰”“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我如何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笛卡爾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確立了“我在”的依據是“我思”,卻沒有言說“我在”的存在方式[30]。因此,海德格爾批評笛卡爾“在這個‘激進的’開端處沒有規定清楚的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義”[24]。“我在”的存在意義是一個基礎問題。其實,東西方哲學所追問的終極問題都是一樣的,都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只不過海德格爾是用他的現象學的體系來回答這個問題,而且他回答得很晦澀,不斷地造生詞生字。他把在世的存在者叫做“此在”,因為他是研究“我”這個人在世界上是用一種什么方式來生存的、存在的。從“此在”在“之中”、在“世界”之中,他要研究“此在”是怎么存在于這個世界當中[24]。這便是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重要部分,他從生存論和存在論等不同角度研究這個問題。在此基礎之上,研究人和人以及人和萬物是怎么打交道的。而馬克思說過“人和世界都是遍在聯系的”[31],黑格爾也是這樣認為的[32]。黑格爾和馬克思是研究人和世界的遍在關系。
既然“我”是“此在”,我和萬事萬物是怎么打交道(umgang)的呢?海德格爾又造了新詞“上手”(zuhanden)、“稱手”(zuhandenheit)和“照面”(begegnen)[24]。那么萬事萬物和人是要照面的,就是只有到了“上手”才能“照面”,“照面”而后才能產生關系,所以“上手”的狀態是非常關鍵的。這種說法有點像王陽明心學里談到的,即我和萬事萬物不是遍在關系,只有到了“上手”狀態時才產生關系,不過王陽明看得更深遠,他認為是我心想到的時候人和物才產生關系。為了說明這一事實,《傳習錄》中特地收錄了這樣一段故事:“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27]在此,“上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看似“上手”,實則“上心”。在“上手”之上還有一個“稱手”。“稱手”是海德格爾進一步解釋“上手”,“上手”可以得到兩個結果,一種是稱手,一種是不稱手,比如說一個錘子去敲打東西,如果一個錘子好用,可以敲打十年二十年,此時它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稱手的狀態,這種稱手只是說工具對使用者而言有某種功用,而不是說你對工具的理解貫徹到你生活的生命歷程中;而不稱手則是用錘子去砸核桃和用板磚去砸核桃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可能一生用錘子去敲打東西,但是不一定一輩子用板磚去敲打東西,而板磚所體現的就是一種不稱手的狀態。我們人和世界相處最好的一種方式就是“稱手”。海德格爾通過“稱手”延伸到對世界的理解應該是詩意的,而“不稱手”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種不詩意的[33]。“稱”就是適合的意思。從“上手”“照面”表現了人和所“照面”之人及物的一種聯系,但是到了“稱手”時,你發現這種聯系并不是每個都適合你,人和人之間會發生很多誤解、很多沖突和矛盾。“稱手”其實也可以翻譯成“友好”的意思“friendly”,即一種友好關系。所以在這個世界上人有很多種存在方式,“上手”和“照面”是一種關系,而“稱手”是一種選擇性的關系。就是說人和人之間合得來,你和他發生關聯的時候可能可以友好相處。國家和國家之間、萬事萬物之間同理。如果不適合那么就不會“稱手”,接著就會發生很多矛盾和沖突。人存在世界上會有很多的矛盾和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的存在就是因為不稱手而產生的。
海德格爾從現象學的角度解釋了人存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合理性、沖突感和遍在感。“稱手”的提出,為尋找人怎么能夠更好地存在世界上,也可以說是“此在”怎么發現我自身的價值提供了方法。這些是通過你與這個世界稱手的交道中發現的。這就是文明與文明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在不斷的矛盾沖突中不斷走向和諧。從這里可以看出,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是受到老莊哲學影響的1,可惜當時沒有人跟他翻譯王陽明《傳習錄》,翻譯了王陽明《傳習錄》,可能海德格爾會走向王陽明。海德格爾揭示了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存在這個世界中要從“照面”和“上手”的狀態下最終走到“稱手”的理想狀態。這個世界上人是不斷照面的,在這個“照面”當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要達到稱手狀態是比較難的,但稱手狀態是達到詩意的狀態的基本前提,“稱手”并不是詩意。“稱手”只是保持了人和人之間的友好、人和萬事萬物間的和諧狀態,但并不一定能上升到詩意。因為這個世界上人和人之間打交道除了沖突與和諧之外還有海德格爾所說的“煩”(sorge)[24]。
人生活在世界上是“煩忙”(besorgen)著的,這種煩即是人和人之間照面、人和事物之間照面,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種生存狀態就是“煩忙”。煩、煩忙是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基本結構,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構造,它具有生存論意義。“煩”是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一部研究人的生存論、存在論的核心,也是他對日常生活世界的本真描述,“此在的一般存在即被規定為煩”[24],“煩是此在本身的原始存在”[24],煩是人生活在世界之中的“這一結構整體的特征”[24],在“煩”的世界中,此在“沉淪在世”[24],沉淪實際上是對自我日常生活世界的逃避。海德格爾從煩的這一生存論機制出發,而到達了此在的源始的存在論機制,此在的存在論機制包含在煩中,即在“煩”中而存在[24]。人要獲得存在的意義,就是要逃離這種煩忙喧囂,不甘心“沉淪在世”。人生活在煩忙的沉淪的世界,人時時會想到要逃離煩忙[24]。西方人說旅游常用“escape from”這個詞,就是描述的人逃離煩忙、逃離日常生活的狀態[34]。此在在世,為逃避煩而尋找存在的意義,是生活世界中的常態,這正是旅游、旅行的價值。逃離煩忙、不甘沉淪,去釋放自我,去尋找生活的意義,通過旅行找回自我,這就是旅游、旅行的發生、動力和源始。
海德格爾研究了人“逃離煩忙”的存在狀態,他說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本質上就是要逃離煩忙達到詩意地棲居[35],而詩意地棲居并不是都要逃離現實生活到外面的世界去。它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你是可以獲得詩意地棲居的,即你不離開你的日常生活環境也是可以企達此境的,但是必須有個條件,即天地人神四位一體[5]。所以,詩意地棲居的前提是人要詩意地生活,能達到這種存在方式的人是真正能發現自我的人,比如藝術家、詩人,海德格爾說過“詩人是離上帝最近的人”[36],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境界也是我們難以理解的。第二層意思是普羅大眾要尋找詩意的生活主要靠逃離煩忙。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人因為“煩忙”,而不會看天,“煩忙”的人都是看著地上的,很少去看自己的內心,更沒有與“神”共在。與“神”共在的心靈是最平安最幸福的,這種人是可以詩意地棲居。這種思想和佛教禪宗的“空”的哲學思想[37]、老子的“道”[38]、莊子的“無”[39]及王陽明的“心外無物”[40]的思想是相通的。我們人生活在大地上,在煩忙當中在喧囂當中生存能成為詩人和藝術家的甚少,煩忙而又世俗的世界總要把充滿善良和詩意的人拉回到世俗的世界中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逃離煩忙便成了人們的心靈的追求。逃離煩忙去旅游能獲得天地人神四位一體。于是,旅游便成了人們生存的一種本性訴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旅游是人存在于世的發自內心的呼喚。這是從發生學、動力學角度來思考旅游源自何處,它的源始的發軔處在哪兒?旅游的發端處就是來源于人們對煩忙的日常生活的逃避,因為在煩忙的生活世界中人們疲憊不堪,生活沒有詩意和寄托,難以找到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之中的存在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不斷地在迷失自我。
從一個人的一生來看,出去旅游的時間并不多,但是人在內心中一直有一種去遠的愿望。后來我們又把體驗解釋為藝術經驗[6],其實藝術經驗和海德格爾所說的天地人神四位一體是完全相通的。因為人的存在一般情況下在日常生活環境中沒辦法體驗到天地人神四位一體,所以只有到遠方去。到遠方去通過旅游體驗通過藝術的經驗才能夠回到自我的內心,才能夠發現自我。所以人的內心不斷地渴望旅游,旅游在人的生存意義上看似不太重要,但在人的存在的意義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旅游的渴望,那么人的存在就沒有意義。從經濟學上來說,恩格爾系數達到50%以上時,表明人們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的支出,人們的生活完全處于勞碌的世界當中,這時人們主要的支出是為生存而不是為存在,收入的大部分用來養兒育女孝敬老人,滿足基本生存;只有當恩格爾系數處于40%~50%的時候,人們的精神需求的消費才被激發[41]。在沒有達到精神需求的條件時,旅游只是心中的夢想,但是人們的神游,精神上對旅游的渴望一直是存在的。為什么還存在這種理想和渴望,因為人要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所以當達到可以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條件時,人們一定會出游。但不管人們是否有實力去旅游,旅游都是人的一種本性存在。
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本質屬性是要尋求自己存在的價值。可是,現實生活又是無助的,科技越發達我們越孤獨,就像英國詩人艾略特所吟唱的[42]:
我們是空心人
我們是稻草人
相互依靠
頭腦塞滿了稻草,唉!
面對現代的這些空洞的人、孤獨的人,羅洛·梅提出人要認識自我、尋找自我[43]。煩是造成孤獨、無助、焦慮的根本原因。我存在的價值,只有在詩意地棲居下我才能夠發現自身的真正價值,這才是我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意義。筆者認為,海德格爾雖未明言旅游,但其論述的從“煩忙”到“逃離煩忙”這個過程揭示了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這是人從煩忙的日常生活世界逃離而尋求旅游的真實世界的過程,并且對這一過程的揭示并非只看重這一過程現象(我們往往只看到了這一現象),而是深入地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質。
3 旅游是去遠,是人存在于世的一種存在方式
從旅游的發生上,人逃避“煩”而去旅游,是為了獲得人的存在性,獲得人存在的價值,是為了“詩意地棲居”。所以,人要“去遠”。那么,“去遠”與“詩意地棲居”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在《旅游體驗的再思》一文中,筆者和謝輝基曾提出旅游的存在性是“去遠”(Ent-fernung/distancing)[6]。去遠和人的空間本質性是相互關聯的,這就是此在的空間性。在研究空間的本質性時海德格爾提到了幾個關鍵詞“場所”“位置”“定位”[24]。“場所”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代表了一種方向性,另外一個指的是環圍,指周邊的環境。空間的環圍確定了周圍世界的存在,周圍世界的存在也就確定了場所本身的位置。“場所”這個概念比“位置”要大。“位置”和“定位”是一個詞,它是指萬事萬物存在上手狀態或者是在手狀態的一種存在地,而“定位”就是確定物的位置,確定它周圍世界的周圍性,這樣物的空間存在性就確定下來了,因此才可能有“場所”。《存在與時間》其實也研究空間,研究人的空間性,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是需要周圍世界的,需要周圍世界來給他定位。
定位依賴于因緣(bewandnis),因緣具備“指引性”。因為有相互的指引(verweisen),所以能夠上手。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以用具(zeug)的整體性為例,在對“錘如何能復歸其本性”的解析中,將上手的東西的存在性進一步規定為“因緣”[24]。所謂因緣,即因何所緣。“此在為他的存在而存在,此在的煩忙活動先行揭示著向來對他有決定性牽連的場所,這種場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緣整體性參與規定的,而上手的東西之為照面的東西就是向著這個因緣整體性開發出來的”[24]。換言之,只有屬于用具上手性的何所用、指引和“因……緣……”關系預先被揭示了,用具才能如此地來照面和上手。在此,借助“因緣”一詞,海德格爾所要揭示的其實是“場所”所在的空間性。因為人存在于場所當中,每個人都要確定他的位置、他的定位、他的場所。海德格爾認為,居住是人本質的特征,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質是居住。每個人都要在一定的場所里面,在場所里面核心的本質是居所[44]。人是為了棲居而活著的,人要棲居在大地之上。海德格爾談到人要棲居在房間里,人在居住當中天地人神共在四位一體時才能達到詩意地棲居[35]。后來諾伯·舒爾茨寫的《場所精神》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通過現象學由居所房子來研究人的棲居方式,揭示人的存在方式[45]。所以這是從空間性來揭示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場所”所在的空間性,實際上是因緣所在的整體,它是具有關聯性的。海德格爾講的“因緣”,就是說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上,他和這個世界發生關聯處于“上手”和“照面”,哪些人“上手”、哪些人“照面”都是因為因緣,哪些人存在都是因為因緣。因緣就是前述的處于“上手”和“照面”狀態,如果大家還合得來就是處于“稱手”狀態。世界的整體是具有關聯性和整體性的。而人存在世界上的空間性也因為因緣的整體性得到了統一。進而周圍的世界也因為整體性關聯而獲得了場所的空間性。所以所有空間的存在方式都是與周圍世界整體關聯的,因此人存在這個世界上不僅看他“上手”“照面”的問題,還要看他與周圍世界是如何關聯的。而周圍世界的因緣和整體關聯反過來可以成為每一個人在居所在場所的存在狀態。
“但具有空間性的上手事物具有合乎世界的因緣整體性,而空間性就通過這種因緣整體性而有自身的統一。并非‘周圍世界’擺設在一個事先給定的空間里,而是周圍世界特有的世界性質在其意蘊中勾畫著位置的當下整體性的因緣聯絡。而這諸種位置則是由尋視指定的。當下世界向來揭示著屬于世界自身的空間的空間性。”[24]空間的關聯整體性意味著空間絕非孤立的存在,它必須與周圍世界相聯系。空間的生存并非偶然,周圍世界影響著空間的空間性,空間的形式、個性、表現無不受其影響;空間也必須尊重周圍世界,空間的生產才具有意義。旅游學術界對空間的生產研究得如火如荼,海德格爾對空間的研究無疑具有指導意義,如果用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去解釋空間生產,會有很大的收獲。
先從“位置”“定位”“場所”來定位了人的空間存在性。每個人生活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都有他的定位和自身的位置,他都會與這個世界廣泛發生因緣、廣泛存在著空間的關聯性,而且都會和周圍世界打交道。一方面他要廣泛的和周圍世界交往,另一方面周圍世界的存在性也規定著他自身此在的空間性,他們是關聯如一體的。至此把人的存在的空間性明確了。
那么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間性如何?“此在在世界‘之中’。其意義是它操勞著熟悉地同世內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所以,無論空間性以何種方式附屬于此在,都只有根據這種‘在之中’才是可能的。而‘在之中’的空間性顯示出去遠與定向的性質。”[24]什么是“去遠”呢?“去遠是人存在于世的一種存在方式”,人的空間存在性就是去遠,我們知道,旅游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種時空存在行為,這樣旅游也是一種去遠的存在方式。旅游世界的空間經由旅游者感知意識和旅游客體共同生成,旅游者經由“去遠”使得旅游世界上到眼前,其空間呈現為一種感知場域的擴充[46]。所以,筆者認為,旅游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是人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一種存在方式。
“去遠”是一種存在建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去遠方或一種距離上的去遠[46],而更多的是一種存在意義上的理解。“去遠說的是相去之距離,是去某物之遠而使之近。此在本質上就是有所去遠的,它作為它所是的存在者讓向來存在著的東西到近處來照面。”[24]旅游作為“去遠”本質上是讓世界走近我,來讓我照面。這種“照面”就是“上手”是相遇,照面和相遇的本質就是使這些遠空間事物的存在性來照面。照面使物近化(das n?hren),“近化乃切近的本質。切近使疏遠近化(n?he n?hert das ferne),并且是作為疏遠來近化。切近中保持疏遠,在保持疏遠之際,切近在其近化中成其本質。”[35]顯然,“近”和“近化”是為了說明“去遠”的本質。在去遠的過程中,科學對距離的消失并沒有帶來真正的近,所謂的近并不在于距離的大小,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心理感受[47]。“近”與“遠”的相對,不是靜態的計量概念,也非科學意義上的動態運作過程。所謂的“近”,其實就是物的聚集[35]。在物的聚集和居留之際,天地人神四位一體,在筆者《論旅游的本質》[5]和《旅游體驗研究的再思》[6]兩文中詳細論述了物的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體和旅游的關系。因此,才有“近”的到來,才有“近”與“遠”的統一。作為“去遠”的“近化”,不是消滅遠,而是使“遠”成為“遠”。在“遠”與“近”獲得統一之際,人得以返回自身,并且獲得詩意棲居。因此,進一步講“近”和“去遠”的實質,其實是天地人神“四重整體”(geviert)中各要素的相互趨近,因為它們在趨近中各自保持了本己,故而實現了“遠”。
因而,旅游的本質是去遠相遇,看起來是走向遠方,而實質上是使遠方走近自己而相遇。而此在去遠越多相遇越多,此在存在的空間性就越大,就是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存在的空間性越大,你的視野就越寬廣。走得越遠你就越容易天地人神四位一體地棲居在這個世界上,因為你見到的大多是美好的東西。所以“此在”在這個世界當中存在,其空間性本質是“去遠”,即“去遠”是此在的存在機制、存在本質。使所有存在者相遇照面,都是其本質和需要。至此又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們存在在世界之中,在本性上是渴望去遠、渴望與世界相遇、渴望與世界照面的,這一去遠的本性訴求本質上并非在于空間的移動,而在于詩意地棲居。
“此在日常生活中的尋視去遠活動揭示著‘真實世界’的自在存在,而這個‘真實世界’就是此在作為生存著的此在向來就已經依之存在的存在者”[24]。“此在”是在煩忙世界中尋視著“去遠”,要通過“去遠”揭示這個世界的存在,目的是想讓真實世界處于“上手”狀態,就是要尋找真實世界。真實世界被Cohen轉換成真實性,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假命題[48]。Cohen的《旅游體驗的現象學》一文[49]是我國學者研究旅游體驗引用較多的,不少學者認為這篇文章“可看作現象學進入旅游體驗研究領域的起點”[50],此文對旅游體驗研究影響深遠,意義重大。遺憾的是,筆者發現在此文中Cohen并未研究現象學,他只是研究了旅游體驗這一現象,即把旅游體驗當做一種現象來研究,而不是用現象學理論與方法研究旅游體驗。
海德格爾所說的真實世界,基于人們在煩忙的世界中難以尋找到真實世界,因為這個世界到處是謊言、到處是欺詐、到處是喧囂,所以他認為人要去遠,才能獲得真實的世界。我們在旅游、在“去遠”的時候,實際上是讓遠方的世界來和我們“照面”。通過遠方的世界“照面”“上手”來企圖追尋到真實的世界。這種真實的世界,顯然不是Cohen他們所說的真實性的問題[48]。人們能夠通過“去遠”、旅游尋找到真實的世界,詩意地棲居在這個世界上,而非尋找真實性。
“此在”存在的本質是“去遠”,在“去遠”的狀態下獲得它的空間性。這是“此在”的一種存在方式。“此在”以這種存在方式,證明著“此在”存在于世界之中。使遠者近而走向遠方,使“此在”的空間不斷地延續。所以旅游者在“去遠”中獲得了存在感,尋找到了詩意地棲居的存在性[6]。旅游者是通過走向遠方,讓遠方“上手”“照面”而確立起“煩忙”著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價值。如果沒有“去遠”,那么人“煩忙”著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價值是很難確立的。也就是說,旅游者在“去遠”的時候,他在那個地方尋找到真實世界,尋找到了詩意地棲居,然后返回到日常生活繼續以前的生活,以此來確立日常生活的意義,從而讓人尋找到自己的價值[51]。人通過旅游尋找真實的世界,進而尋找到自我[52]。日常生活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比張凌云所說的慣常環境與非慣常環境[17]應該更有意義,一個是價值的尋求,一個是現象的述說。真實的世界是與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相對應的,現實的世界難以獲得真實。人就是這樣發現自我的,去“去遠”、去旅行、去詩意地棲居,本質上是尋找到自我,去尋找到自我也是尋找到日常生活的價值之所在。這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和旅游的真實世界之間的關系。看名山大川會體驗到崇高感;看災難博物館,雖然說是黑色旅游,但是人的情感會得到升華,體驗到這個世界的真善美,體驗到世界的偉大;探險、背包旅行等,可以激發自己的潛能,重新認識自我。這就是旅行的意義。人在“去遠”的過程中,重新認識到自我的價值,認識到了真實的世界。
至此筆者認為,旅游的世界其實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它們是同一個世界,只是因為日常生活世界的“煩”,人們無法獲得真實的世界,因此通過旅游、“去遠”而達到詩意地棲居之境,獲得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其實也是蘊含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你只有撥開你生活中的煩忙,才能獲得真實的世界。
所以說旅游走向遠方是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本性。現實生活的世界也即“煩忙”的世界,它是依靠“去遠”來驗證其存在的價值的,這就是旅游的根本意義,就是人在旅游中去追尋真實的世界、追尋存在的意義、追尋自我的價值。旅游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為了尋找到自我,獲得詩意地棲居[48];一方面是為了反過來驗證人的日常生活的存在意義[53]。
4 旅游的終極目標:尋找到本真的自我
海德格爾對于“此在”是誰進行了系統探討,他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找人存在于世的終極意義。他研究了我與世界共在,研究了他人與世界共在的“上手”與“照面”的關系。目的就是要揭示此在共在存在于“煩忙”世界中如何來認識自我,他也認為認識自我的途徑其實是領會自我。“以共在為基礎的生動貼切的相互認識自身常常取決于自己的此在各自在何種程度上領會了自己本身”[24],在共在世界當中認識自我的途徑其實是領會自我,領會到自身的價值、領會到自己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每個人都是常人。每個常人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常人自己,一個是本真自己[24]。作為常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時候往往是煩忙著的,甚至是沉淪著的,但是始終有一個本真的自己存在,并且人們一直追求著本真的自己。如果人不追求本真的自己,人將不能稱之為人了。那么要尋找到本真自己只有企達詩意地棲居,常人要實現詩意地棲居,主要的方式就得去遠方發現真實的世界,從而發現本真的自己。詩意地棲居不管以何種方式實現,最終都指向了真實的世界和本真的自己,最終是要發現本真,而發現本真需要去蔽。去蔽是現象學追求事物本身的一種方法,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心學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一種重要方法。去除遮蔽就是要揭示“此在”本身的存在,就是要最終“領會”到自我。此處的“領會”也是一種領悟,是對“此在”基本狀態的具體領悟。
去蔽,即撥開對自我的遮蔽,發現本真的自我、真實的自我,這一過程就叫“澄明”。此在的存在本性即澄明,“作為在世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澄明的,不是由于其他存在者的澄明,而是,它本身就是澄明”[24] 。此在對自我的發現,與其說來自一種直接的自我尋找,不如說來自一種逃遁[24]。可能在逃遁日常生活時,更易于發現自我。這種逃避,實際上是一種自我的現身,現身就是自己顯示自己,回到自己本身,顯現自身,就是回到自身,就是澄明。所以,旅游就是一種自我逃避,就是在去遠中現身。旅游的價值指向就是人尋找自我。
自我現身(如外出旅游所提供的契機),只是為認識自我提供了一個契機,并不意味著外出旅游都會達到自我現身的效果,也并不意味著自我現身了的每個人都能認識到自我,尋找到自我。獲得了自我現身的契機,關鍵要看一個人自我的領會能力。海德格爾將領會分為尋視、顧視、透視3種狀態:顧視是視過去之在世,尋視是視煩忙在世,透視即自視,即自我認識。自我認識,達到澄明境界[24]。
此在的澄明,是此在“在之中”的完全展開狀態(即去蔽、現身),只有在這種完全展開狀態時,視、自視才成為可能。此在的澄明,只有內心的澄明才是真正的澄明。海德格爾說,所謂閑談、好奇、兩可、沉淪等都是內心被蒙蔽的狀態,最終被拋[24]。一切流言蜚語、欺騙與不道德、不仁不義,皆是內心不澄明的結果。
澄明、自我現身,也是獲得真理的有效途徑。真理是什么?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都把真理看作是人的判斷與它的對象的符合[54]。海德格爾認為,真理的存在結構,不是認知、判斷和對象的符合,它不涉及意識的內容、意識過程與物的關系,而是存在者的自我顯示、自我現身[24],即回到存在者本身而顯示自身。海德格爾對真理的看法可謂兩千多年來所未有。探討真理的存在論結構、真理的存在,是自我揭示和自我顯身。此在“在真理中”,說明此在自己展開自己,自己揭示自己,這是最本真的生存論存在論,最本真的真理。如何自我揭示自我?就是最本真的展開、顯身。
此在如何生活得有詩意?他必須是真在,處于揭示的、展開的狀態,而不是封閉的、遮蔽的狀態,達到這種真的存在狀態,生活才有詩意。由于此在的生存論機制是煩,要么展開,要么遮蔽。此在旅游的時候,人是主動在世界之中展開著、揭示著,人去掉偽裝和封閉,這種顯身(現身)狀態容易讓人回到真實的自我。所以,旅游是人展開自我、獲得真理即獲得真我的重要途徑,人尋找到真實的自我,并獲得詩意地棲居。
從煩的這一生存論機制,到達了此在的源始的存在論機制,此在具有了存在的意義,獲得了真、真理、真我,實現了從生存論到存在論的升華。此在的存在論機制包含在煩中,即在“煩”中而存在[24]。此在在世,為逃避煩而尋找存在的意義,是生活世界中的常態。這正是旅游的意義。
旅游作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代表著人的一生是否圓滿。未旅游的人作為人生始終有一種懸欠(即缺失),旅游是人的成長和成熟的一個重要過程和重要途徑。
并非所有的旅行都能讓人詩意地棲居,這要看旅游是否具有旅游性,旅游本身是否有詩意,即旅行者在旅游的場景中是不是天地人神四位一體。無詩意的旅游也是大量存在的,那些沒有詩意和藝術經驗的旅游,那些只是去遠讓景觀來照面而遠離旅游本性的旅游,都不是詩意的旅游。我們可能從城市化的工業場景進入旅游化的工業場景,從科技化的日常煩忙到科技智能化的旅游煩忙,這些都不是詩意的旅游,太過于科技智能化的旅游也是違背旅游本性的。詩意的旅游是要讓旅游者體驗到與煩忙的日常生活世界完全不同的存在狀態,用現象學還原、直觀的方法,就是讓旅游者體驗到世界本來的樣子,而不是換個地方體驗另一種現代科技生活與智能生活。
詩意地棲居的旅游讓人不斷成長、不斷成熟。人每一次出行旅游,都可能是一次走向詩意的生活,詩意的生活是人逃離煩忙世界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是人生命質量提升、獲得幸福感的重要表現。若一個人經常逃離煩忙,旅行頻次較高,就容易獲得詩意的人生。旅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是尋找一個人的詩意的存在。詩意的存在,是一個人在旅行中悟道、尋找到自我、認識到自我存在的價值的過程。所以,旅游就是人生的幸福之源、教育之本、成長之基。
所以,旅游的本質是人詩意地棲居,這既是旅游的源動力,也是旅游的目標。旅游是人獲得詩意地棲居的重要途徑,實際上,旅游的價值并不僅僅是人獲得了詩意地棲居,而是獲得了詩意地棲居的人在旅游中顯現了自身,獲得了真理,發現了自我。于是,旅游的價值已經關乎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價值,它超越了旅游本身,而成就了旅游的社會價值。
通過以上論述,筆者提出“旅游的世界人詩意地棲居模型”(圖1),將旅游的人詩意地棲居分為3個層級:詩意的生活、詩意的人生、詩意的存在。如果把旅游視為每個人終生的修行,人就是在這樣的修行中,慢慢悟道、慢慢發現自我的過程。
筆者不只是在2014年《論旅游的本質》一文中提出旅游的本質是人詩意地棲居[5],在1996年出版的《旅游資源開發》一書中,已經提出旅游是旅游者離開世俗世界走向詩意的世界而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55]。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旅游的世界人詩意地棲居模型”,進一步闡明旅游、人詩意地棲居、人的存在價值之間的關系。詩意的生活,是旅游者追求的第一層目標,也是基本目標,即通過旅游提高自己的生命質量和幸福感,旅游是一個人生命質量和幸福生活的重要體現,因旅游而使生活充滿詩意。生命質量(the quality of life)或者生活質量,是目前國際旅游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話題,被定義為一個人的生活滿足或不滿足、幸福或不幸福,或者心理或主觀幸福感[56],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生活質量是反映個人目標、期望、標準、意識和對生活的看法[57]。幸福感和生命質量包括自我實現和社會關系、價值等高層次的心理需求[58]。關于幸福(感)的問題,早在幾千年前的古代中國、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一些先哲們就對其做過各種描述,他們主要采用哲學思辨的方法進行詮釋。現代幸福感研究基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快樂論(hedonic)與實現論(eudemonia),進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59]。快樂論體現在主觀幸福感研究中,認為幸福感由愉快與快樂構成,重視個人的主觀評價和感受,認為如果一個人有較多的積極情緒、較少的消極情緒,同時還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那么這個人就是幸福的。實現論體現在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研究中,認為幸福不能只是單純的快樂,更重要的是人潛能的實現,注重人本質的實現與顯現。社會幸福感把考察的視角放在了個人和社會的融通上,關心個體對社會的貢獻和融合,從而在更廣闊的社會環境下來理解人類良好的存在狀態[60]。研究者用幸福感來定義生命質量,邢占軍和黃立清認為生命質量是“人的存在質量,即在特定社會中人們各種需要滿足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表現為人們所享有的生存與發展方面的客觀福利狀況以及所體驗到的主觀福利(即幸福感)水平”[61]。焦嵐認為幸福感是生命質量研究的一個視角,生命質量不僅包括生活質量,還包括生存質量和更高層次的生命追求[62]。
旅游的高級目標是詩意的人生,旅行是一個人的終生修行,人不斷在旅行中挑戰自我,挖掘自我的潛能,如探險、游歷、研學、科考等,旅行是發現、旅行是修行、旅行是自我教育,在這樣的旅行中,獲得詩意的人生。旅游的最高目標是自我的詩意的存在,旅游讓人尋找到自我,發現自我的價值和人存在于世的意義,獲得“澄明”[24]和“自性”[28],達到“致良知”[27]的境界,是人的價值的實現和超越,達到莊子在《逍遙游》中忘我的境界[26]。
5 結束語
本文通過現象學還原的方法,進一步深入地探討旅游的本質問題。從發生學、源動力上探討旅游的源起、發生、生成機制和目標。首先,第一次懸置旅游的本質,回到生活世界。通過還原,發現以前學術界構建了虛無的二元世界——生活世界和旅游世界,但實際上旅游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對旅游本質的認識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本身。之后,進一步懸置旅游的本質問題,也進一步懸置人在生活世界中旅游與生活世界之間的關系。通過還原,尤其是回到海德格爾的生活世界去思考問題的時候,發現了“煩”的生存論和存在論機制,恰好是旅游產生的動力和本源。人逃避“煩”而去旅游,是為了“詩意地棲居”。而旅游的存在性是“去遠”[6],筆者又進一步探討了“去遠”和“詩意地棲居”之間的關系。去遠本質上不是空間的移動,去遠是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本性,是因去遠而獲得詩意地棲居,從而獲得真實的世界,獲得人的存在性,獲得人存在的價值。至此,筆者已厘清旅游的源動力、旅游的本質,并打通了去遠和詩意地棲居之間的關系。在進一步的論述中,筆者發現詩意地棲居的目標,也是旅游的終極目標是尋找到本真的自我(但很難達到),在旅游中,人顯現自身,澄明自身,獲得自我的覺悟,認識到自我存在于世的價值,據此,本文提出了旅游的世界人詩意地棲居模型,將旅游的目標分成3個層級,即詩意的生活、詩意的人生和詩意的存在,最終追問到了旅游的價值,旅游的價值已超越了旅游本身,關系到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價值,從而成就了旅游的社會價值。
旅游是人離開煩忙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世界尋找真實世界,尋找真實自我,獲得詩意地棲居;同時,又反過來驗證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意義。所以旅游是人存在于世的一種人無法拋卻的存在方式,它與人的關系與生俱來,不管一個人是否真正去旅游或者是否真正有能力去旅游,但“去遠”永遠是人心靈的需求。人通過旅游擺脫煩忙的日常生活世界而棲居在大地上并發現自我,這就是旅游對于人類的價值,這也是旅游的源生動力。因之,旅游的價值遠遠超過人們平常所說的旅游本身,而觸及到人作為人存在的價值意義。所以,從人性上來說,旅游是人的精神剛需。這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并不矛盾[63],與恩格爾系數的理論也不矛盾,旅游屬于精神需求。正因為從人的存在性來說,旅游需求是人的精神剛需,當人們的生活水平達到人的出游條件時,這一需求即從內心被激活。所以,從源生動力上來看,旅游的發生本質上是為了尋求詩意地棲居。
人在旅途中,在世界之中存在,能發現自我,獲得真我。通過旅游,可獲得美好的人生,提高生活質量,并能完善自我。筆者認為,旅游是人終生的修行,人在旅行中潛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可不斷地提升自我和修煉自我,旅游又肩負著教育的使命。旅游就是人生的幸福之源、教育之本、成長之基。英國、美國等國家在100年前倡導的自然教育和日本的修學旅行,已得旅游之真諦。
時至今日,我們現在的生活世界依然是科學技術控制和操縱著人類,比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時更盛。物質的富足和精神的空虛并存,物質與精神分裂,人與自然分裂,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受到阻礙;甚至人與社會分裂,人類越來越進入一個分布式社會,蝸居和宅人越來越多,社會溝通也將成為大問題。這些預示著一場新的社會危機即將到來。而旅游生活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增加人與自然的聯結,人與社會的聯結,人與自我的聯結,豐富人的精神生活,療愈人的各種現代病,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所以旅游對于人類的存在有很大的影響。從以上論述,筆者認為,旅游學是不是一級學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研究人,我們就繞不開旅游學科,換言之,旅游的研究也不僅僅是旅游學科自己的事。我們應打破學科桎梏,避免畫地為牢,以開放的胸襟迎接旅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同時我們也知道了,旅游的本質既然直擊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中的存在價值,旅游的價值已經大大超越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旅游本身,我們應當前往更廣闊的時空中去研究旅游,去尋找旅游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謝彥君. 旅游的本質及其認識方法[J]. 旅游學刊, 2010, 25(1): 26-31. [XIE Yanjun. On the essence of tourism and its way of cogni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 26-31.]
[2] 柏拉圖. 理想國[M]. 郭斌和, 張竹明,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6: 101. [PLATO. Republic[M]. GUO Binhe, ZHANG Zhuming,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101.]
[3] 亞里士多德. 形而上學[M]. 苗力田,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 333. [ARISTOTLE. Metaphysics[M]. MIAO Litian,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3.]
[4] 鄧勇勇. 旅游本質的探討——回顧、共識與展望[J]. 旅游學刊, 2019, 34(4): 132-142. [DENG Yongyong. The essence of tourism: Review, consensus and prospects[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4): 132-142.]
[5] 楊振之. 論旅游的本質[J]. 旅游學刊, 2014, 29(3): 13-21. [YANG Zhenzhi. On the essence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3): 13-21.]
[6] 楊振之, 謝輝基. 旅游體驗研究的再思[J]. 旅游學刊, 2017, 32(9): 12-23. [YANG Zhenzhi, XIE Huiji. Rethinking the experience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9): 12-23.]
[7] 樊友猛, 謝彥君. 旅游體驗研究的具身范式[J]. 旅游學刊, 2019, 34(11): 17-28. [FAN Youmeng, XIE Yanjun. Embodiment paradigm of tourist experience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1): 17-28.]
[8] 陳海波. 旅游的本質及旅游學的學科邏輯新探[J]. 旅游學刊, 2019, 34(11): 124-135. [CHEN Haibo. An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ourism and disciplinary logic of tourism science[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1): 124-135.]
[9] 阿爾文·托夫勒. 未來的沖擊[M]. 黃明堅, 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195. [TOFFLER A. Future Shock[M]. HUANG Mingjian,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2018: 195.]
[10] GILMORE J H, PINE J.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4): 97-105.
[11] SCHMITT B H. Experiential Marketing: How to Get Customers to Sense, Feel, Think, Act and Relate to Your Company and Brand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26-30.
[12] FODNESS D. Measuring tourist motiv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3): 555-581.
[13] WANG N.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2): 349-370.
[14] 謝輝基, 楊振之. 論旅游體驗研究中的“身體”現象及其認知[J]. 旅游學刊, 2020, 35(7): 117-132. [XIE Huiji,YANG Zhenzhi. On the phenomena and cognition of the “body” in the research of tourism experienc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7): 117-132.]
[15] 胡塞爾. 純粹現象學通論[M]. 李幼蒸,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75; 94-98; 129; 135. [HUSSERL E. Reasonable Argument of Pure Phenomenology[M]. LI Youzheng,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75; 94-98; 129; 135.]
[16] JAFARI J. Tourism models: The sociocultural aspects[J]. Tourism Managment, 1987, 8(2): 151-159.
[17] 張凌云. 非慣常環境: 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建構旅游學研究框架的一種嘗試[J]. 旅游學刊, 2009, 24(7): 12-17. [ZHANG Lingyun. Unusual environment: The core concept of tourism research: A new framework for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12-17.]
[18] 龍江智, 盧昌崇. 從生活世界到旅游世界: 心境的跨越[J]. 旅游學刊, 2010, 25(6): 25-31. [LONG Jiangzhi, LU Changchong. From life-world to tourism-world: Across the state of mind[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6): 25-31.]
[19] 謝彥君, 謝中田. 現象世界的旅游體驗: 旅游世界與生活世界[J]. 旅游學刊, 2006, 21(4): 13-18. [XIE Yanjun,XIE Zhongtian. Tourist experience in the tourist world: A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4): 13-18.]
[20] 胡塞爾. 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M]. 張慶熊, 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 60. [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 ZHANG Qingxi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60.]
[21] 倪梁康. 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現象學——基于《生活世界》手稿的思考[J]. 哲學動態, 2019(12): 58-66. [NI Liangkang. Husserl s phenomenology of the life-world—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life-world manuscript[J]. Philosophical Trends, 2019(12): 58-66.]
[22] 傅永軍, 張志平. “生活世界”學說: 哈貝馬斯的批判與改造[J].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7(4): 8-13. [FU Yongjun, ZHANG Zhiping. The doctrine of the “life-world”: Habermas critique and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7(4): 8-13.]
[23] 胡塞爾. 第五、第六邏輯研究[M]. 李幼蒸,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 222-227. [HUSSERL E. Fifth and Sixth Logical Studies[M]. LI Youzheng,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222-227.]
[24] 馬丁·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M]. 陳嘉映, 王慶節, 譯. 上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 1987: 31; 65-78; 102-109; 110-124; 126-139; 149; 157-161; 163; 166; 174-188; 207-222; 225; 252; 263; 278.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CHEN Jiaying, WANG Qingjie,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31; 65-78; 102-109; 110-124; 126-139; 149; 157-161; 163; 166; 174-188; 207-222; 225; 252; 263; 278.]
[25] 梅洛·龐蒂. 知覺現象學[M]. 姜志輝,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2.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JIANG Zhihui,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2.]
[26] 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14-18; 21-25. [CHEN Guying. Zhuangzis Present-day 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4-18; 21-25.]
[27] 王陽明. 傳習錄[M]. 葉圣陶, 點校. 北京: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4: 179-182; 233. [WANG Yangming. Transmits the Record, [M]. YE Shengtao, note. Beijing: Beijing Times Chinese Press, 2014: 179-182; 233.]
[28] 惠能. 壇經[M]. 丁福保, 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 [HUI Neng. Tantras[M]. DING Fubao, note.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6: 6.]
[29]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現象學運動[M]. 王炳文,張金言,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5: 692. [SPIEGELBERG H.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M]. WANG Bingwen, ZHANG Jinya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692.]
[30] 胡塞爾. 笛卡爾沉思與巴黎演講[M]. 張憲, 譯.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87. [HUSSERL E. Descartes Meditating London and Paris Speech[M]. ZHANG Xian, tran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87.]
[31] 馬克思, 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122. [MARX K, ENGELS F. Complete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Vol. 4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122.]
[32] 黑格爾. 小邏輯[M]. 賀麟,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6: 281. [HEGEL G W F. The Logic of Hegel[M]. HE Li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281.]
[33] 楊振之, 謝輝基. 稱手的“知-道”: 旅游研究的知行合一[J]. 旅游學刊, 2017, 32(11): 1-3. [YANG Zhenzhi, XIE Huiji. Discussion forum of China tourism developmeng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1): 1-3.]
[34] ROJEK C. Ways of Escape: Modern Transformations in Leisure and Travel[M]. London: Macmillan, 1993: 78-80.
[35] 馬丁·海德格爾. 演講與論文集[M]. 孫周興, 譯. 上海: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5: 176; 189; 213-215. [HEIDEGGER M. Speech and Proceeding[M]. SUN Zhouxing,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76; 189; 213-215.]
[36] HEIDEGGER M. Holzwege[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4: 268.
[37] 方立天. 佛教“空”義解析[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3(6): 55-60. [FANG Litian. Sunya: An interpretation of a Buddhist concept[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3(6): 55-60.]
[38] 王中江. 道與事物的自然: 老子“道法自然”實義考論[J]. 哲學研究, 2010(8): 37-47. [WANG Zhongjiang. Dao and the spontaneousness of things: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Laozis “Dao emulates what is spontaneously so”[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10(8): 37-47.]
[39] 王永豪. “無己”逍遙、“無功”逍遙和“無名”逍遙——論莊子“逍遙游”思想的三個層面[J]. 社會科學研究, 2007(1): 142-151. [WANG Yonghao. “Selflessness, meritlessness and namelessness”—On Zhuangzi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hought of “the carefree excurs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7(1): 142-151.]
[40] 喬清舉. 王陽明“心外無物”思想的內在義蘊及其展開——以“南鎮觀花”為中心的討論[J]. 哲學研究, 2020(9): 49-58. [QIAO Qingju. On the meaning and further implications of WANG Yangmings “nothing exists beyond the mind”: Re-examining the dialogue “Nanzhen Guanhua”[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20(9): 49-58.]
[41] CHAI A, MONETA A. Retrospectives: Engel cur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 24 (1): 225-240.
[42] 張劍. 《空心人》與T. S. 艾略特的思想發展[J]. 國外文學, 1998(1): 54-57. [ZHANG Jian. The hollow 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 S. Eliots ideas[J]. Foreign Literatures, 1998(1): 54-57.]
[43] 羅洛·梅. 人尋找自己[M]. 馮川, 陳剛, 譯.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1: 4-20. [MAY R. Mans Search for Himself[M]. FENG Chuan, CHEN Gang, trans. Guiyang: Guizhou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1991: 4-20.]
[44] HEIDEGGER M.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M]//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1: 147-150.
[45] 諾伯·舒爾茨. 場所精神: 邁向建筑現象學[M]. 施植明, 譯.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0: 7-8. [NORBERG-SC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M]. SHI Zhiming, trans.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7-8.]
[46] 趙劉. 作為意向性的旅游: 兼論旅游世界的時空構造[J]. 旅游學刊, 2017, 32(4): 18-28. [ZHAO Liu. Tourism as intentionality: The construct of time and space of tourism world[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4): 18-28.]
[47] 孫周興. 語言存在論: 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1: 268. [SUN Zhouxing. Ontology Language: Discussion on Heidegger’s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His Later Life[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1: 268.]
[48] 楊振之, 胡海霞. 關于旅游真實性問題的批判[J]. 旅游學刊, 2011, 26(12): 78-83. [YANG Zhenzhi, HU Haixia. Criticism about tourism authenticity[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2): 78-83.]
[49] COHEN E. 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J]. Sociology, 1979, 13(2): 179-201.
[50] 張驍鳴. 現象學體驗學說及其對旅游體驗研究的啟示[J]. 旅游學刊, 2016, 31(4): 42-50. [ZHANG Xiaoming.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lived experi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n tourist experience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4): 42-50.]
[51] 趙紅梅. 論儀式理論在旅游研究中的應用: 兼評納爾什·格雷本教授的“旅游儀式論”[J]. 旅游學刊, 2007, 22(9): 70-74. [ZHAO Hongmei.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itual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 Comments on “tourism as ritual: 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 by Nelson[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9): 70-74.]
[52] STEINER C, REISINGER Y. Understanding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2): 299-318.
[53] 潘海穎. 休閑與日常生活的反正: 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的獨特維度[J]. 旅游學刊, 2015, 30(6): 119-126. [PAN Haiying. Leisure and everyday life: The special dimensionality of Lefebvres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6): 119-126.]
[54] 康德. 純粹理性批判[M]. 藍公武, 譯.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2011: 82. [KANT I.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 LAN Gongwu,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82.]
[55] 楊振之. 旅游資源開發[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7. [YANG Zhenzhi.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M].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7.]
[56] ROBERTICO C, JORGE R, MATHILDA V N. Connecting quality of life,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mall island destinations: The case of Malt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5: 212-213.
[57] HUANG H L, CHANG M Y, TANG J S, et al. Determinants of the discrepancy in patient-and caregiver-r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persons with dementia[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09, 18(22): 3107-3118.
[58] 禹玉蘭, 譚健烽, 曾偉楠, 等. 幸福感溯源及與生命質量的關系[J]. 醫學與哲學(A), 2015, 36(3): 44-46. [YU Yulan, TAN Jianfeng, ZENG Weinan, et al. On the traceback of well-b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quality of life[J]. Medicine and Philosophy(A), 2015, 36(3): 44-46.]
[59] COSTANZA R, FISHER B, ALI S, et al.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 Ecological Economic, 2007,61(2-3): 267-276.
[60] DIENER E.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M].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9: 1-10.
[61] 邢占軍, 黃立清. 幸福社會: 追求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J]. 理論探討, 2012(6): 25-29. [XING Zhanjun, HUANG Liqing. A happy society: The pursuit of an all-round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12(6): 25-29.]
[62] 焦嵐. 心理生活質量研究: 基于大學生心理生活質量的調查分析[D]. 長春: 吉林大學, 2012. [JIAO Lan. Research on Quality of Mental Life—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of Mental Life[D].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2.]
[63] MASLOW A.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 New York: Harper, 1954: 35-46.
Rethink on the Essence of Tourism
YANG Zhenzhi1,2
(1. Tourism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China Leisure and Tourism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What is the essence of tourism?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tudy its essence,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lead to different essences. Tourism is a meaningful human activity; thus, examining the essence of tourism leads to 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 and existence itself. To examine tourism and the meaning of tourism for human existenc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e tourism itself and also the lifeworld. However,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ourism, is important first to “suspend” the related questions before attaining an accurat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dopts a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ist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essence of tourism. The studay examined the origins, occurrenc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goals of tourism in terms of its occurrence and source dynamics. This study began by suspending the essence of tourism and returning to the lifeworld. By means of reduction, the study observed that previous academics had constructed an inaccurate dualistic world: the lifeworld and the tourism world. However, the tourism world is part of the lifeworld, and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at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ourism demands returning to the lifeworld itself. The study then further suspended the essence of tour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lifeworld. By reduct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Heideggers concept of the lifeworld,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existential and existential mechanism of “care(sorge)”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ource of tourism. The tourist escapes concern and travels to attain what Heidegger called “poetic dwelling”. The existential nature of tourism involves “distancing,” and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ing and poetic dwelling. Essentially, distancing is not a movement in space: it is the nature of humans living in this world. It is through distancing that a person attains poetic dwelling, thereby embracing the real worl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and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is way,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source motivation and essence of tourism; it eluci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ing and poetic dwelling. Following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goal of poetic dwelling—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ourism—is to find one’s true self, though this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ourism, people reveal themselves, gain clarity, achieve self-enlightenment,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personal existenc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 a poetic dwelling model for the tourism world, dividing the goal of tourism into three levels: poetic livelihood, poetic life, and poetic existence. Finally, the study trace the value of tourism, which has transcended tourism itself and is related to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thereby achieving the social value of tourism.
Keywords: essence of tourism; poetic dwelling; care(sorge); distancing; lifeworld
[責任編輯:周小芳;責任校對: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