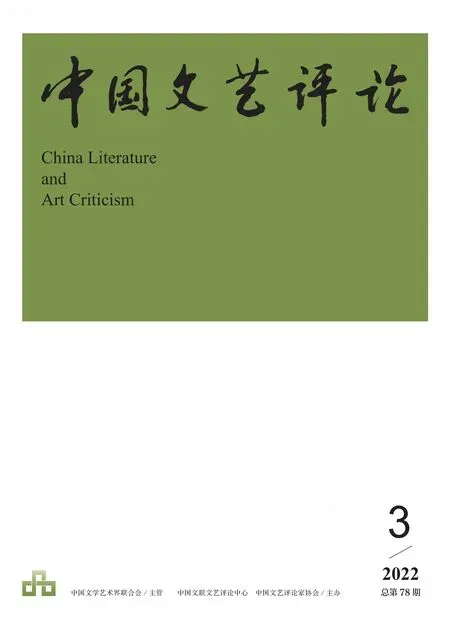如何看待細(xì)節(jié)真實(shí)與個(gè)人經(jīng)驗(yàn)對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的意義?
——周志強(qiáng)現(xiàn)實(shí)主義論的讀解與商榷
■ 閻浩崗
一、讀解
周志強(qiáng)教授近年專注于大眾文化和文化批評(píng)研究。我認(rèn)為他學(xué)術(shù)研究的特點(diǎn)是:選取最日常、最為大眾熟知的文化現(xiàn)象,予以深入的、學(xué)理的分析和詮釋。他能讓你將自己原來懂得的、或原以為自己懂得的東西,變得“不懂”起來;細(xì)思之后,則又恍然大悟,或若有所悟。這與我的路徑和方式恰好形成對比:我在給學(xué)生上課時(shí),總是盡力將一些深?yuàn)W理論簡化、通俗化,變成“精編版”“通俗版”。這也影響到我撰寫學(xué)術(shù)論文的行文風(fēng)格。我這樣做,或許會(huì)損失了理論本身的完整性,是否有曲解誤讀也未可知。但我在這里就準(zhǔn)備用這樣的方式解讀一下周志強(qiáng)現(xiàn)實(shí)主義論的基本觀點(diǎn);而遇到由此引發(fā)的相關(guān)想法乃至不同見解,也寫出來,以就正于志強(qiáng)與讀者方家。
由于志強(qiáng)教授長期關(guān)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與大眾文化現(xiàn)象,他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論有其確定的現(xiàn)實(shí)針對性,就是說,雖然是抽象的理論,但它是由具體的美學(xué)、文學(xué)與文化現(xiàn)象引發(fā)的。筆者以為,它首先針對的是新時(shí)期以來的“純文學(xué)”、形式主義、“新寫實(shí)”、“私人化寫作”等潮流。20世紀(jì)80年代,與文藝?yán)碚撆u(píng)界引入各種形式主義方法及提倡“純文學(xué)”觀念的同時(shí),文學(xué)創(chuàng)作界也出現(xiàn)試圖割斷文學(xué)與歷史及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聯(lián)系的傾向。熱鬧一陣之后,又出現(xiàn)“新寫實(shí)”小說,取材于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糾纏于柴米油鹽的瑣事;題材如此,作者的價(jià)值觀念也認(rèn)同這些瑣碎,并不尋求超越,即認(rèn)同“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的生活態(tài)度。如果說當(dāng)年蕭紅在《后花園》《呼蘭河傳》中寫馮二成子——馮歪嘴子的“活著”時(shí)既有對蒙昧生存的悲憫又包含對生命頑強(qiáng)的贊嘆,余華寫福貴的“活著”、莫言寫上官魯氏的“活著”和生育時(shí)暗寓歷史反思和政治批判,那么,“新寫實(shí)”小說寫小人物的“活著”時(shí)則表現(xiàn)出無奈,以及對社會(huì)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寬容與和解。到了90年代,一些女作家的“私人化寫作”則沿著這一方向向著另一維度發(fā)展,專門將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特別是隱秘體驗(yàn)的瑣細(xì)本體化。“新寫實(shí)”關(guān)注的是創(chuàng)作主體以外的底層生存,“私人化寫作”則以脫離社會(huì)主流的作家個(gè)人為對象。不論是“新寫實(shí)”還是“私人化寫作”,它們都有意與社會(huì)歷史的“宏大敘事”唱對臺(tái)戲,在題材與價(jià)值立場方面對“宏大敘事”予以解構(gòu)和顛覆。志強(qiáng)教授主張超越作家個(gè)人的私人經(jīng)驗(yàn),將揭示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中真實(shí)的社會(huì)矛盾、人的真實(shí)社會(huì)處境和精神困境、文化邏輯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目標(biāo)與最高境界。這樣的文學(xué)雖然也是從具體的人、從個(gè)體生命的具體存在出發(fā),但它并不停留在具體個(gè)人和日常生活真實(shí)上,而要指向“哲學(xué)性的真實(shí)”。筆者認(rèn)為,這與我們以往講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摃r(shí)所謂超越“生活真實(shí)”“細(xì)節(jié)真實(shí)”而追求“藝術(shù)真實(shí)”或“本質(zhì)真實(shí)”、揭示“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意思是相通的。然而,志強(qiáng)教授又特別提醒,他并非主張“樣板文藝”那種“本質(zhì)真實(shí)”,因?yàn)椤皹影逦乃嚒彪m然也超越了作家、藝術(shù)家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高于生活”、不信任個(gè)人的經(jīng)驗(yàn)真實(shí),但“樣板文藝”中超驗(yàn)的“本質(zhì)真實(shí)”是權(quán)威授予,而非個(gè)人得來的,是固化的、千篇一律的,而志強(qiáng)教授強(qiáng)調(diào)要揭示作家尚不熟悉的、無法一語道破的東西,挑戰(zhàn)和突破各種習(xí)見或成見;作家應(yīng)該永遠(yuǎn)處于精神探險(xiǎn)的途中。
二、商榷
在這封信里,恩格斯批評(píng)了哈克奈斯的小說沒有塑造出“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主要是沒有寫出1887年前后的“典型環(huán)境”。因?yàn)閺臅r(shí)代環(huán)境來說,19世紀(jì)末期的英國工人應(yīng)該不同于19世紀(jì)初期,不應(yīng)以消極形象出現(xiàn)。經(jīng)歷過五十多年的無產(chǎn)階級(jí)斗爭之后,工人階級(jí)已起而反抗,這種覺醒和反抗卻沒有在《城市姑娘》中得到反映。恩格斯以巴爾扎克為例,告訴哈克奈斯應(yīng)該怎樣做: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里真實(shí)地、藝術(shù)地寫出了1816到1848年間法國社會(huì)的歷史發(fā)展趨勢,他沒有因?yàn)樽约旱摹巴椤焙驼纹姸鵁o視社會(huì)歷史的實(shí)際狀況。恩格斯將此稱為“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以往筆者在課堂上向?qū)W生闡釋這封信時(shí),將其要點(diǎn)歸納為三點(diǎn):
1.恩格斯肯定細(xì)節(jié)真實(shí)(包括經(jīng)濟(jì)細(xì)節(jié))的重要性;2.恩格斯又特別指出,巴爾扎克式現(xiàn)實(shí)主義與左拉式自然主義的重要區(qū)別,是前者不滿足于細(xì)節(jié)真實(shí)而更重視寫出時(shí)代特點(diǎn)、寫出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趨勢,在典型環(huán)境中塑造典型人物;3.巴爾扎克將忠于客觀現(xiàn)實(shí)與歷史本相置于個(gè)人主觀傾向之上。
三、結(jié)語
總而言之,筆者認(rèn)為,嚴(yán)格意義或原初意義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有其內(nèi)在規(guī)定性:首先是建立在作者和讀者生活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之上的細(xì)節(jié)真實(shí)感。作者因?yàn)榫邆湎嚓P(guān)生活經(jīng)驗(yàn)和高超藝術(shù)技巧而能寫出真實(shí)的細(xì)節(jié),讀者因?yàn)橛蓄愃平?jīng)驗(yàn)或體驗(yàn)而能領(lǐng)略這種真實(shí)、感到其“真實(shí)”,這是原初意義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產(chǎn)生藝術(shù)魅力的前提。其次就是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在為讀者提供細(xì)節(jié)真實(shí)感、因而引發(fā)強(qiáng)烈代入感的基礎(chǔ)上,還要把握生活現(xiàn)象背后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把握生活的邏輯以及社會(huì)歷史的深層真實(shí),給讀者以新的啟發(fā)與領(lǐng)悟;也包括為讀者提供作者自己尚且“不懂”的、難以用理性語言表述的真實(shí),引起讀者新的思考。
文學(xué)史上也有一些作品,雖然作者創(chuàng)作宗旨也在于揭示現(xiàn)實(shí)生活現(xiàn)象背后的“真實(shí)”(即“潛在真實(shí)”)、有強(qiáng)烈的干預(yù)現(xiàn)實(shí)的意識(shí),但它們并不追求描摹酷似日常生活的細(xì)節(jié),甚至故意對生活本相作夸張變形處理、虛構(gòu)離奇情節(jié),例如古典小說《西游記》,以及當(dāng)今被稱作“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或“神實(shí)主義”的小說。對這樣的作品,我們雖也可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但它們并非嚴(yán)格意義或原初意義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對這樣的作品我們?nèi)艄谝袁F(xiàn)實(shí)主義之名,只能是對現(xiàn)實(shí)主義概念的轉(zhuǎn)義借用。如果它們也算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那“現(xiàn)實(shí)主義”真的就成了“無邊”的籮筐,失去其內(nèi)在規(guī)定性了。
- 中國文藝評(píng)論的其它文章
- 審美文化的新動(dòng)向:理論厚積與時(shí)代風(fēng)尚
——“當(dāng)代風(fēng)尚、理論視界與審美文化研究的空間”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 2021話劇:轉(zhuǎn)型之中迎發(fā)展
- 2021藝術(shù)理論:致敬歷史、立足當(dāng)下
- 傳記電影的詩品與哲思
——訪影視導(dǎo)演丁蔭楠 - 中國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團(tuán)體會(huì)員巡禮湖南省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
-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的多重變異、未來性與大眾美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