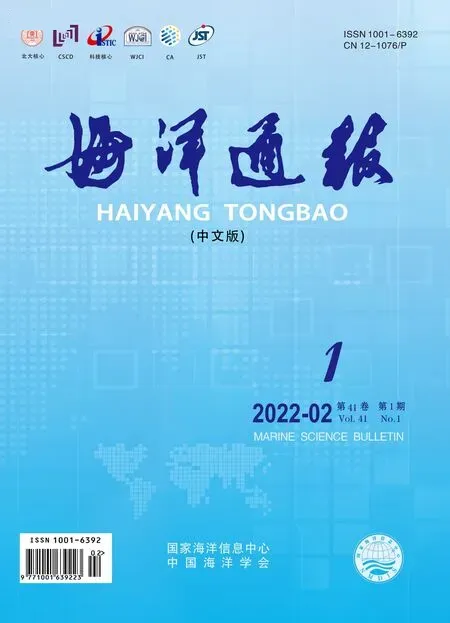中國陸海經濟發展水平及相互作用機制研究
辛欣,姜文達,3,李加林,2,3,田鵬,陳慧霖,楊凱杰
(1.寧波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文化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2.寧波大學 東海研究院,浙江 寧波 315211;3.寧波陸海國土空間利用與治理協同創新中心,浙江 寧波 315211)
陸海產業聯動發展是實現陸海統籌的必要環節[1]。陸海產業具有相互對應關系,二者產業互動、布局交互、資源互補[2],具有高度相互依賴性。陸海經濟間的強關聯性促進了陸域系統與海洋系統之間物質、能量的流動和交換,使得陸海聯系日益緊密:一方面,陸域經濟獲取海洋資源并不斷向海拓展和延伸,帶動海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海洋經濟逐漸成為新的國民經濟增長點[3],通過產業聯動作用促進陸域相關產業發展[4]。要實現陸海統籌發展,就要利用好陸海產業紐帶,以陸海經濟聯動發展為核心,調配系統內要素流動,治理與防控并行,全面協調陸海兩系統可持續發展。在此背景下對陸海經濟關聯性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陸海經濟關聯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陸海經濟協同發展、陸海產業關聯性和海洋經濟對區域/陸域經濟的帶動作用等方面。在陸海經濟協同發展方面,從陸海兩系統耦合度視角分別選取陸域和海洋經濟評價指標,測算其耦合協調程度[5-7],強調發揮沿海地區陸域與海洋的綜合協調優勢,實現陸海一體化發展。在陸海產業關聯性方面,通過灰色關聯分析[8-10]、投入產出分析[11]、相關分析[12]、格蘭杰因果檢驗[13]等方法,定量研究海洋經濟與國民經濟、陸域經濟之間的關聯效應,結果均證實了二者的關聯性,尤其是以漁業為主的海洋第一產業和以食品加工和化學行業為主的陸域第二產業、以濱海旅游為主的海洋第三產業和陸域第三產業之間高度關聯[14]。以此為基礎,學者對陸海產業鏈的整合路徑進行深入研究,提出推進陸海產業鏈整合是實現陸海統籌發展的有效途徑[15]。在海洋經濟對區域/陸域經濟的帶動作用方面,貢獻率分析[16]方法被廣泛運用,目前我國海洋產業由第三產業主導[17],其中以海洋運輸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三產業對地區/陸域經濟推動作用最為顯著。港口也因其在沿海經濟空間的重要地位而受到關注,學者從港口—腹地視角分析其經濟關聯[18]與空間關系[19]。綜上,對陸海經濟關聯性的研究雖大量開展,但均呈現出靜態、無向性特征,其具體、動態的陸海經濟交互影響過程并未被揭示,相互作用機制尚未明晰。故探究陸海產業相互作用機制的研究工作亟待進一步豐富和加強。
目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與海洋經濟相比,陸域經濟起步更早,在陸海經濟一體化發展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20]。在此背景下,推動陸海聯動,實現以陸促海、以海帶陸、陸海互助的陸海一體化發展,應明晰陸海產業相互作用機制。研究基于中國沿海地區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的領先地位,以中國沿海11 省區市為例,揭示了2006—2017 年中國沿海地區的陸海經濟發展現狀,運用地理探測器分析陸海產業相互影響過程,探討了陸海產業相互作用機制,以期為陸海聯動發展研究提供新視角,促進陸海統籌發展。
1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熵權法 熵權法通過測定指標的信息熵值來判斷該指標的離散程度[21],其信息熵值越小,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綜合評價影響程度越大,其權重越大。具體計算步驟如下所示:
(1)原始數據矩陣標準化。設m 個評價對象,n 個評價指標構成的原始數據矩陣為:

根據所選指標的不同性質,對正向、逆向指標分別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

逆向指標:

原始數據標準化后得到矩陣R=(rij)m×n,式中rij為第i 個評價對象在第j 個評價指標的標準值。
(2)計算信息熵值ej。計算公式為:

(3)計算權重wj。計算公式為:


1.1.2 核密度估計 核密度估計是一種非參數檢驗方法,用于估計未知的密度函數,不需要通過先驗知識對數據分布進行假定[22-23]。與參數估計方法相比,核密度估計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減小了參數模型對結果的影響,僅從數據本身出發分析數據分布,可以直接利用數據對概率密度進行估計。此外,核密度估計方法常被用于描述經濟分布運動,可以保留轉移概率矩陣時所破壞的原始連續動態信息。該方法基本原理及計算公式參見孫才志等的論文[23]。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分別繪制陸域和海洋經濟水平綜合值核密度曲線,通過對不同時期陸域和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分布曲線位置、形狀、峰值等變化趨勢分析陸海經濟發展動態演變過程。
1.1.3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探測空間分異性并揭示其背后驅動力的統計學方法,其基本假設為:如果一組自變量對因變量產生較大影響,那么二者空間分布應具有趨同性[24]。地理探測器共包含分異及因子探測、交互作用探測、風險區探測、生態探測四個探測器,其中因子探測可以探測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力[25],用q 值度量,表達式為:
1.2 數據來源與研究對象說明
將陸域和海洋視為兩個獨立的系統,分別選取指標建立綜合指標體系,用于評價陸海經濟發展水平。基于產業關聯視角,分別選取陸域和海洋生產總值及三次產業產值,用于陸海經濟相互作用力分析,其中陸域數據由區域數據減海洋數據所得。所用數據皆來源于2007—2018 年《中國海洋統計年鑒》及沿海各省區市2007—2018 年統計年鑒。
研究區域選取中國沿海11 省區市,據《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三大海洋經濟圈戰略格局。以此為依據,研究將沿海省區市分為三大經濟圈:北部經濟圈,即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山東省;東部經濟圈,即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南部經濟圈,即福建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
2 陸海經濟發展水平
2.1 指標選取
根據已有研究[26]分別從發展規模、產業結構、經濟質量3 方面選取海洋經濟指標8 個、陸域經濟指標8 個。運用spss 26 進行可靠性分析,結果顯示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 均大于0.7,表明陸海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具有可靠性。運用熵權法分別計算沿海省區市指標權重,最終權重取其平均。具體建立指標體系和對應指標權重如表1。

表1 陸海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2.2 陸海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特征
2006—2017 年海洋和陸域經濟發展水平(表2、表3)均呈上升趨勢。海洋經濟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波動變化階段(2006—2009 年)和快速增長階段(2009—2017 年)。究其原因,在2009—2010 年,各省區市在沿海港口外貿吞吐量、人均海洋生產總值、旅游外匯收入、海洋科研經費投入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在2006—2009年,除天津市、江蘇省外,其他沿海省區市的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值基本在0.3 以下;在2009—2017 年,各省區市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迅速:其中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均得到快速發展;遼寧省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則在2015—2016 年有所下降,在2017 年回升,二者海洋科研經費投入在此期間均有下降;海南省則在2012—2014 年呈下降態勢,在此期間,其非農產業占比、三次、二次產業比及旅游外匯收入均有下降。天津市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在整個研究期內呈上升趨勢,2010—2011 年和2015—2016 年稍有下降;江蘇省在2006—2009 年逐年降低,2009—2015 年呈增長態勢,2015—2016 年稍有下降,2017 年回升。江蘇省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在沿海省區市中較落后,相較于其他沿海省區市,江蘇省8個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指標均不占優勢,其中海洋人均生產總值、三次、二次產業占比排名末位。

表2 海洋經濟發展水平

表3 陸域經濟發展水平
陸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海洋經濟發展更穩定,整體均呈快速增長態勢:其中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蘇省、廣東省、海南省在2006—2017 年得到快速發展;遼寧省在2013—2016 年下降,在此期間,其進出口總額逐年減小,2017 年有所回升;2006—2009 年浙江省在0.2 左右波動變化,2009—2010 年迅速增長,其陸域經濟發展規模在此期間增長迅速,2011—2012 年陸域經濟發展水平下降,陸域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和實際利用外資情況在此期間有所下降,2012—2017 年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升;福建省僅在2007—2008 年有所下降,此間其陸域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和實際利用外資情況下降;山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均在2009年出現極小值;此外,廣西壯族自治區在2016 年也出現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極小值。
2.3 陸海經濟發展動態演化分析
應用Eviews 8.0 軟件分別對陸域和海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核密度估計,通過對沿海地區陸海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特征梳理,選取具有代表性的2006年、2009 年、2012 年、2014 年、2017 年五個年份數據繪制核密度曲線。
沿海區域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分布密度曲線如圖1 所示。位置上,右移態勢明顯,說明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有良好發展態勢。形狀上,曲線整體跨度在2012 年、2014 年縮小,在2017 年明顯增大,說明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經歷了先減小后增大的發展過程。峰值變化上,2006年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集中在0.2 左右的低值區域,此時曲線呈現右拖尾。2009 年核密度曲線呈現尖峰形態,尖峰峰值位于0.25 左右,左部出現小波峰,峰值集中在0.1,右部拖尾位置未變,但是集中在該值的核密度值增加,說明2006—2009 年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經歷緩慢增長階段。2012 年核密度曲線仍呈現尖峰形態,但較2009 年曲線形態稍寬,尖峰峰值位于0.5,右拖尾徹底消失,左部小波峰剝離為兩個,峰值分別集中在0.3 和0.4,說明2009—2012 年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水平快速增長,整體由較低水平增長至中等水平,但同時,沿海地區海洋經濟呈現差異化發展。2014 年核密度曲線呈明顯尖峰、雙峰形態,較高水平峰值集中在0.65,較低水平峰值集中在0.45,說明此時沿海地區海洋經濟發展形成明顯差異,且二者皆呈正向發展態勢。2017 年核密度曲線呈寬峰形態,峰值再次右移,集中在0.8,左部小波峰消失,呈現拖尾形態,表明此時沿海地區整體集中于較高值,少數省區市仍處于中等發展水平。

圖1 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核密度分布
沿海地區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分布密度曲線如圖2 所示。位置上,明顯右移的態勢說明沿海地區陸域經濟水平在2006—2007 年發展迅速。形狀上,曲線整體跨度在2012 年達最大值,其后又減小,說明沿海地區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化經歷了先增大后減小的過程。峰值變化上,2006 年核密度曲線呈明顯尖峰形態,尖峰峰值集中于0.1;2009 年核密度曲線波峰開始出現層次剝離,隱有單峰向雙峰轉變的態勢,峰值集中于0.3;2012 年核密度曲線呈寬峰形態,峰值集中在0.5,左部和右部均分別向外部擴張,說明2006—2012 年沿海地區陸域經濟由較低水平提升至中等發展水平,且差異化發展趨勢逐漸增大。2014 年核密度曲線呈現寬峰形態,且波峰分化為兩個,峰值分別集中在0.6 和0.7,左部和右部向外延伸趨勢消失,說明此時沿海地區陸域經濟發展水平均集中于中高水平,差異化明顯。2017 年核密度曲線呈明顯尖峰、雙峰形態,較高水平峰值集中于0.9,較低水平峰值集中于0.7,說明此時沿海地區陸域經濟發展整體集中于較高水平,且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已形成明顯差異化發展。

圖2 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核密度分布
綜上,沿海地區陸海經濟均呈正向發展態勢,但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核密度曲線右移態勢大于海洋經濟發展水平核密度曲線,即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正向發展態勢超過海洋。陸域經濟集中在較高發展水平,海洋經濟集中在中高發展水平,且有少數省區市仍處于中等發展水平。
3 陸海經濟相互作用過程
由于地理探測器原理為空間分異,并不能詮釋其在統計意義上的相關性,故運用spss 26 軟件分別對陸域和海洋生產總產值、人均生產總值及三次產業之間相關性進行檢驗,發現陸海經濟數據均在0.01 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其在統計意義上具有相關性,可對其相互作用過程進一步研究。
3.1 陸海經濟相互作用
分別選取陸域和海洋人均生產總值,運用地理探測器探測陸海經濟間相互作用力(圖3),二者相互影響程度呈減小趨勢,其中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的作用力下降趨勢明顯,2010 年降至最低值,2011 年起有所回升但僅保持在0.5 左右;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的作用力則相對穩定,一直在0.5~0.7 之間波動。從2009 年開始,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的影響程度逐漸超過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的影響程度。

圖3 陸海人均生產總值相互作用探測q 值
3.2 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的具體作用
從陸域三次產業來看(圖4),對海洋經濟作用力最大的是陸域第一產業,其次是陸域第二產業和陸域第三產業,但三者的q 值均處于較低水平,說明陸域三次產業與海洋經濟的空間分異并不趨同。為研究陸域產業分別對海洋三次產業的影響,選取作用力前五列表(表4),表頭中短線前為被作用因子,短線后為作用因子,以“海一—陸一”為例,即陸域第一產業對海洋第一產業的作用力。陸域第一產業對海洋第一產業單向作用力較強。陸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對海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交叉作用強烈,且其作用力皆呈上升趨勢,說明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的帶動效應增強,其中:陸域第二產業對海洋第二產業的作用力最大,且呈波動增加態勢,即陸域第二產業易與海洋第二產業形成產業聯動;陸域第二產業對海洋第三產業的作用力在2014 年前呈較平穩增長,2014 年后有所回落;陸域第三產業對海洋第二產業的作用力在2006—2012 年呈現快速增長,2015 年后有所下降;陸域第三產業對海洋第三產業的作用力則在2008—2010 年下降后,在2010—2012 年快速回升并保持平穩;即除陸域第三產業對海洋第三產業外,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影響幾乎沒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擾動,說明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作用過程穩定,不易受外部金融環境影響。

圖4 陸域產業對海洋經濟影響探測q 值

表4 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的影響探測q 值
從空間上看(圖5a),南部經濟圈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的影響最強,其次為北部經濟圈,東部經濟圈最弱。在北部和南部經濟圈,陸域第二、第三產業對海洋經濟影響較強;在東部經濟圈,陸域第一、第二產業具有更強影響。從三次產業看,陸域產業對海洋第一產業影響最強的是東部經濟圈,其次為北部經濟圈,南部經濟圈最弱(圖5b);對海洋第二產業影響最強的是南部經濟圈,其次為北部經濟圈和東部經濟圈(圖5c);對海洋第三產業影響最強的是南部經濟圈,東部經濟圈最弱(圖5d)。北部經濟圈陸域產業對海洋三次產業均具有較強影響,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帶動作用良好;東部經濟圈陸域產業尤其是陸域第三產業對海洋第三產業影響較弱,陸域產業發展更能帶動海洋第一、第二產業發展;南部經濟圈陸域產業對海洋第一產業影響較弱,對海洋第二、第三產業帶動作用較強。

圖5 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空間上影響探測q 值
3.3 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的具體作用
從海洋三次產業來看(圖6),對陸域經濟作用力較大的是海洋第二和第三產業,2010 年,海洋第二產業對陸域經濟作用力迅速增加,并在2010—2013 年保持較高水平,2014 年回落;第三產業對陸域經濟作用力基本保持波動穩定,海洋第一產業作用相對較弱,說明海洋第二、第三產業易與陸域經濟形成產業聯動。探測海洋產業分別對陸域三次產業的影響,仍選作用力前五列表(表5),表頭命名方式同表4。從三次產業分別來看,海洋第二和第一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作用力較大,海洋第二和第三產業分別對陸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生較強影響,其作用力均在2014—2017 年基本保持波動穩定。具體來看,2007 年后,海洋第二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作用力大于海洋第一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作用力。事實上,自2014 年開始,海洋第三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的作用力也逐漸超過海洋第一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的作用力,說明海洋第一產業受生態環境限制,經濟帶動作用逐漸衰退,海洋第二、第三產業與陸域第一產業形成一定產業聯動。海洋產業對陸域第三產業作用力較大:海洋第二產業對陸域第三產業作用力在2007 年經歷低谷后回升,2008—2009 年又有所下降后再次回升,并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海洋第三產業對陸域第三產業作用力在2008—2010 年經歷下滑后在2011 年回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海洋第二產業對陸域第二產業作用力在2006—2008 年波動變化后下降,在2014 年回升;海洋第三產業對陸域第二產業作用力在2008—2009 年迅速下降,后在2011 年和2014 年分兩次回升,但依舊低于海洋第三產業對陸域第二產業作用力。總體而言,海洋產業對陸域產業作用過程易受外部金融環境影響。

圖6 海洋產業對陸域經濟影響探測q 值

表5 海洋產業對陸域產業的影響探測q 值
從空間上看(圖7a),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影響最強的是北部經濟區,其次為南部經濟區,東部經濟區最弱。在南部經濟區,海洋第二和第三產業對陸域經濟影響強烈;在北部經濟區,海洋三次產業對陸域經濟均有較強影響,其排序為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在東部經濟區,海洋第一和第二產業對陸域經濟具有較強影響。分三次產業來看,北部經濟圈海洋產業對陸域第一產業影響最強,其次為南部經濟圈和東部經濟圈(圖7b);北部和南部經濟圈海洋產業對陸域第二產業影響最強,東部經濟圈最弱(圖7c);北部經濟圈海洋產業對陸域第三產業影響最強,其次為南部經濟圈和東部經濟圈(圖7d)。北部經濟圈海洋產業對陸域三產業均具有較強影響,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帶動作用良好;東部經濟區陸域第三產業對海洋產業影響均處于較弱水平;南部經濟圈海洋第一產業對陸域三次產業影響均處于較弱水平。

圖7 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空間上影響探測q 值
北部經濟圈陸海產業互動良好,其以山東“藍色糧倉”作為第一產業發展優勢,用臨近工業基地夯實其第二產業發展基礎,用大連、日照等海洋旅游城市與大連港、丹東港等港口建設開拓第三產業快速發展路徑,故其陸海產業形成良好聯動,海洋產業對陸域產業影響甚至強于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影響;東部經濟區海洋第三產業與陸域產業未能形成良好互動,東部經濟區海洋第三產業以海洋運輸業為主導,擁有寧波舟山港、上海港等優越港口,但是相比較北部、南部經濟圈,缺乏知名海洋旅游城市。海洋運輸業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旅游產業更易與陸域產業形成互動;南部經濟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陸域第二、第三產業和海洋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迅速,互動良好。
4 陸海經濟相互作用機制
陸海經濟相互作用力呈減小態勢,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影響逐漸超過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的影響。但是從三次產業看,陸海產業相互作用力呈波動穩定或增加態勢,且陸域產業對海洋產業作用增長態勢大于海洋產業對陸域產業作用增長態勢。說明我國海洋經濟正逐漸由陸域經濟的附屬地位發展為具有健全產業結構的獨立經濟體系,但是其對陸域經濟輻射帶動作用仍小于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帶動效應。從三次產業看,海洋第二和第三產業與陸域第二和第三產業兩兩交互作用強烈,陸域產業對海洋第二產業影響較強,海洋產業對陸域第三產業影響較強,形成以海洋第三產業和陸域第二、第三產業為核心的產業關聯機制。
為分析陸海產業的相互作用機制,大致可將其分為三類:資源交換型、產業鏈型和動態互助型。整體而言,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帶動作用強烈,且不易受外部環境干擾,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起促進作用,容易受到生態、資源、金融等外部環境干擾作用。從陸海經濟內部產業聯動來看,已經形成以海洋第三產業和陸域第二、第三產業為核心的作用機制。首先,資源交換型是指當陸海產業發展資源互補時,陸海產業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而形成良好互動的作用機制。例如,以油氣業、礦業、鹽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二產業為陸域第二產業的發展提供資源,但同時海洋第二產業也需要借助陸域空間進行生產活動。其次,產業鏈型是指陸海產業通過生產要素流動和交換形成完整產業鏈條以促進產業互動發展。如海洋第一產業與陸域第二、第三產業通過海洋漁業資源流動形成“海水養殖—海洋水產品深加工—海洋食品與藥物銷售”產業鏈[2];陸域和海洋第二、第三產業通過生產要素的交換形成“船舶工業—交通運輸”產業鏈,陸域第二產業為船舶工業提供必要生產零件、生產空間,船舶工業為交通運輸業提供生產資料。最后,動態互助型是指陸海產業聯系緊密,互聯互關的作用機制。以陸域旅游業為代表的陸域第三產業和以海洋旅游業為代表的海洋第三產業為例,陸域和海洋交互作用共同賦予沿海地區特殊的旅游資源,雙向帶動沿海地區旅游業的發展,呈現動態互助作用機制。
資源交換型是在陸海產業置換其原有資源條件下產生的,該作用機制下陸海產業發展受資源環境限制較大,而產業鏈型則是由生產要素在陸海產業形成流動,加之技術、資金等要素共同構成,其關系網絡更復雜也更穩定,動態互助型則是陸海共享資源形成無明確分界的產業聯系,二者一榮俱榮,緊密相連。對應三種作用機制,應優先注重陸海產業產業鏈式發展,但是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陸海產業交互不僅遵循單一的相互作用機制,三種機制共同影響陸海產業聯動發展過程。要推動陸海聯動,應在可持續發展前提下合理調配陸海資源,優化陸海產業布局,整合陸海產業鏈,推動形成具有陸海完整產業鏈條的沿海產業集群,打造特色產業,加速形成陸海互助的陸海一體化發展。如北部經濟圈陸海產業結構正處于快速高度化進程中,應充分利用其海洋產業帶動效應優勢,在原有工業基地發展基礎上,促進以海洋旅游和海洋交通運輸為代表的第三產業與陸域產業相互關聯;東部經濟圈則繼續發揮其港口優勢,以港口作為陸海產業重要接口,深化陸海產業互動;南部經濟圈則發揮其海洋旅游特色產業優勢,雙向帶動陸海產業,動態互助。
5 結論
(1)我國沿海地區陸海經濟發展整體呈正向發展態勢,2006—2017 年海洋經濟經歷了從波動緩慢發展到快速發展的轉變,陸域經濟則一直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陸海經濟均呈現差異化發展,但海洋經濟發展水平仍落后于陸域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沿海區域海洋經濟發展整體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2)陸域經濟對海洋經濟影響仍強于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影響,且海洋經濟對陸域經濟的影響易受外部環境影響,故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仍應將重心放在陸域經濟發展,以維持本國經濟發展穩定性。
(3) 北部經濟圈陸海經濟相互影響作用最強烈,南部經濟圈其次,東部經濟圈最弱。總體而言,三大經濟圈陸海產業發展各有側重,經濟發展正向態勢良好,應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讓不同省區市/經濟圈發揮其各自職能,加強其經濟輻射效應,帶動內陸區域經濟發展。
(4)陸海產業形成了以海洋第三產業和陸域第二、第三產業為核心的三種作用機制:資源交換型、產業鏈型、動態互助型。在陸海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把握其作用機制,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優化陸海產業布局,促進陸海產業鏈整合優化,實現陸海產業深度融合,動態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