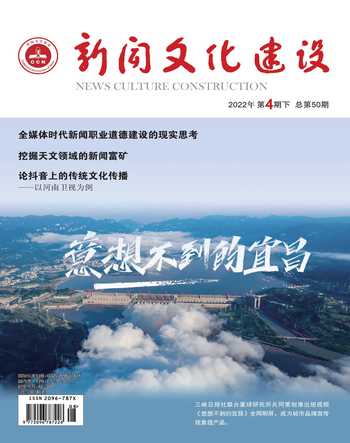社會化媒介視域下女性主體意識的新構建
王逸
摘要:隨著社會化媒體的發展,在不斷推動信息傳播與社交互動緊密聯系的同時,也影響并改變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女性這一主體在廣泛的社交媒體應用下,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然而,我們在媒介輿論中還是會發現,與“女性”有關的話題在社會認知中仍有成見存在。本文結合李普曼《公眾輿論》的“刻板成見”概念,從傳統語境中的“他者”觀點著手,結合社會化媒體時代下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與困境,探析社會化視域下的“她者”重塑路徑。
關鍵詞:社會化媒體;刻板成見;女性主體意識
在移動網絡人群使用規模日益增長和“社交”趨勢推動下,社會化媒體成為我們社會交往、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以更加廣泛的力量滲入生活的點滴,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左右著人們對最終決定的判斷。據顯示,全球互聯網市場上,超過75%的活躍網民使用社交網絡,而女性群體則占據主要地位。隨著社會現實處境的轉變、人們話語權利的平等構建,以及“性別建構主義”思潮的盛行,女性逐漸走向社會舞臺中心。在社會化媒介所創造和傳遞的海量信息中,女性群體也占據有相當可觀的信息空間,但是在總結這些信息后我們發現,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并未完全擺脫“成見”的命運。因此,要正確地引導社會化媒介中女性主體意識的新構建。
一、傳統固化下的“她者”成見
(一)歷史中女性的“他者”語境
《公眾輿論》一書中提道:“成見是投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自身的意識、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念、我們自身的立場和我們自身的權利,成見充滿了被它們所吸納的情感。[1]”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存在,會被身邊的各種環境、文化因素所影響,自己的價值理念、習慣等都會在潛移默化中被改變。因此,我們在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理解過程中,往往會按照一種我們所既定的方式和情感去理解,也逐漸導致人們會對事實的理解產生一種認知偏差,即“成見”。
在我們不同的文化范疇中都存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社會性別文化,取決于兩性間的本質區別,并在社會制度、宗教以及傳統文化的長期影響下,形成了男女之間行為方式、社會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女性逐漸變成“他者”,即波伏娃所說的“第二性”。這種文化大都不約而同地宣稱“男女天生是不平等的”。也就導致了傳統歷史中的兩性關系和地位的差異,從而逐漸形成“他者”語境。
(二)傳統媒介中女性的“自我客體化”
隨著科學技術一次又一次地打破常規,我們社會實現了飛躍發展。人們開始追求思想自由,努力尋找新的價值觀念、渴望社會平等,但因為“世界早在我們觀察之前就已經被告知它究竟是什么樣了”,在先入之見的支配下,“她們”依舊被壓抑和束縛著。即使從20世紀開始,女性在大眾傳播中所占比例和地位有所提升,但“她”仍舊是“局外人”。
傳統大眾媒介作為意識形態生產的重要渠道,通過文字描述、界定以及建構權力影像等方式為人們塑造了世界形態。回顧其中的女性形象。會發現女性角色依然處于被成見的狀態,它以隱蔽的方式維護著“他者”,甚至加深了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當這種性別分工造就的刻板印象進入創作領域,人們無意識地就會將傳統觀念中所附加在女性身上的社會性別特征模式化。詩人彌爾頓曾說,女性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展現溫柔與甜美的迷人風采,如“女性向”文學無法逃脫的“情”。
傳統媒介與消費主義所傳遞的“符號”價值合謀,為了迎合大眾心理的“窺視欲”,卻忽視了女性主體意識的感受。讓人把身體視為自我表達的工具,使女性在“看和被看、評價和被評價”的關系中夾縫生存,用“最美”等字眼把女性標簽化。從這一點來看,在“他者”語境與文化工業話語的雙重裹挾和壓迫之下,大眾傳媒中的女性形象被異化,依舊當作“被看”對象,女性的主體意識也逐漸客體化。媒介通過不平等的話語邏輯來深化女性的集體無意識,即便媒體中并不缺女性,但她們也是“沒有主見的、不能夠發出聲音的、是被遺忘的”。
二、社會化媒體時代女性主體意識的重構
(一)社交傳播賦權,重構女性話語空間
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所帶來的傳播賦權,“她們”重新進入公共領域的性別話語角逐。以女性話題為主的媒體報道頻繁占據熱搜榜單,挑戰被傳統大眾媒介長期把持的話語權力,為女性主體構建著新的性別話語權。同時,社會化媒介自身所具有的交互性和“受眾本位”,使女性在公眾領域的“發聲”有了一種更具有包容性的選擇,為女性主體搭建起一個可見但又不脫離一般公共領域的話語空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社交網絡得以極速拓展,社會化媒體中借助議論圈子,聚合醫護工作者的形象和故事,其間涌現出了大量以女醫護人員為主角的新聞報道,不僅推動了女性醫護工作者的形象構建,更推動與以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主流話語展開協商。對公眾輿論產生巨大影響,也創造出“女性賦能”等替代性話語框架。一時間以高度情感性的召喚,在共情、互助與團結的基礎上構建起想象與行動的共同體。
社交平臺上的播客們也正在通過美妝、穿搭等不同主題分享,通過親身展演并打造新的自我審美定義,借助社會化媒介的可見表征以及自主能動性從而進入公共領域。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女性是如何創造性地運用數字媒體技術,尤其是個性化的、移動的、可以跨越時空等各種界限組合成群的技術,來傳遞信息、分享經驗、營造社群、發起話語行動,重構“她們”與公共空間的關系。在不斷的話語交換中把女性議題和性別視角推出圈層之外,對主流媒體和社會大眾產生影響。
(二)社會化圈層交流,傳遞“她者”意識
如今,社交網絡成為人們學習、生活必不可少的平臺。社會化媒介在革新人際交往互動方式的同時,也為人們在網絡交互中形成社交圈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不同的群體以興趣、價值或情感紐帶構建起了各式圈層,女性群體也用自身的經驗,在不同的圈層交流中不斷地進行自我審視和重構。并努力追求最終內化穩定為個體能動性訴求,并借此來抵抗傳統“他者”語境下的客體化屬性。伴隨“她意識”的覺醒及女性社會價值的提升,更多的女性敢于從自身立場出發,以一種不可回避的姿態,大膽宣揚自身的主體欲望。[2]社會化媒介的圈層的集聚,不僅拓展了女性群體交流的渠道,也為“她者”意識的傳遞提供了更多討論空間。
女性主體意識作為一種精神而存在著獨立的可能性,同時也展現著一種詩意政治想象與建構。她們不斷地積累力量以對抗傳統世界對女性的束縛和壓抑,開始把目光投向社會舞臺,在社會化傳播與交流中傳遞“她者”意識。不僅在社交媒體中表達,也在諸多影視劇的創作中有所展現。影片《離經叛道》的女主角身為猶太人,在那個年代生來就被教法束縛,而且其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傳宗接代。但她不甘于此,于是瘋狂地逃離。即使再艱難也無所畏懼,因為她找到了自我。影片用插敘的手法,原始又具有沖擊力的鏡頭語言為我們講述一段轟轟烈烈的自我追逐,活靈活現地為我們演繹女性對自我價值的發現和展望,更讓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中女性理應擁有的權利。
隨著女性主體意識的崛起,讓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這些傳統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男強女弱”的集體無意識。《三十而已》《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等作品的走紅,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優質女性題材電影稀缺的狀態,也讓大家看到女性題材的更多可能。在“她經濟”逐漸占據主流的當下,對于女性更多的發聲讓“她們”重新開口敘述她們的生活,這有助于社會大眾用自主選擇性的方式與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他者”中心社會的話語權力關系,也為女性重建其主體性創造了更多可能。
三、社會化媒介影響下女性主體意識崛起的困境
社會化媒介所賦予每個人的自由表達權,讓網絡空間言論高度個體化,助力不同圈層的融合、也賦予了不同價值追求的人得以施展的空間。社會化媒體對女性主體意識重新建構所帶來的影響利大于弊,但它所顯現出的困境也不容忽視。
一方面是受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對當下女性行為認知的失范。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說:“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以典型反轉新聞“重慶公交墜江事件”為例。在事故發生后,一條“此次事故是由一名穿高跟鞋開車的女司機逆向行駛所造成的”消息開始刷屏,并且還配上了女司機的照片和視頻,由于“據說”是根據重慶市萬州區政府所傳出的消息而顯得“有理有據”,一時間媒體紛紛轉載,這也導致女司機被無情人肉,被無數網友謾罵。“女司機”這一群體又一次陷入輿論旋渦,成為被公眾指責的對象。本應放在第一位的怎樣及時救援、如何安撫受害者家屬等消息統統被忽略。這傷害的不僅是受害者家屬,還有無辜的社會大眾。為了求快而放棄本應堅持的真實性,放大未經證實的片面消息,靠夸張標題亂人眼球,把女性群體擺在了風口浪尖。網絡上人們紛紛指責女司機的言論,“女性就不應該開車”等字眼甚囂塵上。這些先入為主的下定義,讓人們在遇到問題時,大多數都會先以所屬文化的心理、習慣去認知、理解對象。即使觀察、認識、理解必然具有文化偏向性,又或者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成見,但仍無法超脫。因為除了成見,一個人的裸眼是看不到什么的,只是一些直觀的影像。[3]
另一方面是隱蔽力量的規訓,深入內化在女性的自我認知中。社會化媒體基于互聯網絡,將一個個孤立的“點”鏈接并拓展成一個個“面”,其影響力幾乎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社會化媒體使大家得以超越物理意義上的分隔,可以時刻參與娛樂化的社交生活。但無處不在的定義依舊侵蝕著我們。在社交平臺上,我們更熱衷于塑造精致的形象,分享生活的美好,借助大家的點贊評論來獲得自我的滿足。盡管女性開始積極參與及表達自我審美的觀點,也構建了新的討論渠道和建制標準。但以抖音平臺為例,不少女性所創作的視頻評論區下依舊充斥著對其顏值、身材評頭論足的話語,甚至不少女性也參與其中。雖然社會化媒介的交流互動重新改寫了對女性群體“美”的定義與標準,但在長期審美觀念的灌輸中,人們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種審美觀。權力主體隱藏在廣告、影視劇的身后,長期以來影響人們的審美觀,從而也形成了某種程度上對于審美隱秘的規訓。在社會化媒介時代,這種隱蔽的力量并未消亡,反而更加凸顯。
四、社會化傳播中女性主體意識重構路徑的探索
在社會化媒體交互、公開特性的影響下,女性主體意識的構建呈現出形象多樣、主題多元、制度建構等多種新態勢。“她”既想擺脫封建傳統“成見”束縛,但也有著時代快速更迭下的困惑。因此,其在提升女性主體意識的同時,也對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帶來不小挑戰,各方應引起重視。
(一)打破成見藩籬,增強女性主體意識
社會化媒介作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個更加包容的世界里,眾聲嘈雜也賦予了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的可能性。從女性話題的關注程度來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固有認知中的不合理性,傳播者也逐漸對女性主義者的訴求進行回應。逐漸打破社會化媒介特性所造成的女性議題的圈層化,讓主體下沉去影響更多的女性,改變大眾傳播所固有的思維模式,讓女性主體意識加入其中,推動新聞報道和藝術創作重新塑造女性形象,從更廣的社會層面增強女性的主體意識。由于社會的某些既定設置,讓我們習慣性地對不曾了解的事物按照自己所熟悉的想象定義做出判斷。其實,在這個多元、自由的現代化社會中,我們每個人心中應該形成自己的“成見庫”。在各自所遵循的生活哲學的樣板里,通過不斷學習和深入了解而不斷創新這個“成見庫”,讓自己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打破傳統女性成見,建立清醒的自我主體認知,推動兩性地位平等共建,避免陷入沉默螺旋和“集體無意識”的旋渦。
(二)提升媒介素養,樹立正確價值取向
在不同文化和社會秩序相互交織的當下,女性主體意識的新構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者”語境中人們的新期盼。而同時由于自身活動范圍受限,大家也無法洞察外部整體環境中的所有事物,只能通過傳播媒介去了解自己能力范圍之外的事物。在后真相時代,媒體的規范性報道顯得尤為重要。發表之前先去尋找信息來源,并進行求證,不明事情真相,就不要一味追求時效性。那些未經證實的一定要標注清楚,避免誤導公眾。
對于未經求證就盲目發表并夸大事實的新聞媒體要加以管控,建立更加嚴格的監督管理機制。社會化媒介時代的到來,使人們之間的信息交流更加頻繁。作為媒介工作者要加強責任意識,提高自身素養。不再主觀臆斷、刻板印象定位性別意識,只做客觀的敘事者。要提升對女性主體的認知敏感度。在某些具體的輿論事件中容易產生社會性別意識的盲點,以及傳統性別刻板成見的隱蔽性特點,媒體工作者更要打破這種成見觀,走出“他者”狀態,通過媒介來塑造更加客觀真實且立體多元的女性形象。
五、結語
在社會化媒介視域下,社交網絡的發展為女性賦能,積極推動“她們”走入輿論場,為女性主體搭建起了新的話語空間,構建起新的“她者”意識溝通圈層。但在交互性、時效性等特性影響下,社會對于女性的成見、規訓依舊存在。基于此,我們在這個全民社交化時代,理智的發聲顯得更加重要。用更加客觀的敘事和人文關懷,為女性重筑話語空間,推動女性主體從話語權邊緣深入中心世界,激發女性內在學識與能力的展現。讓“她們”在不斷的積累、沉淀中綻放屬于自己的絢爛色彩,成為獨立的“她者”。
參考文獻:
[1] [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曾麗紅,葉丹盈,李萍.社會化媒介賦權語境下女性“能動”的“可見性”:兼對B站美妝視頻社區的“可供性”考察[J].新聞記者,2021(9):86-96.
[3] 楊保軍.搖擺不定的李普曼:讀《公眾輿論》眉批錄[J].新聞記者,2017(5):7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