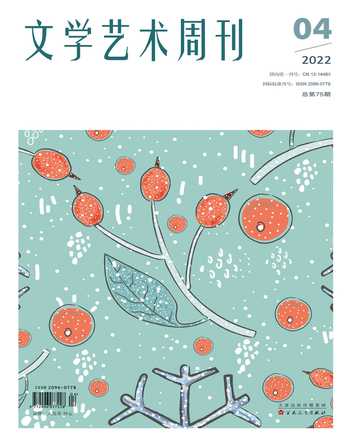論繪畫中的真實再現
一、我們都以主觀視角觀察世界
有人認為照片是對現實世界最真實的反映,其實,繪畫也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反映。從幾何學的角度來說,照片遵循幾何方式對客觀世界進行再現,但繪畫卻融入了主觀對客觀世界的認知。當前,人們普遍認為世界上不存在二維事物,其實不然,繪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二維平面展示三維世界的。只此一點,繪畫就可以與地圖相比。地圖是一種類型化的照片,人們在繪制地圖時,要考慮如何將地理山川展示在二維平面上。但地圖也是不完整的,它不僅反映了客觀世界,也夾雜著制作者的主觀認知。
15世紀,威尼斯僧侶毛羅修士繪制了一幅地圖,以他心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為中心向外延伸。16世紀初,約翰·內斯希望將探險家新發現的區域繪制成一幅大地圖,因此他繼承了古代地圖學家托勒密的投影法,將一張紙平鋪于桌面,然后進行投影。亞洲現存最早的地圖是15世紀的《疆理圖》,這幅地圖將中國和朝鮮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歐洲、非洲則被放在邊角位置。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照片還是繪畫,其實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觀察世界,也就是從自我的角度去繪制圖畫。比如在埃及壁畫中,法老的形象是最偉岸的,其他事物都圍繞法老鋪開,渺小而卑微。說到底,繪畫教會我們觀看,我們需要繪畫,我們的想象同樣需要繪畫,三萬年以來,繪畫一直在協助我們觀看世界。
二、藝術并沒有走出“進步論”
16世紀之前,意大利城邦國家的時尚、富有、豪華遠遠領先歐洲其他國家,城邦君主幾乎個個熱衷于教育、藝術、文物、詩歌,爭先恐后地延聘各地藝術家,數不清的十四行詩與大壁畫遮蔽了當年的血腥。千真萬確的是,彼德拉克、但丁、薄伽丘、喬托、馬薩喬、安吉利科、弗朗切斯卡、曼坦尼亞就生活在13—15世紀,每一位都是君主的貴賓。我們主要的藝術記憶都集中在16—19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的時代。但我們必須懷抱足夠的同情走向米開朗基羅所崇拜的人被當眾吊死的時代。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提過“上半時”和“下半時”的概念,他說現代人對于小說的認知,大多來自18、19世紀,也就是他所謂的“下半時”傳統。他認為應該回到17世紀之前的“上半時”傳統,窺望并借鑒喬叟、薄伽丘、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的文學。其實,詩歌、音樂、繪畫同樣如此。
藝術并沒有進步。我們理解藝術、觀賞藝術的視角至今沒有走出“進步論”藩籬。例如,敦煌壁畫起于漢末,延續到魏晉、隋唐、兩宋,當然還有西夏、遼、金、元代,歷史跨度是“文藝復興”的三倍。可是敦煌壁畫越畫越好嗎?不斷進步嗎?不是。最偉大的敦煌壁畫誕生于公元4世紀的北魏年間,和后世比,北魏畫家幾乎不太會畫畫,可是他們的畫最生動、飽滿、天真、耐看。中國藝術成熟太早,所以敦煌畫家沒有一位留下姓名。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像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是全世界辨識度最高的藝術家,其原因可能與瓦薩里有關。瓦薩里師承米開朗基羅,在16世紀中期寫成了《藝苑名人傳》,日后成為美術史家的重要史料。他把喬托看作藝術發展的起點,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看作藝術的終結,認為沒有人能超越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然而,瓦薩里離他的時代太近了,500年后,我們還要以他的眼光看待歷史嗎?晚近的美術史家早已考證出瓦薩里著作的許多錯訛。拉斐爾并不比喬托好,喬托并不比他的師傅馬薩喬好,馬薩喬并不比那些無名的先輩好。但“文藝復興”三杰的神話延續至今,在公眾面前過度傳播,使人們的歷史視野變得狹窄。
三、筆痕的含義
在繪畫領域,筆痕是畫功的展現。畫家借助兩三道筆痕就能在紙上展現藝術世界,這筆痕把一種事物表現為另一種事物。筆痕的本質是運動,是筆觸按照既定的軌跡運動,借助不同的速度,展示所要表達的事物。筆痕的快慢疾緩可以通過運筆看出來。基于此,很多人開始追求筆痕外露的作品,尤其是簡潔的筆痕,更受人推崇。愛德華·蒙克最擅長以簡潔的筆痕展示作品的魅力,他的代表作品《鐘與床之間的自畫像》僅用簡單幾根線條就畫出了一張床,人們不得不驚嘆他高超的技巧。13世紀中國僧人畫家牧溪同樣筆痕簡潔,他的作品一般很小,用墨非常少,但是墨色濃淡、運筆方向和速度都有著極其微妙的變化,簡單幾筆,就交代出描繪對象。許多中國畫都有這個特點,他們勤于練習,比如畫一朵花,最初可能用十幾筆,隨著反復深入的練習,減少為三到四筆。要想領會中國藝術的深刻內涵,需要深厚的文化和審美積淀。
與中國繪畫密切聯系的書法,也講究筆痕的簡潔,強調借助筆痕的細微變化來展示書法藝術的深刻內涵。中國書畫家、藝術理論家董其昌把繪畫中的筆墨提到極高的程度,他說:“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藝術是精神的,自古以來,中國繪畫的目標不是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和氣韻生動。氣韻這種無形的能量借助畫筆留下了可見的筆痕。中國畫家﹐尤其是文人畫家﹐對筆墨的追求已經達到癡迷的程度,有對干濕筆的研究,有對皴法的分析。明朝一位繪畫理論家將石頭的畫法總結出26種,將樹的畫法總結出27種。中國畫家不認為自己的筆墨粗糙,反而認為過于細致的筆痕算不上上乘。對此,西方畫家也非常認同,生活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就是這種藝術觀點的杰出代表。如果中國古代繪畫大師看到倫勃朗的作品,定會交口稱贊。
倫勃朗著名的素描作品《學步》就運用了簡潔的筆痕。畫中,母親和姐姐攥著孩子的手,母親的手堅定有力,姐姐的手有些猶豫。倫勃朗對姐姐的面部進行了描繪,她仿佛有些緊張,但簡潔的筆痕展示出姐姐優美的身材。此外,姐姐的筆痕緩慢,母親的筆痕迅速,正是這筆痕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在紙上移動,并觀察到人物的內心。母親衣著破舊,并沒有過多細節描繪。一旁蹲著的父親和姐姐形成穩固的三角構圖,讓人們感受到了父親的堅毅。路過的擠奶女不經意的一瞥,讓人們感受她提著的水桶的重量。如此復雜的作品,畫家僅僅用了6筆。
筆痕的歷史如同繪畫史一樣不斷演進。到了18世紀晚期,西方學院派畫家就希望盡可能去除筆痕。有的畫家為了被學院派繪畫接受,將筆痕藏進了畫里。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的高級院士約瑟夫·法靈頓曾經教育自己的學生,要讓畫的完成度高一些,這樣才會被皇家學院所接受,言下之意,就是要他們消除筆痕。約翰·康斯太勃爾的畫在當時就備受爭議,一度被認為是沒有完成的草稿,因為筆痕過于明顯。為此,康斯太勃爾常常將自己的作品復制成兩個版本,一個為了迎合沙龍畫展,另一個作為創作留存。到了馬奈引領的印象派時代,外露、稚拙的筆觸又重回畫面,他們不再受制于學院派繪畫,而是公然宣戰,并贏得了這場生動自由對陣傳統乏味的戰役。
四、繪畫是手眼心的協調
21世紀,霍克尼在他的《隱秘的知識》一書中指出,像卡拉瓦喬這樣的大師也可能借助光學投影來完成作品。他還提出,卡拉瓦喬的作品留有肉眼可見的印痕,借助這些印痕我們可以看到繪畫是如何完成的。卡拉瓦喬不用拉斐爾那種通過紙上構思建構畫面的辦法,而是先把模特的姿勢擺好,如同導演一部戲劇,然后照著每個演員的姿勢進行創作。他先把一個人物,也可能只是人物的一部分,投射到畫布上,接著再投射另一個人物的影像,有點兒像影像拼貼。除此之外,卡拉瓦喬還使用明暗對比強烈的光影畫法。16世紀末期,他的作品開始變暗,有的甚至漆黑如墨。有評論家稱,他這一時期的作品就像在沒有光線的屋子中創作的一樣。而他正是通過這種黑暗,完成了光影在畫布上的投射。但是,畫家僅僅運用光學儀器作是不能創造奇跡的。西方有很多效仿卡拉瓦喬的畫家,他們并非都借助光學器材作畫,當時年輕的倫勃朗就是其中之一。他繼承并強化了卡拉瓦喬的光影處理手法,并將其重構為獨特的藝術語言,他用筆觸和顏色傳遞語言和力量的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強。所有偉大的藝術家﹐如倫勃朗、莫奈、畢加索等,都是年紀越大畫得越松爽﹐他們懂得筆法越凝練,繪畫越難能可貴的道理。大師們在一生的繪畫生涯中,不斷顛覆傳統、顛覆自己,所以晚年作品常常是最好的。
肯尼斯·克拉克寫過,倫勃朗的風景素描“在鋼筆畫下的三道筆痕之間,白紙仿佛充滿了空氣”。千真萬確,白紙上流動著空間,還能看到筆觸畫出的“時間”。除了時間和空間,倫勃朗還能畫出其他摸不著的東西,那就是人物的內心。倫勃朗讓人走近他畫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并穿越時空體會他們所感所想。這是用相機無法捕捉的,這關乎心靈。
中國傳統繪畫講究手眼心的協調,三者必須有機融合,缺一不可。這個說法適用于倫勃朗的每一張畫,他的作品是這一觀點的最佳例證。
阿諾爾德·豪布拉肯在對18世紀的藝術家進行評論時,引用了倫勃朗的話,他說:“假如我要解脫自己的精神,我就不應追求榮譽,而應追求自由。”倫勃朗是具有探險家意識的繪畫大師,他用大膽的方式去創新、去改革,而這一切都來源于他對自由的追求。根據豪布拉肯的描述,倫勃朗是觀念上最具有現代意識的大師,他一直認為作品是否完成取決于畫家本人,如果作畫的目標達成了,那么作品就是完成的狀態。
倫勃朗毫不拘泥于傳統,他用越來越厚的顏料堆砌,用越來越松爽奔放的筆觸作畫,時而用筆桿刮擦,時而用刮刀堆出厚厚的顏料層——那是顏料凝結層的盛宴。幾乎他的每張新畫都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顛覆傳統、重塑人生。正如梵·高說的那樣,倫勃朗是個“魔法師”。當梵·高談起倫勃朗的《猶太新娘》時,他用虔誠的口吻宣稱:“我愿意用十年的生命,換取我繼續坐在這張畫前兩周,只以一塊面包為食。”這張畫作,不僅是它的肌理感、厚重感、層次感令人折服,還讓觀眾與畫家的情感得到連接,這是一幅歷經滄桑仍閃耀著人性光芒的畫作。倫勃朗不僅能呈現人性的偉大,還能呈現人生歷經貧困、凄愴和卑微時的感人力量。
將一個二維平面復制到另一個二維平面上很容易,難的是將三維物象轉換為二維圖像。在這個轉換過程中,藝術家面臨很多抉擇,他們將真實空間轉化為圖畫,把表現對象風格化、主觀化并重新詮釋它。如今,人們受到引導,相信照片就是現實,甚至已經停止思考或質疑有關繪畫的問題,他們欣然接受照片就是視覺上的完完全全的真實。其實,“它”根本不是,現實和真實是兩個模糊且無法界定的概念。照片里看到的只是某種程度上的真實,但畫家不應照搬這個世界,不應被相機扭曲我們的“自然”觀察。
[作者簡介]孫曉芳,女,漢族,遼寧沈陽人,就職于遼寧省文化演藝集團(遼寧省公共文化服務中心),研究方向為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