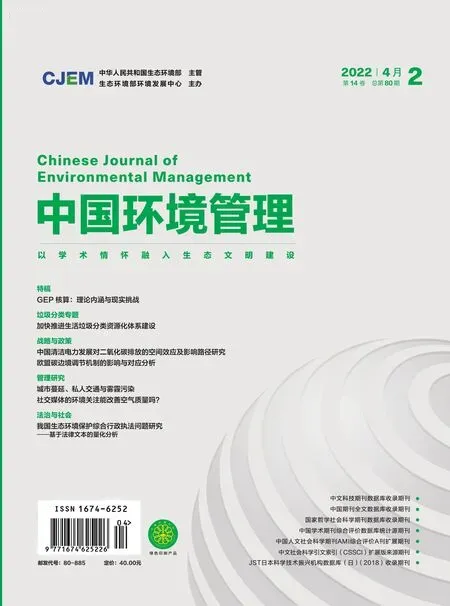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能改善空氣質量嗎?
王俊松
(1.華東師范大學全球創新與發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2.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
引言
重污染天氣已經成為影響居民健康的重要來源,PM2.5是影響空氣質量的最有害的物質之一[1,2]。已有的研究將PM2.5濃度的增加歸因于自然和社會經濟因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境規制、城市化水平或自然因素[2-7]。在社會經濟因素的方面,已有的研究傾向于從自上而下的角度強調中央和地方政府環境規制的作用。較少從自下而上的角度關注公眾壓力對環境質量的影響。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以微博、微信為主的社交媒體用戶持續增加。公眾能夠實時在社交網絡上表達對民生或環境問題的意見。社交媒體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促進地方政府加強了環境規制,改善空氣質量[8,9];社交媒體也被公共機構用于評估網絡輿情、應對突發事件、開展溝通和宣傳工作[10]。自下而上的社交媒體對環境治理的影響往往被忽視。本文主要探討不同城市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如何影響城市PM2.5濃度水平,并進一步從城市創新能力、城市等級和財政分權的角度探討社交媒體環境關注的區域差異與城市PM2.5濃度水平之間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反映的環境關注是降低城市PM2.5濃度水平的重要因素,較高的城市層級和創新能力對這種關系有積極影響。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第一,首次從社交媒體反映的環境關注的角度研究空氣污染的治理,提供一個探討環境問題的自下而上的視角;第二,本文基于中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來定量分析社交媒體與空氣污染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內在機制;第三,采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來控制污染水平的空間溢出效應,并通過引入工具變量等多種方法驗證了結果的穩健性。本文的研究結論將為分析環境污染問題提供新的視角。
1 理論與文獻綜述
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促使網民越來越多地使用社交媒體來表達他們對民生相關問題的關注[11],其中環境污染問題[12]是最突出的議題之一[8,9,13]。新浪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平臺為民眾提供了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的便捷渠道[14]。社交媒體對個人和政府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對于個人來說,社交媒體提供一個討論和表達對環境污染問題的渠道[15]。當嚴重霧霾天氣出現時,超過一半的居民認為政府應該采取措施積極解決問題[16],公民還積極向政府舉報污染事件甚至發起訴訟[17]。公眾在社交媒體上對環境的關注有助于對地方政府施加一定程度的壓力。
對于政府來說,社交媒體提供一個了解輿情、與公眾溝通和宣傳政策的有效工具[18]。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中央政府愿意聽取公眾呼吁,建立嚴格的污染排放環境法規,并通過“壓力傳導機制”推動省級和地方政府執行環境相關法規[19]。但是,我國科層制下的環境治理極易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對稱[17]。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于環境治理的偏好不一致,即使中央政府做出強有力的治理環境污染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官員也有可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偏離中央的制度。同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監管能力有限,從自上而下的角度治理環境問題有其內在的不足。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可以從自下而上的角度幫助監督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合謀行為,為中央政府補足信息,強化中央政府的監管。社交媒體的流行提供了政府與網民溝通的重要平臺。公眾通過社交媒體關注環境問題,并對政府施加環境保護的壓力,改變了政府、企業和民眾應對空氣污染的方式[8,20]。社交媒體上的環境信息和對霧霾等環境問題的關注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動力,推動政府更迫切地治理污染問題。
社交網絡的環境關注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富裕人群和意見領袖往往更關注環境和健康問題,也更容易利用社交媒體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這些人群大多生活在大城市或沿海發達地區,他們對地方政府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施加了更大的壓力。我們認為社交媒體對環境關注的區域差異將顯著影響城市PM2.5濃度水平。因此,第一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社交網絡上對環境問題更關注的區域能夠更有效地降低PM2.5濃度水平。
社交媒體上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不會自動提升環境質量,還需要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治理[21]。地方政府同時面對來自上級政府和居民的環境治理壓力。中央政府通過各種環境規制對地方政府施加壓力[22],巡查并懲罰違反環境法規的城市或地區。在這一過程中,更高等級的城市被迫遵守更嚴格的法規[23],例如,2013 年發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PM2.5濃度在2017 年之前分別降低25%、20%和15%,高于全國平均10%的減排建議。高等級城市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更富裕,對環境和健康問題更為關注[24]。更高等級的城市可能受到中央政府和居民的更多環境治理壓力。我們認為,較高等級的城市有助于促進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降低PM2.5濃度水平的作用。
假設2:對于更高等級的城市,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更容易降低城市的PM2.5濃度水平。
社交媒體產生的環境關注是否能促進城市降低PM2.5濃度水平,還取決于地方政府的能力。Grossman等[25]指出,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改善的作用源于產業結構改善和技術進步的影響。應對公眾的環境治理壓力,地方政府進行產業轉型和技術升級的能力決定了環境治理的效率。在創新能力較強的地區,創新活動有助于緩解資源環境約束,推動經濟的集約化發展,新技術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進產業向清潔和高附加值產業轉變,從而對環境產生積極影響[26-28]。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可以更多地借助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方式應對空氣污染問題,也有更多資金用于環境治理,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選擇[29]。因此,我們認為,城市創新能力將有助于提高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降低城市PM2.5濃度水平的促進作用。
假設3:創新能力更強的城市,其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更有利于降低城市PM2.5濃度水平。
地方政府應對環境關注改善環境的能力也取決于其環境治理的財政能力。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被賦予了更大的發展地方經濟的自主權。財政分權促使地方政府擁有財政收入剩余索取權和財政支出控制權[30]。地方政府更有可能通過吸引和保留低污染企業來提高地方收入[31-33]。即使環境績效已被加入干部考評體系,地方官員仍然不放松經濟發展的目標。地方政府對高污染行業的態度因其財政狀況而異。財政盈余充足的發達城市更容易有效應對社交媒體上民眾的環境保護壓力,政府更有能力通過提升經濟結構、引入污染減排設施、增強環境規制力度等方式改善環境,也有充分的財政收入應對污染企業流失帶來的稅收損失。然而,面臨預算限制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優先強調地方經濟發展,其支持環境保護的財力有限,從而降低面對環境保護壓力時改善環境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本文第四個假設如下:
假設4:公共預算限制削弱了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降低城市PM2.5濃度水平的作用。
已有的實證研究中,少數研究探討了社交媒體和空氣質量之間的因果關系。Zheng 等[34]基于中國的微博數據證實,空氣污染會降低居民的幸福感,且女性的幸福感比男性的下降得更快。較少有研究分析社交媒體對空氣質量的影響。Kay 等[8]利用新浪微博上2012 年和2013 年環境相關的帖子,分析了政府、企業和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發現微博有助于推進環境保護事業,但研究僅僅基于案例分析,影響結論的普適性。李欣等[12]基于省級尺度的百度搜索數據和計量模型分析發現,網絡輿論表征的非正式制度有助于緩解霧霾污染,該研究關注到網絡輿論作為非正式制度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但是研究尺度相對較粗,且機制分析有待深入。當前,社交媒體如何影響中國的空氣質量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旨在基于定量方法,以微博為例分析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的區域差異對空氣質量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可能的作用機制。
2 方法和數據
2.1 空間回歸模型和變量
PM2.5濃度水平存在空間相關性,本文引入空間回歸模型分析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如何影響城市PM2.5濃度水平,以獲得一致的估計。空間回歸模型被廣泛用于環境實證研究的其他領域[35,36]。空間回歸模型一般分為空間滯后(SAR)模型、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其中SAR 模型中的空間相關性源于因變量滯后項的相關性,而SEM 中的空間相關性源于模型的誤差項,SDM 同時考慮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空間相關性,由于因變量和自變量可能同時存在空間相關性,本研究選擇SDM,以獲得可靠的結果。

式中,Y為n×1(n為地級市數量,n=263)的因變量向量;X為n×k(自變量數量為k-1)的解釋變量矩陣;β為解釋變量的系數;ρ為因變量空間滯后項的系數;θ為自變量空間滯后項的系數;ε為擾動項;i為地級單元;t為年份,范圍為2014—2018 年。所有的X變量都滯后一年以消除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每年有263 個地級市被引入模型。W是一個n×n的空間相鄰矩陣。Wij被設定為500km 帶寬內i和j城市距離的倒數。
主要變量介紹如下:因變量是城市每年平均PM2.5濃度水平并取對數(ln PM2.5)。主要自變量是社交媒體反映的環境關注,采用新浪微博上環境相關主題的城市人均發帖數量(PollutantPost)表示,其中環境相關的關鍵詞包括“霧霾、水污染、空氣污染、污染物、環境保護”。自變量包括城市等級、創新能力、財政壓力及社會經濟控制變量。
城市等級:引入城市等級變量(Hierarchy)分析城市的行政等級是否影響城市PM2.5濃度水平,以及是否影響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和城市PM2.5濃度之間的關系。對4 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賦值為2,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的賦值為1,其他城市的賦值為0。預期高等級城市可能有較高的污染水平,但也可能對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做出更有效的反應,并降低PM2.5濃度水平。
創新能力:以城市人均專利授權數(Patent)來衡量創新能力[3,36]。較強的創新能力有助于地方政府應對公眾壓力,從而改善空氣質量。
財政壓力:城市財政壓力可能影響城市的空氣質量,以城市財政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來衡量財政壓力(Finance)并引入模型。預計地方財政壓力對城市PM2.5濃度水平產生顯著影響,且財政負擔將降低政府有效地回應環境關注的能力。
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引入人均GDP(對數)(ln PGDP),以分析經濟發展對空氣質量的影響。引入城市實際利用外資額與GDP 的比例(FDI),以控制全球化因素的影響。引入人口密度(Density)和第二產業占GDP 的比例(Industry)以控制城市化因素對空氣質量的影響[37]。由于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比例存在較強的負相關關系,為避免共線性,未引入第三產業比例變量。引入道路面積(Road)變量,預期可能顯著提高城市PM2.5濃度水平[38]。
其他控制變量:①供暖虛擬變量(Heating),即冬季有集中供暖系統的城市被賦值為1,否則為0;②降水量(Precipitation),以城市的年降水量為對數來衡量;③風速(Wind),以城市年均風速來衡量;④平均氣溫(Tempre),以城市年均溫度來衡量。本文將連續性變量取對數,以降低異方差問題的影響。所有變量的描述見表1。變量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顯示PollutionPost 與其他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很小,表明PollutionPost 的回歸系數是可信的。

表1 變量定義及描述
2.2 數據來源
PM2.5數據來自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將空氣質量監測站點與所在城市匹配,并在城市層面將全年的PM2.5數據取平均得到城市年度PM2.5均值。社交媒體反映的環境關注數據從新浪微博抓取。首先,從2014—2018 年的微博上抓取包含“霧霾、水污染、空氣污染、污染排放、環境保護”等關鍵詞的發帖①選擇2014 年作為研究起始年份是因為該年是能夠獲取的系統的地面觀測PM2.5 數據的最早年份,2014 年前的城市PM2.5 數據只能根據衛星數據推算,存在較大誤差。;其次,抓取每個帖子的微博ID、發布時間、發布地點、ID所在地點等數據;最后,根據發帖位置對每個城市的每年環境相關的發帖數進行匯總。為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影響,城市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采用環境相關的微博發帖數量占該城市人口的比例表示。道路和降水相關數據來自中國科學院資源與環境科學研究中心(http://www.resdc.cn)。其他經濟和社會屬性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3 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和PM2.5 濃度水平的空間分布格局
表2 顯示2018 年各省份微博環境相關發帖數及PM2.5均值。可以發現,環境相關發帖主要位于中國東部和南部地區。京津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擁有最多的環境相關的微博發帖數。東部地區是對環境關注度最高的地區,而大多數西部和東北部地區的居民對環境的關注度較低。發達地區的居民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并且更注重生活品質,關注自身和子女的健康,在面對嚴重霧霾或污染時,更容易做出積極的反應。

表2 各省份微博環境主題發帖數及PM2.5濃度均值(2018年)
PM2.5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主要位于華北地區,其中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和安徽北部是受PM2.5影響最大的省份。這些地區有豐富的煤炭資源分布,或存在消耗大量煤炭的工業。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是另外兩個受PM2.5影響較嚴重的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口和產業較為密集。廣大西部地區受重污染天氣的影響相對較小。
與環境相關的微博發帖量和PM2.5濃度水平的空間分布存在一定的異同。盡管二者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密度都較高,微博的環境關注更多集中在發達地區,這意味著這些地區的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面臨更大的公眾壓力,但同時,更好的財政條件以及人們對環保的認知有助于這些地區更有效地控制PM2.5。除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外,PM2.5濃度水平高的地區與煤炭資源和消耗煤炭資源的重化工業的分布更趨于一致。
微博的環境關注與城市排名的分布情況如圖1(a)所示,縱軸為微博上的環境相關主題的發帖數量,橫軸為發帖量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可見發帖量高度集中在頭部(排名前兩位)城市,排名前十的城市占到了微博上環境相關發帖的50%以上。PM2.5濃度水平由高到低的分布則相對平緩,如圖1(b)所示。

圖1 微博上的環境關注和PM2.5濃度水平與城市排名的散點圖(2018年)
4 環境關注與城市PM2.5 濃度水平:計量結果
由于存在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本研究采用隨機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結果見表2。ρ在所有估計中都顯著為正,進一步證實PM2.5濃度水平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一個城市的空氣污染會使鄰近地區的空氣質量惡化,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39,40]。表3 中第(1)列只引入微博的環境關注變量,第(2)列引入所有控制變量,第(3)~(5)列分別引入環境關注與城市等級、創新產出和財政壓力變量的交互項,探討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PM2.5濃度水平影響的作用機制。

表3 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
結果基本符合預期。除第(4)列外,社交媒體環境關注的系數均顯著為負。第(4)列中,當引入PollutionPost 和Patent 的交互作用時,PollutionPost 不顯著為負,但加上交互項以后,PollutionPost 的整體效應仍然為負。因此,可以認為,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的PM2.5濃度水平。人們對環境污染的關注可能促使地方政府積極應對并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城市等級、創新能力和城市財政壓力的系數顯示,城市等級制度和城市的財政負擔對PM2.5濃度水平沒有顯著影響,而創新能力顯著提高了空氣的PM2.5濃度水平,與預期相反。這可能是由于較強的創新能力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和產業集聚,包括污染性產業,從而促使PM2.5濃度水平上升。
PollutionPost 和城市等級的交互作用系數在1%的濃度水平上顯著為負[第(3)列],表明層級更高的城市更能促進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降低PM2.5濃度水平的作用。大城市的公民更關注污染問題。同時,較大的城市能夠更好地響應公眾的呼吁,轉向清潔的產業結構或實施更嚴格的環境規制。同樣,第(4)列的交互項系數顯示,創新能力強的城市,其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更容易降低其PM2.5濃度水平。這表明面對公眾的環境關注時創新能力強的城市更容易通過提升技術降低污染,并向綠色產業轉型[26,27]。第(5)列的環境關注和財政壓力交互項系數不顯著為正,顯示財政壓力大小不能有效促進公眾的環境關注對環境的改善。在面臨公眾環境壓力時,財政負擔重的地區仍然無力有效治理環境。
控制變量的系數基本符合預期。富裕地區更有利于降低PM2.5濃度水平,表明發達城市更有能力和動機控制污染。城市的FDI、人口密度、第二產業比例的增加顯著提高了城市PM2.5濃度水平,表明人口和產業的集聚均可能導致空氣惡化。城市集中供暖是PM2.5濃度水平上升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因為中國北方地區在冬季嚴重依賴煤炭取暖。城市年均風速能顯著降低PM2.5濃度水平,而降水量、溫度和道路密度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不顯著。
從自變量空間滯后項的系數看,周邊城市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本地區城市PM2.5的影響不顯著,周邊城市的財政壓力、供暖和道路密度均可能增加本城市的PM2.5濃度水平,這是由于財政壓力可能促使周邊城市更多地發展污染產業,提升了本城市的PM2.5濃度水平。周邊城市的城市供暖和道路密度均可能使污染溢出到本地區城市,從而影響空氣質量。周邊城市其他變量對本城市PM2.5的影響不顯著。
進一步通過調整變量和模型來檢驗系數的穩健性(表4)。首先,剔除與其他變量高度相關的變量,包括專利、財政壓力和人口密度,并以表2 第(2)列的模型為基準進行回歸。結果顯示PollutionPost 的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不變。其次,我們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重新回歸,第(2)、(3)列的結果顯示,變量的系數仍然顯著為負。因此,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可以降低城市的PM2.5濃度水平的結論是穩健的。
還可能出現反向因果關系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可能導致PM2.5的下降,但也可能出現反向因果關系,即空氣污染使微博上關注環境話題數量的上升。我們試圖通過引入工具變量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偏誤。把3 年前的城市網民比例和工資作為工具變量引入工具變量面板數據回歸,這些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網民比例是一個合適的工具變量,因為它與內生變量PollutionPost 正相關,而它可能不會通過其他渠道影響PM2.5濃度水平。結果顯示在表4 的第(4)列和第(5)列。第(4)列不包括控制變量,第(5)列包括控制變量。Cragg-Donald Wald F 檢驗拒絕了弱工具變量的假設,表明結果可以接受。回歸系數顯示結果仍然穩健。第(6)列同時引入了互聯網用戶的比例和城市工資作為工具變量,選擇3 年前的城市工資作為工具變量的原因在于更富裕的人更關注環境,更有可能表達意見,但應該不會通過其他渠道影響到現在的空氣質量。過度識別檢驗的Sargan-Hansen 統計量為0.074,p值為0.78,接受工具變量為外生的原假設依然穩健,進一步證實了微博上環境關注對空氣質量的改善產生了積極影響。

表4 穩健性檢驗的結果
5 結論
眾多研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國城市空氣污染的決定因素,但較少關注到自下而上的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對改善空氣質量的影響。本研究探討了社交媒體所反映的環境關注對城市PM2.5濃度水平的影響以及內在機制。社交媒體為公民提供了一個關注環境的渠道,也是政府進行輿情監測和公眾溝通的重要平臺。社交媒體的公眾參與和監督可以從自下而上的角度幫助中央監督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合謀行為,為中央政府補足信息,強化中央政府的環境監管。本研究闡明了公民的環境意識和環境參與對我國環境治理的重要性。
空間回歸模型的結果證實了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能有效降低PM2.5濃度水平,表明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已經成為我國影響環境治理重要因素。高等級城市及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能夠更好地回應社交媒體的環境關注,并降低PM2.5濃度水平,而財政壓力無助于城市應對環境關注改善空氣質量,研究還證實了工業化、城市化和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對城市PM2.5濃度水平的顯著影響。本研究的結論表明,公眾通過社交媒體參與環境討論,從自下而上的角度為環境治理提供信息并強化監管,改變了政府、企業和個人應對空氣污染的方式。在分析環境問題時,應該充分考慮到新興社交媒體平臺的影響。在環境治理的過程中,對于高等級城市和創新能力強的地區,應充分發揮自下而上的公眾監督力量,促進環境的不斷優化。對于財政壓力較大的落后地區,環境治理依賴于自上而下的監管和扶持,中央政府應通過財政扶持或專項轉移支付等手段幫助環境壓力大的落后地區優化產業結構,促進高質量發展和環境改善。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受數據可得性的影響,本研究的時間段較短,隨著時間的推移,社交媒體對環境的長期影響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此外,本文未充分考慮污染企業的遷移對城市空氣質量的潛在影響,未來有必要對此做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