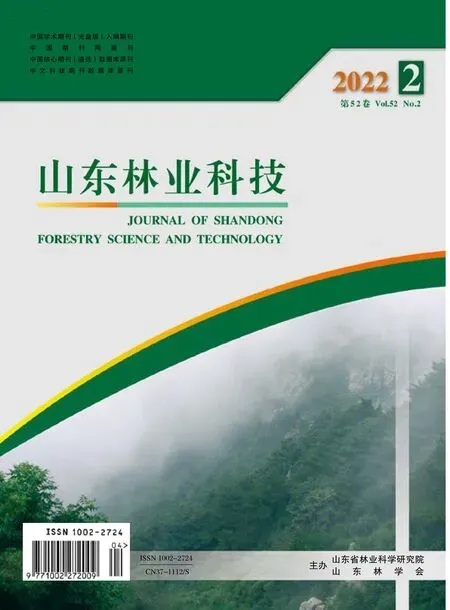基于MaxEnt模型的西雙版納保護區曼稿片區印度野牛生境適應性分析保護建議
文世榮,方 國,張明霞,楊建波,李嘉斌,賀如川,張 潞,甘忠莉*
(1.云南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護局,云南 景洪666100; 2.廣西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廣西 桂林541001;3.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201; 4.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100049; 5.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云南 勐侖666303)
熱帶地區具有非常高的生物多樣性,然而也面臨著極大的人口和經濟發展壓力。 其中最容易受到威脅的物種往往是體型較大或對生境有特殊要求的物種[1],所以在建立保護區時,也會優先考慮到這些物種的需求,并力圖通過保護這些物種來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功能[2]。
西雙版納位于我國西南邊陲,是全球25 個熱點保護區域之一[3],整個地區的面積僅占中國的0.2%,卻承載了中國超過16%的高等植物種類和36%的鳥類[4],是很多瀕危物種,如亞洲象(Elephas maximus)、印度野牛(Bos gaurus)、犀鳥(Bucerotidae spp.)等的家園。 其中,印度野牛在全國的種群數量估計不足200 只[5,6],在國內僅記錄于云南南部西雙版納、普洱和藏南地區[6],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在IUCN 紅色名錄中被列為易危VU 級別[7],在中國紅色脊椎動物中被列為極危級別[8]。 張忠員等(2018)總結了1988—2016年之間的西雙版納印度野牛種群變化趨勢,發現由于受到棲息地破碎化和狩獵的威脅,它們的數量從650~712 頭減少到目前的152~167 頭[5];甘宏協和胡華斌(2008)基于印度野牛的生境要求,在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曼稿片區和納板河保護區之間規劃了廊道;丁晨晨等(2018)則根據文獻和訪查數據,對全國的印度野牛適宜棲息地進行了分析[6]。 然而,以上研究工作中野牛分布數據均是基于訪查或短期野外調查獲得,且數據年代較久遠。 為了為保護印度野牛提供詳實的建議,需要開展實地調查,并結合當地的植被、地形、村莊等信息,對不同地點的棲息地適宜程度進行分析。
西雙版納國家級保護區由勐侖、尚勇、曼稿、勐養、勐臘5 個不相鄰的保護片區組成,其中曼稿片區位于勐海縣內,面積78.70 km2,是5 個片區中面積最小、海拔較高一個片區。 曼稿片區是目前比較穩定的印度野牛分布區之一[5],同時,由于面積小,周邊村寨較多,保護區面臨的人為干擾壓力較大,在這一片區開展野牛相關研究,可以幫助保護區制定參考策略,也可以為野牛分布的其它區域提供參考。
本研究主要基于2019—2020年的曼稿片區內的紅外相機和實地調查數據,利用MaxEnt 模型對保護區及其周邊區域的印度野牛生境適宜性進行了分析,并基于分析結果,提出了保護區的管理和今后的廊道建設等方面的計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點
曼稿子保護區位于東經100°15′—100°30′, 北緯22°00′—22°10′ 之間,海拔范圍為1080—1770 m。地貌主要以淺切割中山為主,氣候類型為南亞熱帶氣候,植被為闊葉林,地勢較高處有面積不大的思茅松侵入(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2010)。 當地年均降雨量1400 mm左右, 每年的5—10月為雨季,11月到次年4月為旱季。在本研究中, 我們以曼稿保護區向外緩沖5 km 的范圍劃定了研究區域以便包括周圍的村莊和野牛的潛在擴散范圍,面積共約370 km2(圖1)。

圖1 研究地點的植被和野牛的野外調查點分布情況Figure 1 The position of study region in Yunnan province, the vegetation map and survey sites of Gaur in study area
1.2 印度野牛分布位點獲取
在開始正式野外調查之前,我們先對整個保護區進行了訪查和預調查,預調查覆蓋了整個保護區范圍,根據訪查和預調查, 我們發現野牛主要分布在保護區的邊緣地帶,尤其是西部,所以在這些地方著重安裝了紅外相機,并開展了野外調查。 在2019年10月到2020年10月之間,在保護區的不同海拔帶選取小路,并沿小路安放紅外相機拍攝野牛和其它野生動物,每個紅外相機之間距離不小于500 m,紅外相機安放高度為40~120 cm,相機的拍攝模式為3 張連拍,靈敏度為中。紅外相機下面不設任何誘餌。并每隔4 個月更換一次電池和相機存儲卡。 我們一共在曼稿片區內布設了23 臺相機。 此外,我們通過樣線調查記錄印度野牛的痕跡,例如腳印、糞便等,具體方法為在不同海拔范圍的小路內以1 km/小時的速度行走,并記錄所有樣線及兩邊50 cm 范圍內看到的野牛痕跡(圖1)。
1.3 研究地點環境變量獲取
影響印度野牛分布的主要信息包括地形、植被、海拔、氣候因子例如降雨量等。 我們基于2016年的遙感影像(分辨率30 m),對研究地點的地物覆蓋信息進行了解譯,把當地的地物分為水體、城鎮和村莊、常綠闊葉林、針葉林、灌叢等類別,并在分類結束后,把水體、城鎮和村莊歸并為“其它”類別,分類具體過程見楊建波等(2019)[9]。 然后,我們從世界氣象數據庫(http://www.worldclim.org/)下載了19 個環境因子,對它們進行相關性分析后去除了相關性高的變量,然后插值到30 m 以保持和其它圖層分辨率一致。 同時基于30 m 分辨率的等高線提取了當地的坡度、坡向等數據,并計算了當地的道路、水體的密度和每個像素距離居民點的距離(表1)。

表1 野牛棲息地預測模型中用到的環境變量Table 1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used in the MaxEnt model for gaur’s habitat prediction
1.4 預測模型的建立
我們運用MaxEnt 軟件對研究地點的印度野牛棲息地適宜性進行了分析[10],MaxEnt 是現今常用的一種棲息地分析軟件,它的運行只需要物種的分布點(presence only),而且操作簡單,可信度高,近年來在物種棲息地預測方面取得了廣泛的運用[11-13]。 我們在模型中輸入了24 個印度野牛的野外分布位點,其中10 個基于紅外相機調查獲取的照片確認,14 個來源于痕跡觀察,在運行過程中,選取75%的數據用于模型運行,25%的數據用于檢驗;模型中的環境變量包括表1 中的各個因子。 獲得運行結果后,通過模型AUC 值判定模型的效果,并利用Jackknife 刀切法探討各個環境因子的貢獻;并選取相等靈敏度和特異度(Equal training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的cloglog 閾值對結果進行了重分類,大于這一閾值設為野牛的適宜生境,小于這一閾值設為不適宜區域。
2 結果與分析
2.1 當地環境變量
經過解譯遙感影像,我們獲得了當地土地覆蓋類型圖。 對19 個氣候因子進行相關分析后,我們保留了其中的11 個,最后輸入到模型中的環境變量見表1。
2.2 模型運行結果
模型AUC 值為0.987,效果很好。 對印度野牛分布影響最大的幾個因素包括最濕季降雨量、道路密度、坡度、植被類型等,它們的貢獻率依次為20.5%、20.3%、,12.9%和10.2%,可以看到,印度野牛的出現率隨最濕季降雨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時它們偏好靠近道路、平緩的常綠闊葉林和灌叢(圖2)。 基于Jackknife 刀切法判定的各個因子的重要性見圖3。

圖2 模型中貢獻率最高的四個環境變量對野牛出現率的影響情況a:最濕季降雨量;b:道路密度;c:坡度;d:地物覆蓋類別(1 為其它,2 為茶葉,4 為灌叢,7 為常綠闊葉林,8 為針葉林)。 紅色為模型均值,藍色為加減一個標準差后的數值。Figure 2 The effect of most important four variables to the presence of Gaur.a: Precipitation of Warmest Quarter; b:Road density; c:slope; d:vegetation type(1:others,2:tea plantation; 4:shrub;7,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8:conifer forest).The red is mean, and blue shows the number with ±one standard deviation.

圖3 基于Jackknife 刀切法對各個環境變量重要性的評估Figure 3 The results of the jackknife test of variable importance.
在模型中,取相等靈敏度和特異度閾值為0.272,我們把大于0.272 的區域設為野牛的適宜生境,其它區域則設為不適宜區域。所得結果見圖4。在研究區域內,野牛的適宜生境總面積為21 km2,其中61%位于保護區內。

圖4 西雙版納曼稿保護區及其周邊區域印度野牛的適宜生境圖Figure 4 The suitable habitat map of Gaur in Mangao protected area and surrounded region.
3 討論
我們利用一年時間的樣線和紅外相機調查,獲得了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曼稿片區印度野牛的分布點,并對它們的適宜生境進行了分析。 雖然由于受到人力物力的影響,我們的紅外相機只能覆蓋保護區的部分地區,但是MaxEnt 是基于出現數據(Presence data)進行預測的模型,而且所獲取的結果AUC 值為0.987,所以我們認為有限的野外數據并沒有很嚴重影響模型效果。 丁晨晨等(2018)認為西雙版納勐海縣和勐臘南部具有印度野牛的高適宜性棲息地[6]。 本研究結果與這一研究結論大致相同,但是我們的模型顯示,最濕季的降雨量對野牛的棲息地選擇有比較重要的影響,同時野牛更傾向于選擇靠近道路的區域活動,并且喜歡在坡度平緩的天然植被活動(圖3),而甘宏協和胡華斌(2008)認為野牛主要活動于天然的灌叢和林地、坡度陡峭的區域。 在過去50年來,西雙版納的天然林一直受到橡膠種植的威脅,在低海拔和坡度平緩的地方,大片天然林被橡膠林替代[14,15],由于對天然植被的依賴性,野牛很可能被迫選擇到坡度更陡峭的天然林中活動,基于本研究的模型數據,在分布有天然植被的地方,野牛會優先選擇更平緩的地帶;模型中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變量是道路,從圖3 可以看出,野牛喜歡在靠近道路的地方活動,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年它們在研究地點的道路附近不會受到狩獵威脅,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道路的林緣開闊生境更為適合野牛[16]。
在現期野牛的適宜生境中,有61%位于保護區內,從圖3 中可以看出,野牛并不會明顯的回避人類居民點,而保護區外也存在有大量的天然植被,可以為野牛提供棲息地,所以在保護區的管理中,需要注意防范偷獵,在保護區內部和周邊的村寨開展足夠的宣傳教育,以保證野牛在保護區內外的棲息地中自由活動;另外一方面,保護區周邊和內部都有村寨,保護區內的人為活動幾乎不可避免,所以社區工作在曼稿保護區的管理中非常重要,在保障當地村民合法合理活動的同時,也要加強巡護和宣傳,并在未來基于現有的野牛適宜生境分布狀況制定計劃,才能保證保護效果。
曼稿保護區所在的勐海縣,是整個西雙版納州印度野牛分布比較集中的區域,在曼稿東北面的納板河保護區,和南面的布龍保護區,都有印度野牛的記錄[5]。 在未來,可以考慮通過建立廊道規劃對勐海的野牛棲息地進行聯通和恢復,尤其是恢復低海拔和坡度平緩地帶的天然林,恢復結果不僅可以使野牛受益,也可以同時保護很多生活在常綠闊葉林和熱帶雨林中的的其它野生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