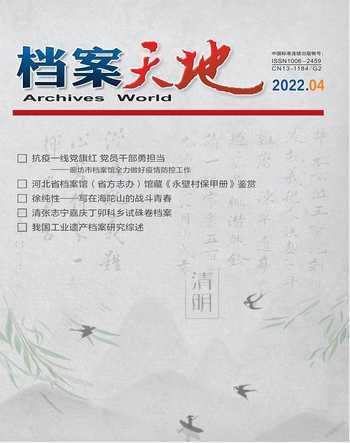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問題與對策探析
葉青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1]。非遺檔案是指與非遺有關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載體的檔案材料[2],對“活態”非遺開展“固化”建檔式保護是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開展非遺保護與傳承工作的必然要求。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就明確了為非遺建檔的任務,同時指出了要在保護的前提下對非遺進行合理利用[3]。
一、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必要性
(一)為綜合檔案館創新檔案開發利用提供了契機
綜合檔案館內反映地方特色的檔案資源稀缺,非遺檔案能夠生動地展現當地獨有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對非遺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有利于綜合檔案館特色館藏優勢的形成。綜合檔案館對館藏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不僅為科研人員開展非遺學術研究查找資料提供了官方渠道,同時還能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檔案文化休閑娛樂方面的需求。
(二)促進非遺的保護、傳承和傳播
非遺是國家和民族記憶的寶貴資源,反映了中華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傳統知識及其表達,代表著民族歷史發展的社會記憶,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4]。為非遺建檔是非遺檔案工作的基礎和前提,使傳統非遺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新時代煥發出新的活力。
二、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主要形式
(一)開展非遺檔案編纂
檔案文獻編纂是檔案館主動配合社會需要、積極開發檔案資源供公眾利用的常見手段。在非遺檔案收集、整理的基礎上,綜合檔案館逐漸開始非遺檔案的編纂工作,非遺檔案編纂成果是宣傳非遺項目、開展非遺利用的重要工具。我國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四級綜合檔案館中均有部分檔案館開展了非遺檔案編纂實踐,非遺檔案編纂工作受到了綜合檔案館的普遍重視[5]。除傳統的文本編纂外,近些年來綜合檔案館也嘗試與其他機構合作,以數字化的形式開展非遺檔案編纂實踐,如武漢市檔案館與市廣播電視臺等合作,拍攝完成了《江城非遺坊》影視節目,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向公眾展示了“武漢歸元廟會”“黃鶴樓傳說”等非遺項目。
(二)舉辦非遺檔案展覽
非遺檔案展覽一直是公共文化機構開發利用非遺檔案的主要形式,綜合檔案館也相繼舉辦過一些非遺檔案展覽。2012年5月,“黔姿百態——貴州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展”在上海市檔案館開展,這是首個由省級檔案館(貴州省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聯合推出的國家級非遺檔案展,此次展覽分“地方戲曲”“音樂舞蹈”“傳統技藝”“節慶習俗”四大版塊,向公眾展示了“侗族大歌”“苗族蘆笙舞”“苗族銀飾”等貴州省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級非遺項目。2018年6月,湖北省檔案館以“展非遺檔案存荊楚記憶”為主題開展非遺建檔成果展覽,展示了“安陸皮影戲”“紅安繡活”“黃陂泥塑”等國家級和省級非遺作品115件。
三、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問題分析
(一)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意識有待提高
總體來看,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力度不大,非遺檔案開發利用實踐狀況并不樂觀。首先,受“重藏輕用”理念影響,綜合檔案館對非遺檔案也是偏重收集、整理、保管而忽視利用。其次,綜合檔案館并非是為非遺建檔和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唯一主體,非遺檔案管理過程中存在著主體分布泛化、職責不清的窘迫狀況,[6]客觀上導致了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積極性不高。最后,非遺檔案是專門檔案的一種,對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要求檔案工作者掌握充足的非遺專業知識,但目前綜合檔案館內非遺專業人才稀缺,檔案工作者整體較為缺乏非遺檔案開發利用方面的經驗和知識,難以對非遺檔案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進行充分挖掘。
(二)有關非遺檔案利用者的研究較為缺乏
新時期下,檔案利用者的非遺檔案信息需求在不斷地發生變化,除部分學者有科研方面的需求外,普通公眾也更加希望能夠方便快捷地獲取到系統全面、形式多樣、趣味性高的非遺檔案信息,以滿足自身文化休閑娛樂方面的需求。綜合檔案館應對利用者的非遺檔案信息需求進行全面的了解,深入分析利用者的非遺檔案利用心理,適應新時代下公眾的信息獲取需求。目前綜合檔案館尚未對非遺檔案利用群體進行充分的研究,對公眾的非遺檔案信息需求了解程度不夠,非遺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三)未開展非遺檔案資源的共建共享
檔案館并非是為非遺建檔的唯一主體,非遺保護中心、圖書館、非遺傳承人等均可為非遺建檔,客觀上導致了非遺檔案的分散。當前綜合檔案館大多還未與其他建檔主體開展合作,館內非遺檔案資源有限,檔案館與檔案館間也未開展非遺檔案資源的共建共享,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孤島”現象的出現。綜合檔案館的非遺檔案開發利用工作囿于本館資源,橫向、縱向機構的無形壁壘破壞了非遺檔案信息的完整性,在為利用者提供同一類非遺檔案信息時僅能體現非遺的局部,難以對非遺的全貌進行全面的展示。
(四)非遺檔案信息輸出方式較為傳統
綜合檔案館對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仍多采用較為傳統的方式,如提供非遺檔案閱覽、咨詢等基礎服務,也有部分綜合檔案館嘗試開展了非遺檔案編纂、非遺檔案展覽等活動,但僅少數綜合檔案館將新理念、新技術、新平臺引入到了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中。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今天,利用者對非遺檔案信息的系統性、趣味性等有了更高的要求,綜合檔案館在堅持應用傳統方式開發利用非遺檔案的同時,也應將新理念、新技術等引入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中,主動探索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新方式。
四、綜合檔案館參與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優化對策
(一)提高非遺檔案開發利用意識
首先,轉變“重藏輕用”的傳統觀念。綜合檔案館應認識到為非遺建檔和保管非遺檔案并不是非遺檔案工作的目的,開發利用非遺檔案,使傳統非遺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新時代煥發出新的活力才是非遺檔案工作的最終目的。其次,明晰自身在非遺檔案保管、利用中的主體作用。非遺檔案是國家檔案財富中的一部分,依據《檔案法》等規定,將非遺保護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等機構保存的重要非遺檔案移交檔案館管理,既能使非遺檔案得到長久有效保護,又有利于形成資源優勢,便于非遺檔案資源的系統開發利用[7]。最后,檔案工作者應充分認識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的重要性,自覺學習非遺相關知識,主動汲取非遺檔案開發利用經驗。
(二)推進非遺檔案個性化服務的開展
檔案利用者的非遺檔案信息需求受職業、喜好、年齡等因素的影響,體現出個性化的特征[8],綜合檔案館應對利用者的各項需求予以明確,盡可能實現個性化的非遺檔案服務,使利用者的各項需求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滿足。互聯網時代下,檔案個性化服務的實現主要依靠微信、微博、APP等新媒體來實現,綜合檔案館在堅持傳統媒體的基礎上,也要主動使用新媒體來推送非遺檔案信息。綜合檔案館可盡快開通微信、微博等新媒體,也可研發檔案APP供利用者使用,并積極引入大數據分析等技術,依據利用者的身份信息、查找記錄等判斷利用者的喜好,為利用者推送其可能需要或感興趣的非遺檔案信息。
(三)建設非遺特色檔案資源庫
豐富詳實的非遺檔案資源是綜合檔案館開展高質量非遺檔案開發利用工作的基礎和前提。首先,盡可能全面地搜集、整理非遺檔案材料。各級綜合檔案館應深入本行政區域內非遺資源所在地,轉變傳統觀念,深入了解非遺的起源、發展等狀況,全面采集非遺檔案材料[9]。其次,開展非遺檔案數字化建設。對非遺檔案開展數字化建設,有利于綜合檔案館利用檔案網站、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宣傳、展陳和傳播非遺檔案信息。最后,與相關機構開展非遺檔案特色資源庫的共建共享。綜合檔案館可聯合本行政區域內的非遺保護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等非遺保護機構共建非遺數據庫,也可與其他行政區域內的檔案館或其他非遺保護機構共享非遺數據庫,豐富本館的非遺檔案資源。
(四)采取多種方式輸出非遺檔案信息
檔案信息的輸出是檔案利用工作系統的窗口,綜合檔案館開展高質量的非遺檔案開發利用工作要主動采取多種方式輸出非遺檔案信息。首先,堅持傳統非遺檔案信息輸出方式中的精華部分,如編輯發行非遺檔案信息參考、開展非遺檔案資料編纂、舉辦非遺檔案展覽等。其次,主動結合新技術、使用新平臺輸出非遺檔案信息。綜合檔案館可積極引入VR、AR等新興技術,綜合使用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樣化的形式對非遺進行全面系統的介紹。如AR影像圖書《了不起的非遺》,它通過圖片、文字、音頻、視頻等形式動靜結合地展演和展示了武漢市的非遺文化[10]。綜合檔案館還可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平臺輸出非遺檔案信息,切合公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的碎片化閱讀習慣。最后,開發非遺檔案文創產品。綜合檔案館可借鑒各大博物館的做法,以非遺檔案內容為靈感來源開發文創產品,激發公眾了解非遺項目的興趣。
(五)構建暢通的非遺檔案信息反饋機制
非遺檔案工作者根據反饋信息,能夠及時了解利用者需求的變化,從而調整非遺檔案信息輸出的內容和形式,使利用者的需求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綜合檔案館可以通過給非遺檔案利用者發放調查問卷、發送電子郵件、電話回訪等傳統形式收集反饋信息,也可通過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與利用者進行互動交流[11],了解利用者的意見和建議以及非遺檔案信息利用需求。
參考文獻:
[1][3]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EB/OL]. (2005-08-15)[2022-01-05].http://www.gov.cn/zwgk/2005-08/15/content_21681.htm.
[2][6]聶云霞,龍家慶,周麗.數字賦能視域下非遺檔案資源的整合及保存:現狀分析與策略探討[J].檔案學通訊,2019(6):79-86.
[4]張赟,王昊,劉友華等.面向我國非遺檔案工作的主題演化研究[J].檔案與建設,2021(6):40.
[5][10]王曉漫,戴旸.檔案部門參與非遺檔案編纂的現狀與對策研究[J].宿州學院學報,2020,35(6):9-11.
[7]華林,段睿輝,李婧楠.云南少數民族傳統手工藝非遺檔案活態性開發研究[J].檔案學研究,2019(4):94.
[8][11]王春華.“非遺”檔案文化的精準傳播模式研究[J].山西檔案,2017(4):140-142.
[9]黃秀萍.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傳播看非遺檔案的開發利用[J].辦公室業務,2014(21):72.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