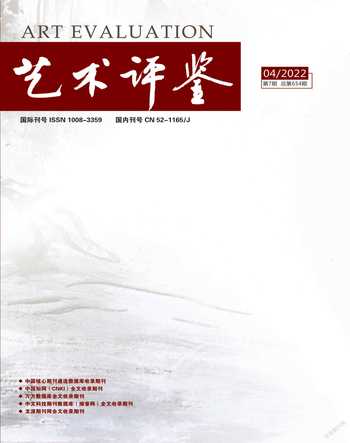介入和參與:中國公共雕塑的時代命題
段冬玲
摘要:公共雕塑藝術(shù)的動態(tài)發(fā)展是社會政治與歷史巨變的直接反應(yīng)。對社會問題高度敏感并保持深刻自省的藝術(shù)家有責(zé)任以介入社會問題的自覺性參與公共雕塑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研究。廣泛合作和公眾的深度參與是公共雕塑藝術(shù)實現(xiàn)其功能和價值的有效途徑。公眾的精神文化訴求和當(dāng)代藝術(shù)觀念的結(jié)合,是處于深刻社會變革期的新時代中國對公共雕塑藝術(shù)的內(nèi)在要求。
關(guān)鍵詞:公共雕塑? 位置? 社會問題? 公眾參與
中圖分類號:J0-05? ?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2)07-0172-04
什么是公共雕塑?相對于可以出現(xiàn)在任何地方的其它雕塑來說,公共雕塑是有特定的位置,占有公共空間,為公眾集體擁有,并持續(xù)產(chǎn)生公共話題的雕塑藝術(shù)作品。公共雕塑是社會環(huán)境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qū)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公共雕塑的根本意義不在于風(fēng)格、形式、材料以及裝飾的趣味,而在于其所處的特定位置,以及由此建構(gòu)的公共精神場域。在全球化飛速發(fā)展的21世紀(jì),新國際關(guān)系的變化使不同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更加劇烈也更加廣泛,藝術(shù)介入社會成為藝術(shù)家、社會學(xué)家熱烈討論和積極實踐的國際化問題。在中國持續(xù)向世界開放、城市化進程日益加速和鄉(xiāng)建計劃蓬勃開展的時代潮流中,如何在大眾文化盛行的社會環(huán)境中創(chuàng)新人文交流方式,喚起民眾深層次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新時代中國公共雕塑藝術(shù)的重要課題。作為公共雕塑藝術(shù)實踐的主體,敏感且自省的藝術(shù)家對于藝術(shù)的社會價值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成為其積極介入社會問題討論,以合作者的姿態(tài)參與公共雕塑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自覺要求;另一方面,公眾和公共雕塑的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公眾正從公共雕塑藝術(shù)的“觀看者”轉(zhuǎn)變?yōu)楹献髡吆蛥⑴c者。
一、公共雕塑的地域特定性
公共雕塑因其位置的特定性而與公眾建立起一種公共關(guān)系,生發(fā)穩(wěn)定的社會輿論,進而激發(fā)集體感情,并因此產(chǎn)生關(guān)于集體責(zé)任的意識。無論是有宏大敘事的廣場紀(jì)念碑雕塑,美化城市的景觀雕塑,還是服務(wù)于社區(qū)和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的生活主題雕塑,都因其地理位置的特定性和公眾集體擁有的權(quán)利屬性,確定了它們不同于其它形式的雕塑和其它形式的公共藝術(shù)的特質(zhì),也因此對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方案提出了限制性的要求。安德魯·考西在《西方當(dāng)代雕塑》一書中論述了1951年不列顛節(jié)的《云霄塔》和同時參展的其它雕塑作品相比較所具有的公共雕塑的特質(zhì):“大量的公共工程滿足于各種雕塑的創(chuàng)造,但沒有一件作品的地位能比云霄塔更重要,它證明了英國在技術(shù)與科學(xué)上的威力。——云霄塔有它的位置,其他雕塑卻無立足之地,從這層意義上說,它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只是碰巧出現(xiàn)在了那個位置。”①同時期最大規(guī)模的國際雕塑競賽獲獎作品《無名政治受難者紀(jì)念碑》,作為“無地點”“可轉(zhuǎn)移”的現(xiàn)代主義雕塑,最終因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和公眾的民族主義立場,既沒有矗立在英國的多弗爾懸崖上,也沒有能夠成就西柏林欲將其矗立在洪堡山以挑戰(zhàn)特累普陀公園蘇軍紀(jì)念碑的野心。和短期的偶然出現(xiàn)在某個公共場所的雕塑相比較,公共雕塑不是空降的外來物種,而是與生活在特定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中的民眾的“共生之物”。明確的地理位置關(guān)乎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共識,就像布朗庫西安放在特爾古日烏的《沉默桌》和《無限柱》,不僅是現(xiàn)代主義雕塑的典范,它們還關(guān)聯(lián)著羅馬尼亞人的生活日常和抵御入侵的歷史過往。
優(yōu)秀的中國公共雕塑藝術(shù)無不向公眾傳達著清晰的地域文化特質(zhì)和人文精神:位于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jì)念碑浮雕》,向世界講述著百年間中國人民為謀求民族獨立和自由幸福不懈抗?fàn)幥笕倮钠D難歷程;位于蘭州的《黃河母親》象征著華夏大地生生不息源遠流長的黃河文化;深圳市的《深圳人的一天》展現(xiàn)了新千年深圳人陽光自信的生活狀態(tài);《王府井街頭雕塑》將老北京市井文化的歷史和新北京的日常生活進行了有效的聯(lián)結(jié);《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組雕》警示和平時代的人們勿忘六朝古都曾經(jīng)遭受外侮的慘痛歷史;甘肅瓜州的戈壁灘上,《大地之子》成為古老的絲綢之路上聯(lián)結(jié)東西方文明的新地標(biāo)。無論是在首都的中心廣場,還是在城市的街區(qū),以及荒悍的戈壁沙洲,成功的公共雕塑總能與那個區(qū)域的環(huán)境、歷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建立起有效的關(guān)聯(lián),和公眾產(chǎn)生對話與互動,共同建構(gòu)充滿人文情懷的精神坐標(biāo)。
二、公共雕塑與社會問題介入
藝術(shù)家作為公共雕塑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主體,其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決定著公共雕塑的審美品質(zhì)和深層次的文化意義。藝術(shù)家如何看待藝術(shù)與社會、藝術(shù)與公眾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介入社會問題的討論,如何把諸多公共因素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語言,使環(huán)境、作品與公眾之間產(chǎn)生共鳴,是公共雕塑能否發(fā)揮社會職能、實現(xiàn)社會價值的關(guān)鍵。當(dāng)代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要求藝術(shù)家在參與公共雕塑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以自覺的態(tài)度介入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和判斷,并致力于將公共雕塑創(chuàng)造成話題中心。
英國藝術(shù)家杰瑞米·戴勒說:如果你是一位出色的藝術(shù)家,你就是介入社會的,無論你創(chuàng)作的是繪畫還是雕塑。藝術(shù)家對社會的關(guān)懷是成為偉大藝術(shù)家的條件。我們?nèi)绻褗W登伯格設(shè)計的公共雕塑——那些建筑般矗立在城市空間中的“日常用品”羅列出來,簡直就是一個美國人出入商超的購物清單:針線、手鋸、印章、衣夾、口紅、別針、羽毛球、車輪、火柴、冰激凌、油畫刀、湯勺和櫻桃以及手鉗和錘子……藝術(shù)家以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美國消費文化的關(guān)注與思考,并與公眾建立近乎親密的聯(lián)系。“我們的確在這些東西上傾注了宗教情感,看看星期日報紙廣告上描繪的東西多美……畢竟,物質(zhì)造型也就是身體造型,是由人類創(chuàng)造的,充滿了人類情感的崇拜對象”。②雕塑家諾切和埃斯特·吉爾茲夫婦在1986年為德國漢堡郊區(qū)的小城哈爾堡設(shè)計了一座可以沉入地下的《哈爾堡反法西斯紀(jì)念碑》,一根1米見方涂滿鉛粉的空心鋁殼立柱,并在旁邊設(shè)置了公告欄:“請哈爾堡的市民和這座城市的游客,在塔上留下您的姓名。帶著很多人的名字,這座高12米的塔將會逐漸下沉到地下。直到有一天塔會完全從我們的眼前消失,到時候我們再也見不到紀(jì)念反法西斯的這座塔。因為對抗非正義需要站起來的終歸還是我們自己。”③超過7萬多名市民和游客在紀(jì)念碑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關(guān)于納粹的傷痛記憶,其中也不乏少量贊頌納粹的反文化涂鴉。《哈爾堡反法西斯紀(jì)念碑》每年以2米的速度下沉,六年之后,只剩下1米見方的塔頂與地面持平。在地勢稍低一點的地鐵入口處,人們可以通過小玻璃窗看到下沉到地下的塔的形狀。公眾的參與實現(xiàn)了關(guān)于爭論和開放的設(shè)計意圖,雕塑家的個人表達終結(jié)于公共輿論的自然生成。
公共雕塑藝術(shù)的發(fā)展直觀地反映著一個國家和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文化脈絡(luò)和精神信念的歷史巨變。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中國公共雕塑不再僅僅是國家權(quán)力和政治意志的形象代言,藝術(shù)的主題從宏大的英雄頌歌轉(zhuǎn)向?qū)κ浪咨畹默F(xiàn)實關(guān)照。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從制作服務(wù)于政治宣傳和思想教化的紀(jì)念碑雕塑,到承擔(dān)服務(wù)于城市建設(shè)的景觀藝術(shù)工程,不論形式語言還是主題內(nèi)容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在深層次的思想解放和大眾文化蓬勃發(fā)展過程中,藝術(shù)家個人化的思想觀念和形式語言得以自由發(fā)揮,由政府和企業(yè)家資助的雕塑公園建設(shè)以及各種形式的公共藝術(shù)活動遍地開花,美化環(huán)境一度成為公共雕塑的首要職能,城市公共空間成為精英藝術(shù)家個人藝術(shù)觀念的戶外雕塑展廳。在“回避社會苦難、拒絕歷史記憶、放棄對于邊緣、底層和野地的人文關(guān)懷、在自我迷戀中尋找專利圖式,以適應(yīng)海內(nèi)外藝術(shù)市場和媒體傳播的需要”④的藝術(shù)環(huán)境中,“形式自由成為藝術(shù)自由的標(biāo)準(zhǔn),個人表現(xiàn)成為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價值準(zhǔn)繩”⑤。大量自以為是的雕塑以侵略性的姿態(tài)植入公共空間,公眾作為公共雕塑藝術(shù)最重要的權(quán)屬主體失去了立場。失語于無法理解的深邃與高雅,被強制觀看還無法脫離現(xiàn)場的觀眾在疑惑中保持著習(xí)慣性的集體沉默。鑒于此種普遍的現(xiàn)象,自省的藝術(shù)家和敏感的批評家開始質(zhì)疑和討論公共雕塑的社會價值和根本意義所在。
藝術(shù)家從事公共雕塑藝術(shù)創(chuàng)作必然要面對特定地域內(nèi)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政府、投資方、公眾、地理環(huán)境、文化歷史等,這就要求藝術(shù)家要以自律的姿態(tài)介入當(dāng)?shù)厣鐣瞵F(xiàn)實。1999年大連市為紀(jì)念建市一百周年建造的公共雕塑《百年之路》,就是藝術(shù)家將公共雕塑的主題性、功能性、紀(jì)念性和審美統(tǒng)一起來,建構(gòu)起環(huán)境、作品與公眾之間良好的互通對話關(guān)系的成功案例。藝術(shù)家對大連的百年歷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從俄國人占領(lǐng)大連建立港口,以及之后的日俄戰(zhàn)爭,到解放后的和平建設(shè)以及改革后的面貌更新,只能用一種宏觀的概念——一路前行中的繁衍、壯大和聚集來體現(xiàn)。這個概念的最終呈現(xiàn)方式是,在開闊的星海灣廣場上,一條80米長的青銅道路深印著從百歲老人到新生嬰孩的廣大民眾的足跡,走向遠處海邊一本平面展開的巨書。《百年之路》以帶著民眾體溫的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結(jié)隊前行的腳印打動著大連市民和外來游客的心,環(huán)境、藝術(shù)、歷史、文化與現(xiàn)實問題得到持續(xù)的充分的討論。
21世紀(jì)的中國是多元的市民社會逐步形成的重要時期,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社會轉(zhuǎn)型是中國公共雕塑藝術(shù)家無法回避的時代課題。“當(dāng)代藝術(shù)向生活現(xiàn)實和大眾文化的拓展,意味著藝術(shù)家改變現(xiàn)代主義的個人化的形式追求,更加看重藝術(shù)和他人的交流、和社會的互動”⑥。在參與社會文化建設(shè)的過程中,藝術(shù)家必須反省自身的存在以及和大眾溝通的方式,以轉(zhuǎn)變藝術(shù)觀念和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的自覺和自律規(guī)避藝術(shù)因思想對立而被拒絕、因不相融合而被疏離的窘境。公共雕塑既是藝術(shù)家獨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和獨立思想觀念的延伸和放大,更是影響和傳達特定區(qū)域深層次社會價值觀念的物質(zhì)載體。因此,自覺介入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的討論,積極回應(yīng)公眾的藝術(shù)需求,著眼于公眾的文化生活利益,是倡導(dǎo)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新時代對中國公共雕塑藝術(shù)家的現(xiàn)實要求。
三、公共雕塑與公眾參與
公共雕塑的所有權(quán)屬于公眾。公眾在參與公共雕塑藝術(shù)建設(shè)的過程中,通過建言發(fā)聲,合作交流,能夠產(chǎn)生既私密又可以共鳴的經(jīng)驗,使公共雕塑作為存續(xù)和協(xié)調(diào)人與人、人與自然及人文環(huán)境之間密切互動關(guān)系的媒介,超越純粹的形式美學(xué),成為文化精神的載體。漢娜·阿倫特說,我們身邊的事物通過某種形式才能呈現(xiàn)自身,而藝術(shù)的唯一目的就是使這種形式呈現(xiàn)出來。⑦
積極倡導(dǎo)“社會雕塑”的約瑟夫·博伊斯在1982年的《給卡塞爾的7000棵橡樹》計劃中,號召完成了7000人次的“種一棵樹,立一塊石頭”的儀式性藝術(shù)行動,并將其闡述為“對于所有摧殘生活和自然的力量發(fā)出警告的行動”。“重要的是,一個護士或農(nóng)夫的能力是否能轉(zhuǎn)為創(chuàng)作的力量,并把它視為生命中必須完成的藝術(shù)課程。”⑧橡樹被視為日耳曼人靈魂的象征,7000棵橡樹代表7000個個體的自由意志植入卡塞爾城,并在復(fù)雜的社會生活中喚起個體參與公共藝術(shù)計劃的記憶。
20世紀(jì)90年代初,參與性公共藝術(shù)開始在全球盛行。從美國到東南亞,從歐洲到俄羅斯,雖然被冠以各種名稱:“對話藝術(shù)”“介入主義藝術(shù)”“社區(qū)基礎(chǔ)藝術(shù)”“合作藝術(shù)”等等,但都以群體性或多人參與合作為共同特征。1990年,策展人馬麗·簡·雅各布發(fā)起一個大型的“文化在行動”的主題性展覽,展覽旨在以“藝術(shù)介入社會”的方式,鼓勵藝術(shù)家以全新方式與社會、政治、族群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并動員社區(qū)居民積極參與進來。在藝術(shù)家和民眾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民眾從沉默被動的接受者轉(zhuǎn)變?yōu)榉e極主動的合作者和參與者,并對參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行為和作品的最終實現(xiàn)充滿了責(zé)任感和榮譽感。
桑德蘭是英國北部一個擁有河流、海岸線和美麗海灘的城市,同時也是曾經(jīng)的造船業(yè)和玻璃手工藝重鎮(zhèn)。1991-2001年間,雕塑家Colin Wilbourn、作家Chaz Brenchley和桑德蘭本地居民共同完成了一條雕塑小徑——沿威爾河入海口一公里長、由多組不同主題雕塑組成的圣彼得河畔雕塑項目。雕塑項目通過報紙廣告招募到作家Chaz Brenchley參與駐地創(chuàng)作,為每一組雕塑寫作充滿故事性的文字片段,作為跟雕塑相聯(lián)結(jié)的隱晦的神秘線索,用鋼板蝕刻或混凝土澆鑄,與雕塑共同呈現(xiàn)。參與創(chuàng)作的桑德蘭居民包括16位從事地方史工作的成員、來自四個小學(xué)的五、六年級的小學(xué)生以及手工作坊的盲人和弱視者。不同的雕塑主題涉及桑德蘭在二戰(zhàn)中遭受德軍轟炸的歷史,輕松稚趣的海洋故事,對城市四季生活的贊美和懷念,以及孩子們充滿勇氣和冒險精神的小童話。參與的居民在雕塑家的幫助下創(chuàng)作完成雕塑,或安置在河畔的騎行通道邊,或以浮雕的形式鑲嵌在社區(qū)的圍墻上。無論當(dāng)?shù)氐木用襁€是度假的游客,都可以停下腳步走近雕塑,還可以走進去,坐下來,通過撫摸和閱讀感受和研究桑德蘭的故事。樸素的雕塑無聲地散發(fā)著古老又年輕的桑德蘭的溫度,而參與雕塑創(chuàng)作的居民,十幾年來無論是否遷居到了他處,威爾河畔的雕塑成為他們永遠的精神棲息處。
參與,能夠使藝術(shù)和公眾之間構(gòu)成雙向交流關(guān)系,并與良性政治體制互為印證,以藝術(shù)的力量增強民眾文化自信,推進社會公平。國際化的參與性公共藝術(shù)活動,在新千年的中國也得到了快速回應(yīng),并且在發(fā)生著巨大變革的中國特色的社會環(huán)境中,呈現(xiàn)出從城市社區(qū)到偏遠鄉(xiāng)村的發(fā)展趨勢。
中國公眾參與公共雕塑項目的歷史可追溯到20世紀(jì)50年代的人民英雄紀(jì)念碑的設(shè)計與建造。1953年興建委員會將設(shè)計模型和不成熟的畫稿在天安門廣場面向公眾進行公開展覽。“這次展覽的目的,就在介紹上述設(shè)計工作的演進進程和一些尚未完全成熟的畫稿草案,我們誠懇地期待著你們寶貴的意見。”⑨群眾的意見得到充分尊重,一些建議被采納并最終得以體現(xiàn)。2000年6月落成于深圳的《深圳人的一天》,是體現(xiàn)著當(dāng)代參與性公共雕塑方法論的典型案例。這個大型公共雕塑項目的參與者除了深圳雕塑院的雕塑家,還有建筑師、媒體記者以及來自深圳各行業(yè)的普通勞動者:清潔工、公務(wù)員、設(shè)計師、包工頭、打工妹等,其中還有外國人的參與。這些勞動者的形象和他們的姓名職業(yè)等信息通過模制鑄造放置在社區(qū)的浮雕背景墻前,浮雕墻上鐫刻著日常生活的各種信息:電視節(jié)目、蔬菜價格、體育賽事等等,普通人和他們的生活日常成為雕塑的主體,參與者清晰的身份特征和充滿自信的精神氣質(zhì)成為深圳這座快速崛起的新移民城市展現(xiàn)給世人的最真實的面貌。《深圳人的一天》因公眾的深度參與:從規(guī)劃設(shè)計到制作呈現(xiàn),以及持續(xù)的社會評價和討論,使公眾的主體意識得到前所未有的體現(xiàn),公共雕塑與社會生活完美的聯(lián)結(jié)在一起。2011年落成于北戴河火車站廣場的《對接·啟程》,是一件將進入現(xiàn)場的觀眾巧妙地轉(zhuǎn)化為作品的一部分的公共雕塑。作品將火車站、老式火車、北戴河的歷史人物、現(xiàn)實世界的過客匯集一處,建構(gòu)成一個產(chǎn)生對話和交流的公共場域。“演員和觀眾在看與被看的過程中參與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只要是進入這個場景中的公眾,都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參與者。”⑩
2010年以來,方興未艾的中國新鄉(xiāng)村文化建設(shè)使參與式公共藝術(shù)的社會實踐得以從大城市到小城鎮(zhèn)再擴展到鄉(xiāng)村和田野,公共雕塑也成為當(dāng)?shù)孛癖娕c世界對話的開放性資源。藝術(shù)助力社區(qū)改造和鄉(xiāng)村建設(shè)的活動,主要由美術(shù)學(xué)院師生和一批具有前瞻視野的藝術(shù)家群體主導(dǎo),并鼓勵和吸引當(dāng)?shù)鼐用駞⑴c其中,在充分尊重特定區(qū)域居民生活和文化傳統(tǒng)的前提下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yīng)。在2018年首屆“守望原鄉(xiāng)-2018廣安田野雙年展”上,王度以《龍女的簪子》幽默地回應(yīng)了當(dāng)?shù)馗挥刑厣霓r(nóng)耕文化、鄉(xiāng)土文化和院落文化。他根據(jù)當(dāng)?shù)亍褒埮路病钡膫髡f偽造了一個考古現(xiàn)場,讓龍女遺落在人間、千百年尋而未得的巨型發(fā)簪出現(xiàn)在考古坑底。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吸引了大批的觀眾趕往現(xiàn)場,當(dāng)?shù)氐臍v史文化、風(fēng)土人情以可視的形象和樸素的語言與當(dāng)?shù)鼐用褚约巴鈦碛慰彤a(chǎn)生了強烈共鳴,也由此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話題,并以其永久存在的區(qū)域位置的特定性顯現(xiàn)出公共雕塑向鄉(xiāng)村發(fā)展的新方向。
基金項目:本文為河北省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的研究成果,項目名稱:文化自信與新時代公共藝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項目編號:HB20YS028。
①(英)安德魯·考西:《西方當(dāng)代雕塑》,易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頁。
②(美)奧登伯格:《地點與建筑雕塑》,何尚主編,《接近天堂的美》,南寧:廣西經(jīng)濟出版社,第305頁。
③(韓)承孝相:《古老之美 承孝相的建筑旅行》,李金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91頁。
④王林:《如何談?wù)撝袊漠?dāng)代藝術(shù)》,賈方舟主編:《2007中國美術(shù)批評家年度批評文集》,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7年,第57頁。
⑤王春辰:《“藝術(shù)介入社會”:新敏感與再肯定》,《美術(shù)研究》,2012年,第4期,第27頁。
⑥王林:《如何談?wù)撝袊漠?dāng)代藝術(shù)》,賈方舟主編:《2007中國美術(shù)批評家年度批評文集》,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7年,第59頁。
⑦(美)漢娜·阿倫特:《文化的危機》,轉(zhuǎn)引自卡特琳·格魯:《藝術(shù)介入生活》,姚孟吟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147頁。
⑧(法)卡特琳·格魯:《藝術(shù)介入社會》,姚孟吟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110頁。
⑨殷雙喜、翁建青、唐堯、陸軍、孟繁偉:《公眾視野與文化沖突——關(guān)于雕塑的深度對話》,《美術(shù)觀察》,2011年,第7期,第9頁。
⑩孫振華:《中國當(dāng)代雕塑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第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