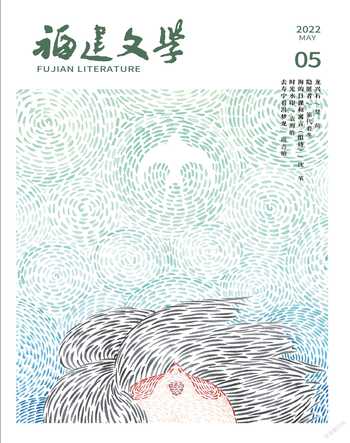卷首語
有學者對當下小說詩性品質的缺失做過恰當描述:“一些作品過分注重對于真實的開掘和敘寫,偏執地沉溺于故事性追求,而缺乏或者忽略將其提純為藝術的手段和能力,以至于作品幾近于新聞、紀實等體式”,“某些小說創作者似乎過度熱衷于書寫‘惡與‘丑,而忽略了對于‘美的發掘”,“過分注重故事性,則往往忽視或者漠視語言。準確性欠佳、冗長、粗鄙、直露的語言在小說文本中大行其道”。(仕永波《光明日報》)
此言真矣。何為小說的詩性?如何寫出?是小說寫作的大問題。
昆德拉將詩性定義為一部小說所能“接受的最高苛求”,他還提出“小說是關于存在的一種詩性思考”。這里說詩性,是廣義的,“不是指將小說抒情化”,昆德拉明確指出“小說是反抒情的詩”。詩性是一種藝術追求的范疇,可以說,藝術的高級屬性是詩性。小說的詩性是指小說的靈性,是輕逸之美,從語言到現實到意象都樸素而脫俗,它的對立面是小說的通俗性、庸俗性和媚俗性。對讀者而言,詩性是精神的彼岸,是“詩無達詁”,是一種觸及內心和靈魂的審美沖擊力。簡言之,詩性是作品藝術性高低、強弱的刻度。昆德拉認為,小說的詩性就表現幾個方面:“超越一切之上尋找美”的意圖;每個特殊字詞的重要性;文字強烈的韻律;適用于每一個細節的獨創性要求。今天看來這幾條詩性準則仍然沒有失效,順著它們標識的路標而行,我們仍然可以抵達藝術的終點站——那個稱為詩性的地方。
本期“重點推介”推出楚荷的中篇《龍興石》,這篇現實性突出的小說重拾中國小說的諷刺傳統,對某類文人的文品和人品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畫。程迎兵、第代著冬、李文鋒等新一代小說中堅力量亮相本期。俗話說距離產生美,外地作家寫本土題材和本土作家寫本土題材還真不一樣,比如本期散文《去壽寧看馮夢龍》,是浙江作家寫福建題材的作品,那種敏感度和切入視角就不一樣。這種寫作態勢或許會給我們某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