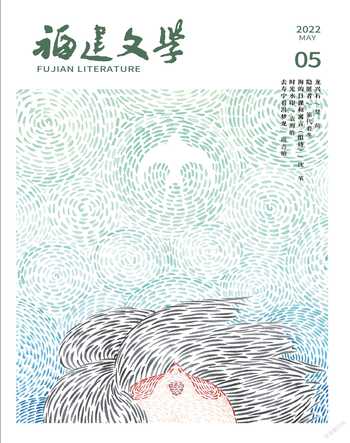別人的世界
麥冬
一
黃披星在出了一本詩集、一本隨筆,又在《長江日報》開了幾年專欄后,寫起了小說,讓很多人感到有些意外,不過,對他來說這完全是一個深思熟慮的結果。在創作談《窗外的世界》中他談到了自己從詩歌寫作轉向小說寫作的原因:“從某種程度來說,詩歌只要一個人也就是只要關注自己就可以完成;雖然真正好的詩歌也是需要對人世的洞察和對自然的依戀,但這還是可以在完善自我的過程中完成。小說基本不行,它很需要對‘我之外’的事物的關注。從‘我’身上走到‘他’身上,是關于時間的跋涉。或者說到一定的階段,詩歌的容量似乎不夠了,還需要更加具有文字體量的東西來描述自我。這大概就是小說生成的起因。”
讀黃披星的小說,經常就會有這樣的想法跳出來,哦,他寫的就是我的阿姨、姑媽、堂姐啊,我沒能寫出來,被他寫出來了。確實,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這些人好像就是我們身邊的人,他說的都是我已經知道的內容,他的那些人物都是我的左鄰右舍,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
他的故事也都很簡單,沒有大起大落,也沒有大奸大惡,看上去就是生活的“原生態”。奇怪的是,我們并沒有因為他沒有為我們提供“傳奇”感到不滿,我們好像滿足于他這種沒有想象力的誠實,這些幾乎稱不上故事的故事都已經讓我們心滿意足了,并心甘情愿地讓他帶著走入一個又一個心事重重的人物的內心世界。我們沉浸在他的敘事中,沉浸在那些人物的屈辱、委屈、苦悶、頑強,還有他們高超的“自我平衡能力”中。故事結束了,我們會覺得他說的這些不完全是虛構,看上去就像是真的似的。這種閱讀反而是愉悅的,我覺得這種愉悅來自作者的真誠,來自他帶給我們的一種自然、真實的感覺。
我們知道在《飛天的腳印》中有非虛構的因素,在黃披星其他的小說中也或多或少可以找到類似的成分。熟悉黃披星的朋友,只要讀了《漁村客運》,不難猜測到小說中的碼頭就是“石城”碼頭,有一段時間,他就在碼頭附近的學校里上班,這段從碼頭到鎮上的路途,他再熟悉不過了,加上他對場景的天生感受力,他筆下的碼頭、漁村、鄉村公交車這些相關的環境也寫得具體而真切,讓你覺得就是生活本身,它不是畫上的布景,也不是臨時搭就的舞臺。當然,他也展示了出色的對人物的觀察與描繪能力,往往寥寥幾筆,司機、乘客、售票員,他們的外貌特征與道德品性全都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
黃披星曾在一篇隨筆中思考過“何謂真實”:“何謂真實?關注人:捕捉行為、細節、表情、話語,想象它;延伸到自然之物,對草木花葉,鳥獸蟲魚,安詳對話交換呼吸;細節的準確,會帶來神奇的過程;樸實,就是對語言的最大敬重;唯有真實才能抵達語言的核心……”
什么是真實?如何去表現真實?本來就存在著許多分歧,因為這些分歧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文學流派,不過,有一點倒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你是否有真實表達的誠意。在黃披星的寫作中,我們看到了這種誠意,這種誠意首先表現在他在描寫事物或者人物的時候,展示的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一視同仁;這種誠意還表現在他如何處理作品和他自己個人體驗的關系上,在黃披星的小說里,他的自我是敞開的,許多人物身上都留下他真切的生命體驗,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物也充滿了不尋常的生命力,而這也正是小說家對人物與讀者的雙重的真誠。
通常來講,作家會選擇自己熟悉的,同時也比較認同的人物去描寫,這樣會更容易產生移情,也更容易激起自己表達的沖動。黃披星在農村出生,在農村長大,除了出外求學的幾年時間,他基本上都生活在農村,大學畢業從學校回來后,他也長期在鄉村學校教書,所以有非常真切實在的農村與城鎮生活的經驗,而他寫的也正是這些。
二
在黃披星的作品里,常常由“我”直接來敘述,你甚至可以把這個“我”看作作家本人,他不但是事件的旁觀者,更是事件的參與者。而那些看上去是客觀的、甚至全知全能的敘事在他這里也常常帶上了強烈的主觀色彩。這樣的敘述視角,使得作家和讀者的心理距離進一步拉近,這也使得他的許多小說看上去與非虛構作品相當接近。
比如,《村葬》基本上就是一場鄉村葬禮的現場實錄,紀錄片似的冷靜敘事已接近殘酷的生活真相,透露出黃披星對人性悲涼的看法。
“貴萍是后半夜死掉的。這一點基本可以確定,但更具體時間誰也不知道。是凌晨兩點、三點還是四點?——就沒有人知道了。”
這是小說的開頭,有點加繆《局外人》的意思,實際上全文也都彌漫著《局外人》那種零度敘事。小說通篇是不動聲色的語調,完全抽空了感情色彩,你可能感到不舒服,但你又不得不承認,他寫得很真實。為什么會這樣呢?難道我們都變成了冷漠無情的人,變成只會照顧好自己的“肚皮”與“肚腩”的人?難道生存的本能就可以取代一切嗎?就算生存至上,夫妻之間、母子之間,就該如此寡情少義嗎?人心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是一直如此,還是說我們生活的時代確實有些不同?
現在,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打量黃披星筆下的這些人物,考察他與人物的關系,發現他對待人物的態度接近評論家張定浩的一個概念,那就是“哀矜”,這個概念接近我們常說的悲憫,稍有區別的是,這種悲憫中,帶著某種超脫與淡淡的疏離,有點類似于老子說的“不仁”。
在黃披星的作品中,他總能找到人物埋在最深處的“心結”并試著去解開它。但這樣的結,往往不是你把兩端輕輕一拉就可以解開的,相反,你越拉它會扎得越緊。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黃披星表現出了足夠的細心與耐心,而正是在這種細心與耐心中,我們理解了黃披星的小說藝術,也理解了他對筆下人物的真切同情。
黃披星小說里的人物,往往都具有某種典型性。比如《漁村客運》里的亞梅、《園子》里的蘇梅,以及《騎馬下海》中的柳娟、《村葬》中的貴萍等,她們都是農村的普通人物,基本上不是留守婦女就是喪偶女性,可以說都是“沒有男人的女人們”。連她們的名字也不外乎就是梅、萍、柳、蘭,都是我們身邊普通的植物。在面對命運的風雨時,她們總是那副樣子,不抱怨,不瘋狂,不歇斯底里,也遠離了廉價的傷感,她們只有樸素、簡單、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活著,有一個家就好,如果大家平平安安的那就更好了。這個形象代表了什么?到底有什么特殊意義?這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清的,所以黃披星的回答是,把“她”的故事一再重復著講述,在他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復中,“她”成為“她們”,于是,我們發現她們身上的共同點還真不少,知道了她們都是有故事的人,也意識到了她們的命運是與這個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的。也許,這正是黃披星正在思考的東西。
三
2011年8月,黃披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不下雪的城市》,收錄了他早期的大部分詩作,這些作品現在看來有點生澀,傳遞出來的信息也有些含混,但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理性與思辨的色彩。幾年后,他的詩歌風格有了明顯的變化,語言更加平易簡潔,冷靜節制,它所傳達出來的體驗卻更加清晰堅定。在他的隨筆《另一種抵達》中,他談到了自己的詩歌觀念:“詩和音樂,我的一對翅膀”,“我寫作,為了保持清醒”,“我認可詩是加速的思想”,“詩終將為糾正而存在:糾正語言;糾正日常”。這里的關鍵詞是“清醒”“思想”和“糾正”,實際上這不但是他的詩觀,也始終貫穿在他的隨筆寫作中。
2011年的秋天,黃披星離開莆田去寧夏支教,他也把在莆田開始動筆的系列音樂隨筆的寫作帶到了寧夏。在西海固,黃披星陷入了某種沉思,完全處在自己與自己交談的內心對話中。在2011年11月的某一天,他接連寫了三篇隨筆,每一篇里都充滿了反省、抉擇以及近乎慘烈的自我拷問。我很少看到有人如此認真地對待自己,如此嚴肅地面對自己的內心。
不少詩人擁有杰出的批評的才華,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詩人評論的傳統,他們能夠把邏輯思辨能力和詩人的直覺完美結合,他們的判斷往往既快速、直接又清晰、堅定。我注意到了,在黃披星的隨筆中,他選擇了一種更富于挑戰性的語言,但在我看來,還是不夠明晰與通透,行文也稍顯急切、匆忙,跟他自己所期待的從容自在還有一定的距離。黃披星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不過,他認為這與他的“流浪心態”有關:
當我從溫暖的南方來到這酷寒的西北,也會生出某種帶有流浪性質的內心體驗,在一點點文字記錄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流浪的初級階段,我會不知不覺地生出一些很是強硬的心理護欄,以防在對溫情的回顧中變得低沉甚至沉淪。而我發現,這樣的情緒是會帶進文字中的,它會使文字變得急切而又剛性十足。而這,是對表達的積淀缺乏的癥狀,也就是說,在某種遺棄感沒有被克服之前,從容自在的表達變得難以做到。
寫作者面臨的總是全面的考驗,黃披星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新的舊的,前人今人,真實批判,語言形式,傳統現代,國內國際,發現回歸……都是陷阱,不能后退,要踹要蹚,獨立作戰,要尋回自己……”這里他說的是音樂,其實也是詩歌、隨筆、小說等所有藝術共同面臨的處境。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已經別無選擇,他只能不斷地去磨煉自己的寫作風格,不斷地去忍受著自我蛻變的痛苦,不斷地在自己的聲音中尋找另外一種聲音。
這種清醒賦予黃披星一種自我修正與自我變革的能力。他曾經在詩與小說、自我與他人之間完成了一種自我突破,現在他的小說寫作也來到了這一階段。
黃披星之前的小說往往都是日常的、原生態的一些“小事”:遷墓,買塊墓地,一場手術,給小偷或丈夫的情人匯錢,還有公共汽車上的一個小小的插曲等,但這些“小事”卻包含了豐富的經歷與情感,它們給人的感覺是,雖然沒有復雜的故事,卻有復雜的人性,沒有曲折的情節,卻有曲折的人生。
在新近的創作中,黃披星的小說敘事藝術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他的近作中增加了想象與虛構的成分,增加了一些戲劇性甚至傳奇性的成分,人物形象也更加鮮明、獨特。比如《十五廟主》里裝神弄鬼的“老爹”、《盜路者》與《弦上的羽毛》中的兩位失戀者,以及《化蝶》中臉上掛著小丑面具送外賣的小丁。這些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他能很好地把握住人物身上固有的特質,把握住人物的精神活動與內心世界。他總能抓住人物內心的欲望,抓住他想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擔心的是什么、他為何苦惱、他想改變什么。他牢牢抓住了這一點,也就走進了人物最隱秘的內心世界。
以黃披星新近寫的小說《木魚與金魚》為例,小說故事的核心是一個魚缸,這個小小的魚缸卻把兩個家庭的傷痛揭示了出來。于是,我們在平常甚至庸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中,看到了不平常的行為和感情,看到了一位越走越遠的“妻子”,一位“準出家”狀態的“老爹”。我們看到,他們在默默地品嘗各自的人生滋味,承受著各自日常生活的沉悶單調,最后帶著各自的失落與失望各奔東西。小說實際上寫的是兩個小家庭瓦解崩塌的過程。黃披星的敘述客觀節制,只在小說的最后,才流露出壓抑已久的內心情感。
黃披星是個生活的有心人,這雖然是句老話,但在他的作品中,再次印證了這句老話不老,也再次印證了,只有能夠設身處地、像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那樣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才是一個小說家最重要的天賦。黃披星總能很好地進入人物的內心深處,這樣我們在閱讀他的小說的時候,也就不知不覺間跟著他走近他人,走進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內心世界。我們閱讀的時候,突然間感到自己的內心翻騰著與小說中的人物同樣的屈辱、悲傷、無助、委屈與憐憫。
“人如其名”,在日常生活中,黃披星總是那么的勤奮、專注,給人一種“披星戴月”的趕路人形象。現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就要出版了,而他的手頭還有一部長篇小說也正在修改中。可以說,他已經找到一塊屬于自己的領地,找到一種屬于自己的觀察世界的方式,他的寫作也因此擁有了更大的空間與更多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 李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