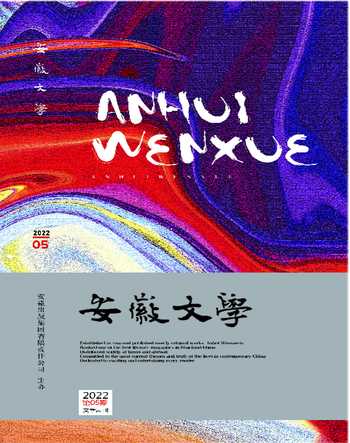遙遠的牽手
司玉笙
初秋的陽光下,那個老男人已在村外的小河邊徜徉許久。
河邊有幾行桑樹,其中兩棵最粗壯。那人就在林間出出進進,而后站在河堤上來回端詳,掏出手機換著角度拍照,好像在考察什么。有路人經過,他就問,你是樂桑村的嗎?
路人看看他,用當地方言回了一句,就過去了。他聽得懂,就輕嘆一聲,再往村里望一眼……
幾十年前,一個男孩作為下鄉知青,插隊落戶到這個村。這男孩會唱歌會譜曲,大隊文藝宣傳隊就把他作為骨干使用。每到農閑,宣傳隊就到各生產隊巡演。演出結束往往都過了午夜。知道男孩一個人住在牛屋旁的倉房里,大隊專門安排生產隊指定一戶社員負責男孩的夜飯。
那戶社員家與牛屋就一路之隔。夜間演出回來,院門總是虛掩著的,輕輕一推就開了——這是事先約定好的。
摸進廚房,飯菜就蓋在地鍋里,端起來還熱。每吃到嘴里,耳畔就想起這戶女主人的聲音,別嫌糙米粗豆,要得管你個飽!除了女主人,還有一個女孩脆亮的聲音飄過來,小王哥,得空了也教教俺唱歌。
那時候,女孩正上初中,放學回來就幫女主人做飯洗衣喂豬,采桑養蠶也是一把好手,村里人都喊她佃妹子。
那天夜里回來后,男孩依舊去那院里取飯,當掀開鍋蓋時,一股熱氣帶著異香直撲鼻面,端起來一看,除了兩個米團,還有大半碗炕好的蠶蛹子!
男孩捧著碗正在發愣,忽聽得院子里有什么響動,抬頭一看,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消失在正屋門內。
幾天后,他遇見佃妹子,說,那天的蠶蛹子真好吃。
對方笑笑,看看四周低頭不語。
他又問,你喜歡唱歌?
娘說了,想唱歌到桑樹底下去,風一吹,那就是最好的歌。
哦,我明白了。
第二年開春,男孩從城里帶回來一棵桑樹苗,栽到小河邊。有人問起,他就說,這是新品種,長大了,風一吹就唱歌。
不過兩年,那桑樹已拳頭粗,枝條蓬散,形似妙傘;葉子寬闊,如同神掌。而最先采摘這桑的就是佃妹子。她邊采邊唱,聲如暖風拂耳。
就在這年冬天,男孩穿上了綠軍裝,戴上大紅花去部隊了。
上高中的佃妹子放寒假回來方知此事,就問娘,小王哥走時誰送他哩?娘說,能去的都去了。咱家沒給他送個啥?送了,一捧蠶蛹子。熱的涼的?涼的,放心窩里焐焐就熱了。
佃妹子聽了,扭臉跑回屋里。
次年春,那棵桑樹旁又多了一棵同品種的樹苗。一高一矮,迎風含首相揖,枝頭觸碰猶如大手牽小手……
佃妹子,你還好嗎?
屏蔽回憶,老男人突然對著桑林大喊一聲,好像要喚回那個遠去的歲月。
你這一喊怪嚇人的!一個聲音在背后說。
扭頭一瞧,是一位老農,騎坐在一輛老舊的三輪車上,也在看樹。倆人眼光一碰,同時發問,你是?
相互一抖身份,老農驚訝得上眼皮都斜了,急急地跳下車。哦,你就是那個會唱會彈的小王!
你就是會計毛蛋哥!
四只手緊緊地搦在一起,道道青筋蚯蚓似的鼓動。
老了哩,要不報出名兒,就是臉碰臉也不敢認。退休了,你才有空兒來?
是晚了些……佃妹子她現在怎么樣?
哦,她現在是個大醫生,奔武漢抗過疫哩……那時候,她就知道怎么防病,生產隊的蠶房讓她把得可嚴咧……你夜里回來能吃上熱飯熱菜,都是她不斷鍋底火,怕涼了傷胃……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我也是后來聽她娘說的。她娘還說,你要是個女娃多好,吃住都可在她家。
老人家現在哪兒?
早被佃妹子接省城去了。
她家、還有那牛屋呢?
哪還有啥的牛屋土房?你瞧瞧,一碼色的紅磚樓房和蠶房,哦,這樹還在……第一棵是你栽的,第二棵是她上大學那年栽的——不得了,高考復來第一年她就考上了醫學院。
不是復來,是恢復。
反正就是那意思——恁這一開頭,誰家只要有當兵走的,考上大中專的,都要在這兒植一棵桑。沒事兒我就過來看看,摸摸樹心里就暖暢。
明年我定帶孩子來多栽幾棵。
好,好哇。
說話間,兩個老男人已身入桑林。走到佃妹子那棵桑樹前,當年的男孩張開雙臂緊箍樹干,花白的頭顱抵在上面蹭磨,簌簌有聲。嗚咽中,吐出一句誰也聽不清的話。
兄弟,你說啥哩?
我,我一次也沒牽過她的手,不敢……
老會計長嘆一聲,拉起他手引向那第一棵樹,倆人伸展的手臂頃刻將兩棵樹牽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