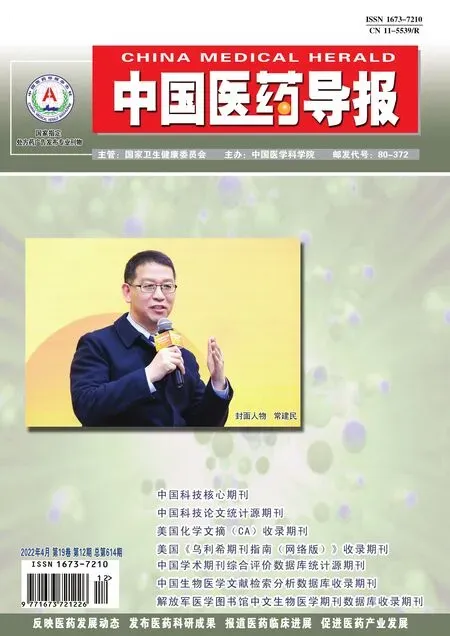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早期與晚期被動運動康復療效比較的meta 分析
高 凱 王小菲 李玉福 王華軍 高彥平 鄭 偉 李 嘉 李 玲
1.石家莊市第三醫院骨科,河北石家莊 050000;2.暨南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骨科,廣東廣州 510630;3.廣東省人民醫院風濕免疫科,廣東廣州 510080
肩袖損傷是導致肩關節疼痛的常見病因之一[1-2]。有統計數據表明65%~70%肩關節疼痛與肩袖損傷有關[3-4]。術后科學合理的康復訓練是關節功能恢復的重要保障。不當的康復方案必然造成術后關節僵硬等并發癥,發生率可達4.9%~23.2%[5-6]。傳統康復方案需在術后肩關節制動6~8 周,而加速方案最快允許術后第1 天開始各方向的被動運動,兩種方案時間相差較大,缺乏循證醫學證據。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從關節活動度、關節功能和肩袖再撕裂等3 個方面系統評價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早期與晚期被動運動兩種康復方案,為肩袖修復術后患者提供有效、科學、適時的康復方案。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及排除標準
1.1.1 研究對象 肩關節鏡探查1 條或以上肩袖肌腱全層撕裂的患者,年齡>18 歲。肩袖撕裂大小及縫合技術不限。
1.1.2 干預措施 早期被動運動組為術后2 周內開始肩關節被動運動,晚期被動運動組為術后4 周之后開始肩關節被動運動。
1.1.3 結局指標 ①術后12 個月時肩關節的最大前屈角度;②術后12 個月時肩關節的最大外旋角度;③術后12 個月美國肩肘外科協會(American Shoulder and Elbow Surgeons,ASES)評分[7];④術后12 個月簡明肩關節功能測試(simple shoulder test,SST)評分[8];⑤末次隨訪肩袖再撕裂發生率,末次隨訪時間≥12 個月。
1.1.4 納入標準 ①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②年齡>18 歲;③關節鏡下行肩袖修復術;④1 條或以上肩袖肌腱全層撕裂;⑤中英文文獻。
1.1.5 排除標準 ①作者針對同一主題多次發表相關研究,僅保留最新一次研究;②文獻質量得分差者(使用Cochrane 手冊評價工具進行偏倚風險評價,文獻質量等級為“C”);③從文獻中無法獲取數據者。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Cochrane Library(2021 年5 期)、PubMed、中國知網、維普、萬方及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搜集關于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早期與晚期兩種被動運動療效的RCT,檢索時限設定:從數據庫提供的最早時間至2021 年5 月。中英文檢索策略如下:中文檢索策略:#1 肩袖損傷;#2 肩袖修復;#3 #1 OR #2;#4 早期被動運動;#5 早期被動活動;#6 早期被動鍛煉;#7#4 OR#5 OR#6;#8 隨機對照試驗;#9#3 AND #7 AND #8;英文檢索策略#1 rotator cuff tear;#2 rotator cuff repair;#3 #1 OR #2;#4 early passive motion;#5 early passive exercise;#6 #4 OR #5;#7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8 #3 AND #6 AND #7。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文獻篩選:由兩位研究者分別獨立確定文獻是否符合納入標準。最終的納入文獻即為將兩位研究者所得的文獻交叉匯總后所得的文獻。資料提取包括4 個方面:①納入文獻中基本信息,如標題、作者、來源等;②研究對象、干預措施、療效結果等;③偏倚風險評價的關鍵要素;④結果測量數據及結局指標。由以上兩位研究者各自獨立進行,交叉核對,分歧意見交整個研究團隊談論解決。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兩位研究者分別獨立采用Cochrane 手冊的相關評價工具進行偏倚風險評價[4],分歧意見交整個研究團隊談論解決。包括:①隨機分配方案的產生;②對隨機方案的分配隱藏;③對研究者、研究對象采用盲法;④對觀測指標評價者采用盲法;⑤研究結束時對象失訪情況;⑥可能存在對研究結果選擇性報告的情況;⑦其他方面的偏倚。根據達標情況給出“高風險偏倚”“低風險偏倚”“不清楚”三種評價。若某研究達到上述所有標準,文獻質量等級設為“A”,表示發生偏倚的可能性小;達到部分標準,文獻質量等級設為“B”,表示發生偏倚的可能性為中度;完全達不到標準者,文獻質量等級設為“C”。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tata 12.0 及RevMan 5.3 軟件進行meta 分析。用相對危險度(relative risk,RR)表示計數資料效應指標,用均數差(mean difference,MD)表示計量資料效應指標;各效應量均采用該點估計值和95%CI表示。納入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異質性大小通過結合I2定量來判斷。P ≥0.10且I2<50%,異質性較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P <0.10 且I2≥50%,異質性較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meta 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α=0.1。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按照檢索策略,初步納入160 篇文獻,重復者被剔除之后剩余142 篇。依照文獻篩選流程逐層剔除,最終有5 個RCT[9-13],共443 名肩袖損傷患者納入本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2.2 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偏倚風險及質量評價
納入的5 篇文獻為均為英文,研究者所在地是美國、韓國、法國等不同國家。納入文獻見表1。對5 篇納入文獻依據Cochrane 手冊5.1.0 的相關方法進行偏倚風險評估,具體內容見表2 和圖2。5 篇納入文獻,每篇1 個RCT,其中2 篇文獻質量等級為“A”,3 篇文獻質量等級為“B”,未有最低檔“C”,提示納入本研究的RCT 總體質量較高。

表1 納入文獻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術后12 個月肩關節前屈角度 共納入5 個RCT[9-13],包含443 例肩袖損傷患者。初步meta 分析顯示不同文獻間異質性較小(P=0.28,I2=21%),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 統計分析。術后12 個月,早期被動運動組最大肩關節前屈角度大于晚期被動運動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MD=1.22,95%CI:0.21~2.23,P=0.02)。見圖3。
2.3.2 術后12 個月肩關節外旋角度 共納入5 個RCT[9-13],包含443 例肩袖損傷患者。初步meta 分析顯示不同文獻間異質性較大(P=0.04,I2=60%),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 統計分析。術后12 個月兩組最大肩關節外旋角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D=2.30,95%CI:-2.31~6.92,P=0.33)。見圖4。
2.3.3 術后12 個月ASES 評分 共納入3 個RCT[10-12],包含287 例肩袖損傷患者。初步meta 分析顯示不同文獻間無統計學異質性(P=0.70,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 統計分析。術后12 個月時,兩組ASE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D=-2.71,95%CI:-6.99~1.58,P=0.22)。見圖5。
2.3.4 術后12 個月SST 評分 共納入3 個RCT[10-12],包含287 例肩袖損傷患者。初步meta 分析顯示不同文獻間無統計學異質性(P=0.97,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 統計分析。術后12 個月時,兩組SST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MD=0.15,95%CI:-0.55~0.84,P=0.68)。見圖6。
2.3.5 術后末次隨訪肩袖再撕裂率 共納入5 個RCT[9-13],包含443 例肩袖損傷患者。初步meta 分析顯示不同文獻間無統計學異質性(P=0.47,I2=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 統計分析。兩組術后末次隨訪肩袖再撕裂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79,95%CI:0.54~1.15,P=0.22)。見圖7。
3 討論
肩關節僵硬是肩袖修復術后常見的并發癥[14]。以往研究表明早期進行被動運動可防止粘連形成從而減少關節僵硬的發生[15-17]。Gallagher 等[18]總結認為早期康復鍛煉相比延遲康復鍛煉可獲得更好的活動度及肩關節功能評分。本研究也顯示術后12 個月早期被動運動組肩關節活動度和功能恢復優于晚期被動運動組,其中早期被動運動組肩關節前屈角度大于晚期被動運動組,術后早期功能康復鍛煉可增強患者在早期獲得更好的臨床療效,增加患者滿意度及對后續康復治療配合度。
康復方案另一焦點是肩袖發生再撕裂的潛在影響。術后延遲被動活動有利于減少腱-骨愈合部位的微動,減少發生肩袖再撕裂的風險[19]。但也有研究表明術后早期被動活動并不會增加再次撕裂的風險。Chan 等[20]對肩關節鏡下肩袖修補術后早期活動及延遲活動兩種康復方法進行分析,發現早期活動與延遲活動的術后肩袖再斷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沈翀等[21]和Chen 等[22]的研究也證明早期被動運動組與晚期被動運動組之間肩袖再撕裂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本研究meta 分析也得出類似結論,在肩袖再撕裂率方面,早期被動運動和晚期被動運動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且兩組安全性相同。此外肩袖質量對再撕裂也有影響[23]。有研究對肩袖撕裂大小和縫合方式分析后發現,<3 cm 肩袖撕裂早期被動運動組比晚期被動運動組再撕裂風險低,但無論使用何種方式固定,只要肩袖撕裂>5 cm 早期被動運動組均比晚期被動運動組再撕裂風險高[24]。因此對于大的和巨大的肩袖撕裂,術后過早進行被動運動可增加發生肩袖再撕裂的風險,早期進行被動運動應慎重[25]。
綜上所述,對于關節鏡下肩袖修復術后患者,通常情況下早期被動運動比晚期被動運動可獲得更滿意的肩關節功能,而且并不會增加肩袖再撕裂的風險。但是制訂康復方案應綜合考慮不同個體的實際情況,對于高齡患者、伴有脂肪變性等并發癥者、巨大撕裂者等特殊情況,康復方案應該相對保守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