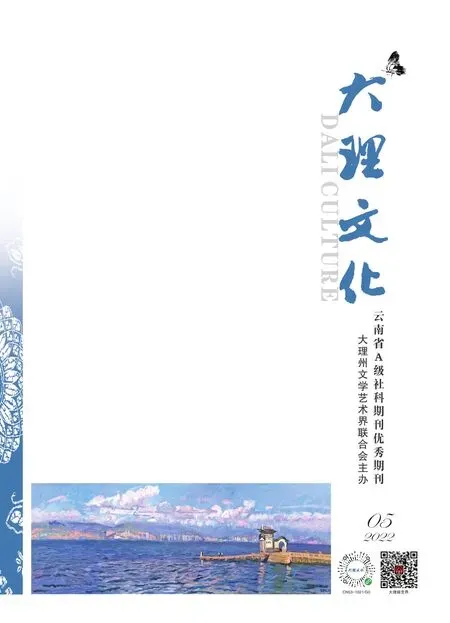『爬格子』的歲月
●高正達 文/圖
改革開放后,一度停刊的報刊相繼復刊,新的報刊也像雨后春筍紛紛創刊。各級報刊不斷擴版,用稿量不斷增大,為報刊電臺寫新聞稿的業余通訊員、特約記者應運而生,不斷壯大,成了新聞報道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當年,通訊員、特約記者統稱為“編外記者”。其中農民通訊員,被業內人士稱之為“泥腿子記者”。廣大通訊員筆耕不輟,當好黨和人民的喉舌,憑寫新聞和文藝稿,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文化底蘊深厚的大理,通訊員隊伍質與量都走在全省前列。作為曾經的一分子,至今想起當年“爬格子”(手寫方格稿紙)之路,仍然心潮澎湃、歷久彌新。
在當今新媒體、自媒體時代,只需在手機上輕輕一點,人人都可以立馬在各種社交平臺上發布新聞信息(盡管有些是雞毛蒜皮的瑣事)。而傳統媒體時代,業余通訊員從采寫到刊播一條新聞,要經歷很多程序,付出很多艱辛。其中的酸甜苦辣,圈子外鮮為人知。
編外記者也精彩
1984年,我初中畢業后回村里當選為農業社社長(現在的村民小組長)。一天,村中一名4年級的小學生拾到一塊手表,馬上把表交到我手里。我問他為何要把表交給我,他回答,老師說拾到東西要交公,在學校里拾到東西交給老師,在村里只有交給社長。在一名小學生的純潔童心感動下,我寫了一篇表揚稿,寄給大理報社,幾天后“豆腐塊”消息就見報了。從此,我與新聞采寫結下不解之緣。
同一年國慶節前夕,我到洱源縣城趕街,在電影院門口的櫥窗里看到一張征稿啟事。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縣里決定出版一本書,反映全縣各行各業35年來的發展成就。回家后,我寫了一篇《三叔騎上自行車》的通訊寄給征文組。我的稿子雖然沒有被采用,但卻被縣廣播電視站的編輯發現我有寫作愛好。當時的縣廣播電視站站長尹福全帶著編輯董煥斗,騎著自行車專程到我家里,把我發展為通訊員,向我頒發了“大理州廣播電視局通訊員證”(大理州廣電局設總編室負責對縣市廣播站統一編審和管理),正式聘為一名農民通訊員。當時的情況與現在只要投稿即視通訊員不一樣,需頒發聘書和通訊員證。
那個年代,不管是單位干部職工還是普通群眾,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能寫稿的人不多,縣廣播電視站的通訊員只有十多名。不像現在,每個單位都有宣傳專干,年輕職工都是大學生,能寫稿的人很多。全縣的新聞單位就只有廣播電視站一家,除了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云南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每周一、三、五有自辦節目《洱源新聞》《科普園地》(以摘編稿件為主),時長不定。播出是用木電桿架起高音喇叭進行有線廣播,只覆蓋縣城所在地城關區和與縣城比鄰的茈碧區的壩區。我為了聽到自己的廣播新聞編輯有什么改動,曾無數次騎自行車7公里,到縣城聽廣播。我到廣播站送稿時曾經看到過錄制自辦節目的過程,當時條件十分簡陋,沒有錄音室和調音臺,沒有導播和提詞器,播音員在自己宿舍里,拿著畫滿圈圈點點的手寫編輯稿用一臺收錄機錄制,播錯或卡殼又把錄音帶倒回去重錄。反反復復才錄成一條新聞,播音員的語氣和音量都不一樣。但由于沒有其他獲取信息的渠道,本地新聞又有種親切感,聽眾還是比較喜歡聽。
1996年7月,《洱源報》創刊,縣廣播電視站的通訊員全部聘為報社的通訊員和特約記者,創刊座談會上,全縣通訊員已發展到近百人。
短短兩年時間,大理州各縣的縣報相繼創刊,作為縣市委機關報,從半月報、旬報到周報,從四開小報到對開大報(這里指的是報紙尺寸大小)。當時,12縣市除了《大理市報》有公開出版的刊號外,其他11家縣報均為內部出版發行。1999年3月1日,全州12家縣市報作為《大理日報》縣市版,在縣內公開發行,如《大理日報·洱源版》。縣市報改為大理日報縣市版后,原出版機構一律改為大理日報××縣市采編部,由大理日報組織縣市版編審部負責對縣市版的統一編審和管理;縣市版原辦報機構的隸屬關系不變,經費來源、人員編制由縣市統籌。2003年12月31日,大理日報縣市版全部停辦,又恢復為內部報紙,不再稱為報,改為《××時訊》《××通訊》。1987年1月至1991年7月,各縣廣播電視站先后升格為廣播電視局。1990年起,各縣相繼建成30-1000瓦輸出功率的調頻廣播和中波廣播電臺,除了部分偏遠山區處于信號盲點無法接收外,大多數聽眾都可以用收音機收聽本縣的自辦節目。后來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維護成本高,經費不足等原因,相繼停辦。
1982年1月1日復刊的《大理報》為4開4版周2報,后歷經多次改版,從周3報、周4報到周6報,從4開4版的黑白小報到對開8版全彩印刷的日報。《大理報》(后改為《大理日報》)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躋身全國百家先進報社,除了一代代報紙人的共同努力,也離不開廣大通訊員的辛勤耕耘。1984年《大理報》刊發的通訊《金沙江邊的小食鋪》獲全國好新聞三等獎,是云南省州市報紙獲全國新聞獎最早的一家,這篇獲國家級獎的新聞作品就是鶴慶縣通訊員羊瑞林采寫的。
改革開放10多年間,全州報刊電臺蓬勃發展,成為廣大通訊員隊伍辛勤筆耕的園地,施展才華的平臺。
1986年1月,我第一次被《大理報》評為優秀通訊員,參加了一年一次的通聯工作會,并正式聘為《大理報》通訊員。當時,評為優秀通訊員的標準是,每年在《大理報》發表12篇以上新聞作品。雖然,看上去也就平均一個月發一篇,但那時是周3報,一個月也就出12期,又是4開小報。報紙版面有限,全州通訊員隊伍有上千人,一個月擠進一篇實屬不易。新聞稿必須題材鮮活、文筆流暢、語言精練,還要謄寫工整,才有可能被采用。
參加通聯會的通訊員有100多名,省州專職新聞編輯記者還為通訊員授課。那次聽課已時隔三十多年,至今還歷歷在目。當時大理報社的骨干編輯記者李正烈、趙守值兩位老師給我們講述了如何發現新聞、如何采訪、如何取舍提煉等新聞實戰經驗,讓我的新聞采寫能力有了很大提升,采寫的新聞稿件發生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最欣慰的是還認識了一大批文友,其中不乏和我一樣的農民通訊員。每個縣參會的農民通訊員都有兩三個,有永平的李智紅、大理市的趙勤、鶴慶的吳育民、洱源的段定中、祥云的胡子龍、劍川的康東福……
當年從事專職新聞的“正規軍”從未歧視過我們業余寫稿的“游擊隊”,提起“泥腿子記者”反而倍加尊敬。當時的報社總編輯是陳國珍,通訊員報到的當晚,他專門到下關兵站(招待所)看望段定中、吳育民等幾名年齡稍大,名氣也大的農民通訊員。第二天的會議講話中,陳總編脫稿用了很大篇幅表揚了農民通訊員。記得他說,農民通訊員生活在最底層,條件艱苦,但仍然筆耕不輟,寫出了大量讀者喜聞樂見的新聞作品,每年都有新聞作品在全省,甚至全國獲獎,為大理州贏得了榮譽。專職新聞工作者要向農民通訊員學習。那次會議,參會的通訊員每人發100元車旅費和誤工補助,一本稿子和一本采訪本,陳總編還決定,農民通訊員沒有工資,發雙份。
會議結束聚餐時,洱源老鄉坐的那桌已經坐滿,我便隨意挑了個空位坐下,同桌的人大多不熟悉,只有兩三個在會上發言的人,我認識他們,他們不一定認識我。我顯得有些拘謹。坐在我旁邊的大理報社張鴻光老師一一向大家敬酒,敬到我時,他問我是來自哪個單位。我卑微地回答,我沒有工作,來自農村,并報了自己的姓名。張老師馬上站起來,雙手舉杯說:“我們大家要么從事專職新聞工作,要么搞單位宣傳工作,寫新聞稿其實就是本職工作,而你身處農村,業余寫了那么多的稿子,其中不乏好稿子,你才是我們尊敬和崇拜的人,衷心地敬你一杯。”同時,他還號召同桌的人一起敬我,讓我鬧了個大紅臉。
后來,我又參加過幾次大理報社的年度通聯工作會,認識的同行也越來越多。我所認識的州內10多名農民通訊員,多年后,要么靠寫稿改變了命運,要么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文化人。
永平的李智紅,是主要寫報紙副刊文學作品的農民通訊員,寫新聞,也寫文學作品。高中畢業后,他與高考失之交臂,回到家鄉的小山村種過地、趕過馬、燒過窯、當過木匠、當過民辦教師,不管干什么都業余筆耕不輟,是個寫稿高產者。通訊員中傳頌著,有時李智紅下山投稿,稿件要背滿滿一籮筐。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最終,李智紅靠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和一摞獲獎證書,破格成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他先是調到永平報社工作,后來提拔為縣文聯主席,最后調到州文聯工作。李智紅不僅成為國家干部,還成為知名作家,被國內名刊《讀者》聘為簽約作家,出版個人專著和主編著作10余部。
大理市的趙勤也因寫作上的突出貢獻,被錄取為國家干部,先后在大理市喜洲鎮、大理市文聯、中共大理州委宣傳部、大理市省級旅游度假區管委會工作。現為大理州文聯保留副處級干部。
祥云的胡子龍,洱源的宋炳龍,后來一直做自由撰稿人,專攻小說創作,成了州內響當當的農民作家。胡子龍的小說被《解放軍文藝》《西南軍事文學》等軍事名刊采用過。宋炳龍出版長篇小說兩部,當選為洱源縣作家協會主席,被聘為《洱源文化》特聘副主編。
鶴慶的吳育民、張長寶,洱源的段定中,他們都是農民通訊員中的佼佼者,憑著對寫作的愛好和執著追求,一直堅持筆耕不輟到耄耋之年。段定中在新世紀之初,八十多歲高齡還堅持寫新聞,一直寫到臨終時。他去世后還有新聞發表和獲獎,我曾在報刊的獲獎名單上看到段定中打著黑框的名字。
我本人也因新聞報道的突出貢獻,被共青團云南省委、中共大理州委授予省、州“新長征突擊手”稱號,被州縣黨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2003年底,銳意改革的大理電視臺不拘一格招聘人才,我憑著當年的云南省記協好新聞一等獎、全國少數民族地州盟報好新聞三等獎,以及一摞國家級、省級報刊的新聞作品復印件,被破格錄取。說是破格,是因為當時各單位招聘都有本科以上學歷、年齡35歲以下兩道門檻。而我的學歷只是函授專科,年齡已經39歲。當我的試用期滿,臺辦公會討論我正式聘用的問題時,一位臺領導提出,全州還有兩三千名大學生待業,怎么要招聘一個農民。當時的新聞中心主任張建明發表意見說,招聘一名大學生可能要培訓適應一兩年才能上手,而他頭天報到,第二天就能以文字記者獨當一面了。就這樣,當了20多年“泥腿子記者”的我,終于放下褲管,爬出田埂,用扛鋤頭的肩膀扛起了攝像機,成了大理電視臺新聞中心一名專職記者,不惑之年終于找到自己人生的最佳位置,改寫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
很多單位的業余通訊員,因在新聞采寫中,熟悉部門和基層工作經驗,文化知識得到提升,大多走上了領導干部工作崗位。
處處留心皆新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聞界將內容鮮活,第一時間搶到時效性強的新聞稱之為“活魚”。如果新聞事件水過三秋田,你才去采訪,再好的新聞都成了“死魚”“臭魚”,莫說受眾沒胃口,到編輯手里就被斃了。
業余通訊員生活圈子小,新聞線索自然有限。而在當地重大活動或重大題材方面,根本無法與專職記者爭搶。通訊員大多只有專門到專職記者不常到的偏僻地方,捕捉專職記者的“漏網之魚”。而通訊員中,單位干部職工又要比農民通訊員有明顯優勢,他們起碼在工作中容易弄到本系統或相鄰單位的總結報表等權威準確的材料。而農民通訊員就只有死守自己的小圈子里的新聞素材。有的農民通訊員為了獲得更多的新聞線索,發展了自己的“線人”,為自己提供新聞線索。而大多數農民通訊員靠的是在生產勞動和生活中,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時通訊員與別人一起同行,別人可能沒發現什么不尋常,而通訊員可能在一句聊天、一張海報、一個異常舉動中,挖到新聞線索,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源源不斷地寫出群眾喜聞樂見的“豆腐塊”小新聞。

編輯部給通訊員的回信、賀卡、稿費單
鶴慶的張長寶曾經在通訊員通聯工作會上向我交流過獲取新聞線索的經驗。他充分利用鄉村醫生的優勢,在就診過程中,與來自十里八村的患者親切地拉家常;在進藥品或衛生系統的培訓、會議中與人聊天。例如,問就診的村民莊稼收成如何?為何收成好?哦,原來收成好是實施了良種和科學種田。那么,接著又問農科部門如何推廣,農民的觀念是如何轉變的,目前村里的積極性如何,科學種田的規模達到多少等。了解到有價值的新聞線索,下班后,便騎上自行車去找當事人實地采訪。張長寶就這樣足不出鄉,每個月都能采寫出三五篇內容鮮活的新聞,被多家新聞單位采用。1984年至1987年間,張長寶連續獲得云南人民廣播電臺的好新聞一等獎或二等獎。
而我主要靠“觀察法”,在日常生活中獲取新聞線索。去趕街賣農產品、購買生產生活物資的過程中,我曾觀察到不少好新聞。有一次我去農貿市場賣糧食,看到一位賣糧的白族大媽,過完磅后,從懷里掏出電子計算器從容地算賬,感覺眼前一亮,馬上過去與白族大媽攀談。她談笑風生地說,自己文化低,不大會算賬,曾經被人忽悠,吃過好幾次虧。后來娃娃給自己買了計算器,一夜就學會了,手指輕輕一點,又快又準,再也不會吃虧了。回家后,我當晚寫出了《計算器成為洱源農民的新寵》。去籽種公司購買良種時,一位村民向銷售人員索要發票,銷售人員說,發票用完了,下個街天補給他,那位村民說他不買了,下個街天有發票再買。我立即追上去問他,為何把發票看得如此重要。他回答,上一年,他們村里一批良種出現質量問題,導致減產減收,投訴后,有發票的村民獲得了賠償,而沒有發票的村民因沒有依據而無法賠償。我據此寫成了《洱源農民學會當“上帝”》。在街上,我看到購買軍便裝的人多,寫成了《軍便裝成為農民的“工作服”》;看到有農村人開始購買電飯煲,寫成了《“田螺姑娘”進農家》。
而有些好新聞是我在生產生活中觀察到的。1987年,洱源縣開始在幾個鄉鎮發展烤煙種植,我們村全村都種烤煙。村里那些上了年紀的種田老把式,因文化水平低,難以適應科技要求高、從未接觸過的烤煙種植,都從家長的位置上退下來,聽年輕子女的安排。據此,我寫成了《奔小康,兒子領著老子走》。只要留心觀察,新聞無處不在。《鐵牛下田、水牛出埂,三營鎮上千頭水牛“退役”》《洱源農民看天下,旅游成為新時尚》《小村有個農民歌舞廳》《訂份報刊成時尚》《保姆走進農民家》……這些觀察到的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新聞,大多被《農民日報》《經濟日報》《云南日報》等報紙采用。
利用觀察法,我足不出村還采寫過兩條“國際新聞”,成了我通訊員“爬格子”職業生涯中難忘的兩次采訪。
1989年秋天,我正在村西的彌茨河邊挖秧田,突然看到河對岸縣畜牧局的牧草基地里,開來10多輛小車,下來一群人圍在田里轉。新聞敏感告訴我一定有大新聞。我立即丟下鋤頭,爬出田埂,顧不上洗腳穿鞋,趟過小河,到人群中打聽他們在做什么事。有人告訴我,澳大利亞牧草專家來進行牧草結籽能力試驗驗收。我當場提出請求采訪,當時我的采訪本和通訊員證是隨身帶的。翻譯查驗了我的通訊員證后,向澳大利亞牧草專家奧恩轉達了我的訴求。奧恩看我高挽著褲管,腳桿上沾著泥巴,驚訝地問翻譯怎么像個農民。我指指腳上的泥巴說:“我是泥腿子記者。”金發碧眼的奧恩哈哈大笑,豎起毛毛茸茸的大拇指,用生硬的漢語說:“中國、農民、了不起!”說完愉快地接受我的采訪。我據此寫成《澳大利亞牧草結籽能力試驗在洱源獲得成功》的稿子,由于涉及外事,我還專門跑到縣畜牧局審稿蓋章。
1999年9月的一天,我在村東214國道邊的農田里做活計,看到路邊的村衛生室門口圍了很多人,以為出了什么醫療事故,趕快跑過去看。原來是我村村醫趙貴全參加云南省衛生廳和加拿大聯合舉辦的鄉村醫生培訓班,結業后,加拿大醫學專家馬通理一行專程從昆明隨趙貴全到我村訪問考察村級衛生室建設運行情況。村醫趙貴全請我幫他拍幾張照片,我立即跑回家,取相機,最終刊發了攝影報道。后來,《大理日報》晚刊記者專訪趙貴全做深度報道,因無法補拍加拿大醫學專家馬通理到訪的照片,還用了我拍的兩張照片做配圖。這兩條“國際新聞”可謂是可遇不可求,如果不是多年積累練就的新聞敏感,就有可能與之失之交臂。
在交通、通訊、信息都不發達的年代,通訊員為了獲取新聞線索,可謂是絞盡腦汁、各有千秋。由于篇幅關系,難以一一贅述。不過,大家不管用什么途徑獲取新聞線索,都恪守新聞職業道德,遵守新聞真實性的原則。也有極個別的通訊員,為了多上稿,投了有虛假成分的新聞稿,最終被人舉報,經新聞單位通報后,沒有媒體再敢采用他的稿子,斷送了自己愛好的業余新聞事業。
通訊員的苦與樂
說起業余通訊員,很多人只知道其光鮮的一面,背后所吃的苦鮮為人知。有的通訊員寫了幾篇后,吃不了苦最終選擇放棄。能夠多年堅持下來的人實屬不易。
當業余通訊員,因為有本職工作,只有放棄喝酒、打牌、聊天、看電視和休息時間,才能見縫插針擠出時間采寫稿子,夜深人靜還在“爬格子”。而稿費和付出往往不成正比(特別優秀、稿件采用率高的通訊員除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縣級媒體的稿費2元一篇、州級3至5元,省級5至8元。記得當時我最高一個月的稿費200多元,平時也就二三十元,能買兩三條煙。要當好通訊員,必須自費訂幾份報刊,以便學習新聞業務知識,借鑒同行的經驗,研究欄目的用稿特色和需求,獲取征稿信息等。同時,還要購買紙張筆墨、工具書、郵票。每年的稿費收入能夠保本就不錯了。不過,大多數通訊員不怕苦累、無怨無悔、持之以恒寫稿,并不完全是為了稿費,更主要的是為了愛好、追求、情懷,甚至是一種責任和擔當。當然也有稿費收入高的,如李智紅,每月稿費比工資還高,但是,在通訊員中稿費高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不少通訊員連寫稿的成本也收不回來,處于虧本狀態。
上個世紀90年代,各級新聞媒體相繼出臺了“郵資總付”的優惠措施,投稿時只需將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并在右上角寫上“稿件”或“郵資總付”就不用貼郵票,編輯部按月與郵電局結賬。有的編輯部還定期不定期給比較活躍的通訊員寄贈稿紙。
當年,通訊員采訪新聞比起現在花費的時間要多得多。在采訪中要反復核實,特別是一些專業術語用哪幾個字都要核實清楚。同時要認真記錄,采訪結束還要把采訪記錄讀給采訪對象聽,不然回到家寫稿時發現有疑惑或需要補充的情況,又得跑一趟。不像現在,可以用錄音筆、手機錄音記錄,采訪結束留個采訪對象的電話,隨時可以核實情況、數據。
通訊員采寫的新聞稿件要想提高采用率,除了題材新穎、標題別致醒目以外,還必須書寫工整。曾經有編輯老師介紹,有的好稿子,因書寫潦草,編輯看不清而只能忍痛割愛。所以,大多數通訊員都是先打草稿,修改好后再用正楷一筆一畫地謄寫。有時寫錯一兩個字就用涂改液或改正紙,盡量讓稿紙卷面清秀,讓編輯看起來舒心。改正紙背面有粘膠,大小剛好與方格稿紙一樣大,撕下來貼在寫錯字的格子上,再把正確的字寫在改正紙上。有時發覺寫漏幾個字,或寫錯幾句話,就得重新謄寫一頁,決不能有大的涂改讓編輯老師看起來不舒服。當時投新聞稿不像文學稿一稿一投,可以一稿多投,中央、省、州、縣各級媒體之間不沖突,報紙與電臺也不沖突。有時覺得寫得好的一篇稿子要投好幾家報刊電臺,甚至是十幾家。通訊員大多采用復寫紙,謄寫一遍復寫出三四份。后來,又有編輯老師介紹,有的編輯收到復寫稿最上面清晰的那兩份,會優先考慮,如果收到的是末尾稍微有些模糊的那兩份,就不大愿意看,就像高考時填報志愿第一志愿與最后一個志愿的關系。所以,自認為寫得好的稿子就不用復寫紙復寫,而是要投幾家媒體就用鋼筆謄寫幾份。記得當年我寫得好的一篇稿子投了12家媒體,也就是說謄寫了12份。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先后有8家新聞單位采用。
為了不讓稿子折痕過多,編輯看起不舒服,通訊員購買投稿用的信封都是買牛皮紙大號信封,稿子只需對折就能裝進信封。我每次買信封都買100個,同時買100支碳素筆和圓珠筆,能用3個多月,平均每天投一份稿件。作為農民,常年四季捏鋤頭和鐮刀,手心上磨起老繭很正常。而我與眾不同的是因長期謄寫稿子,右手握筆的拇指、食指、中指上也有一塊老繭。
通訊員之間最引以為榮的是刊發版面頭條、加編者按或編后語的新聞、“花邊新聞”。“花邊新聞”是編輯為了讓題材鮮活、短小精干的新聞吸引讀者瀏覽版面時的眼球,把新聞用花邊框起,并非現在所指的娛樂新聞、八卦新聞。誰要是上了上述一條新聞,收到樣報時,都會反復賞讀,每讀一遍都是一種享受,精神為之振奮。
新聞要是配上照片,更客觀真實,看起來更直觀,所以很搶手。但那個年代,照相機屬于稀有高檔奢侈品,會玩相機的人更是鳳毛麟角,專職記者也只有少數人配備有相機。1997年,我為了提高上稿率,攢了幾個月的稿費500多元,妻子為了支持我,賣了幾只雞、1筐雞蛋、2袋大米,給我籌了400元,我專程到下關正陽商場買了一臺鳳凰牌單反相機,一個閃光燈,如獲至寶。幾個月后才發現,相機是燒錢的。一個膠卷20多元,能照24張,洗印費每張0.7元,一個膠卷照完成本就要40多元。而新聞的時效性很強,拍了一張自認為有價值的照片,就必須取出膠卷去沖印,根本等不到一個膠卷都拍完。有時遇到親朋好友,人家要請你幫拍幾張,又不好意思收錢。幾個月下來,拍兩三個膠卷才有一幅新聞照片被采用,得到的稿費連洗印費也收不回來,更莫說膠卷成本。后來除了十分好的題材以外,我不再輕易拍攝新聞照片,到相機閑置不用也就發過10多張新聞照片。報社編輯也知道拍照片成本高,不采用的照片基本都退稿,以便作者另投他報。退稿時還說明退稿原因,并向作者普及拍照角度、構圖、背景、用光、快門速度、聚焦等一些基本知識,為我后來進入電視臺,在較短時間內熟練攝像機操作起了關鍵的作用。照相和攝像有很多相通之處,只不過照相的畫面是靜止的,攝像的畫面是運動的。我第一天用攝像機就懂得黃金分割線構圖,令教我的攝像老師刮目相看。
當業余通訊員雖然要吃苦,但也有很多樂趣和收獲,當地干部職工和人民群眾都十分尊敬、愛戴通訊員。通訊員在基層有著一定的社會地位。每年春節前夕,當地黨委政府和宣傳部門,都要走訪慰問新聞報道成績突出的通訊員;各家媒體都給廣大通訊員寄贈精美的新春賀卡、掛歷、慰問信。
洱源江尾鄉黨委不管換了多少屆,一直延續著邀請本鄉優秀通訊員段定中列席鄉黨委會的慣例,為的是給他提供新聞線索,同時,也聽取他反饋新聞采訪中發現的一些基層問題。
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是傳統媒體的黃金時代,有不少人民群眾自費訂閱報刊,我們村有位村民曾經自費訂閱報紙10余年。每逢街天,縣城報刊零售亭的生意十分興隆。1990年至2000年,洱源縣為了推廣科學養奶牛和農業科技知識,要求每戶養奶牛戶訂閱《云南科技報》,由鮮奶收購站發行,全縣共有4萬多農戶訂閱《云南科技報》。那時,農村電視機還沒有普及,村民的業余文化生活、獲取信息知識、了解黨的方針政策的途徑主要靠閱讀報刊。常有村民專門到村公所(現在的村委會)或小學借閱報刊,每逢街天,縣圖書館公共閱覽室總是擠滿背著籮筐的村民。我曾捐出幾百冊藏書和雜志,在村里辦了個文化室,把我訂閱的20多份報紙也放在文化室,免費向村民開放。一個300多人的小村,每晚到文化室閱讀的村民都有四五十人。所以,通訊員在當地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周邊村子里的村民遇到我時,常有人說在報紙上讀到我的文章,豎起大拇指為我點贊。也有不少人專門找到我為我提供新聞線索。我的一條轟動全縣的新聞,就是幾名鄰村村民到我家,向我算了飼養奶牛的幾筆賬,請我幫他們寫一篇聯名呼吁奶價太低的“讀者來信”。那時各家媒體都有“讀者來信”(記者來信、通訊員來信)欄目,專門為基層呼吁、監督、解決問題。我通過思考分析,又做了大量的采訪調查,寫成數據詳實,邏輯嚴密的新聞調查,雖然沒獲什么新聞獎項,但卻是我從事通訊員工作時最自豪的一篇新聞,它惠及千家萬戶。
那是1996年的事。當時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產品也在不斷漲價,而鄧川奶粉廠的鮮奶收購價格上漲速度,遠遠落后于豆糠、糧食漲價的速度。一些耕地面積少,靠購買豆糠、糧食飼喂奶牛的農戶,扣除成本,利潤空間不大,農村飼養奶牛的積極性曾經一度低落。我通過深入采訪調查寫成的新聞調查,反映一斤鮮奶不如一斤醬油,洱源飼料漲價飼養奶牛虧本。新聞在《云南科技報》《云南經濟報》等報刊上刊登后,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洱源縣物價局專門派人找到我核實新聞報道的情況,并到奶牛飼養戶家中調查。當時國有企業還實行計劃經濟,最終洱源縣物價局調高了鮮奶收購價格,并出臺鮮奶保護價政策。我利用輿論監督為廣大奶牛飼養戶爭得利益,飼養奶牛的地區都在傳頌著我的名字。有一次我去離家較遠的一個村做客,掛禮時剛報上姓名,埋頭記賬的人放下毛筆,站起來用崇敬的語氣說:“你就是為我們提高奶價的高記者!”隨后,馬上請來總管客事的“老總理”,邀我樓上請,當貴客招待。

通訊員證、特約記者證
當通訊員,還能使我在孤立無援時獲得幫助。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帶著兩名村民到雞足山尋找離家出走的村民。當時還沒有從洱源到雞足山的公路,我們繞道下關再到賓川牛井鎮,繞了一圈,到達雞足山金頂寺,身上的現金所剩無幾,已經沒錢住山頂簡陋的油毛氈房大通鋪旅社,想在野外露宿。開旅社的人告訴我們,山頂積雪未化,晚上很冷,會凍壞的。并告訴我們雞足山西坡有條小路,兩個小時可以步行到洱源雙廊(當時雙廊還沒有從洱源劃歸大理市)的五星、石塊,可以到村里借宿。結果天黑后迷路了,我們向著黑暗中的幾點燈光走,快到山腳有戶人家,一問才知是到了鶴慶的黃平。我們與那戶人家商量借宿,可他家里實在不方便留我們,他教我們原路返回再向洱源方向走,不遠就是洱源縣林業局的余金庵林管所,所內有招待室,住宿費很便宜。當我們到達林管所時已經是深夜12點,叫開門投宿時,才發現我們開的證明在下關住旅社登記時弄丟了。當時還沒有實行居民身份證,沒有身份證明,林管所的工作人員擔心我們是壞人,不予接待,連在他們屋檐下待一晚也不允許。正當我們無奈地準備繼續在夜幕中前行時,我在衣袋里掏煙,觸到隨身攜帶的通訊員證,欣喜若狂地把通訊員證遞給工作人員,他看了一眼即刻眼里放光,激動地說:“哇,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正達啊!我經常在報紙上讀到你的文章,今天終于有幸見到真人。”工作人員隨后熱情地把我們迎進林管所的招待室,還叫醒炊事員給我們做飯,第二天還給我們烙了麥面煎餅帶在路上當作午飯,沒有收我們一分錢。到達雙廊后,我們搭載拉煤的拖拉機,順利回到洱源三營老家。
通訊員的奇趣事
我所認識的通訊員,都一心撲在采寫新聞稿上,在圈子里留下了不少趣聞軼事。
1985年的一天,洱源江尾的段定中,家里請工做農活,家人安排他在家做午飯。他正在洗菜,突然聽到村里響起一陣鞭炮聲。農忙時節不會有人辦喜事,新聞職業敏感促使他前去探個究竟。
循聲而至,是奶牛販子給同村村民段錦生送錦旗和感謝信。原來3天前,牛販子購買了段錦生家的一頭奶牛,付款后請段錦生代養3天再來牽牛。第二天已經賣了的奶牛產下一頭小母牛,按當時的價格值好幾百元。鄰居都說,段錦生和牛販子講好價賣的是一頭牛,不是兩頭,小牛應該歸段錦生。而淳樸的段錦生則認為,付款后奶牛就已經是牛販子的了,自己只不過是代養,所產小牛犢當然也應該是牛販子的,所以,把一大一小兩頭牛都牽給牛販子。牛販子把牛牽回去后感動得給段錦生送來錦旗和感謝信。
段定中馬上投入采訪,回到家立即寫新聞稿。等段定中謄寫完新聞稿,剛好家里雇的工回家吃飯,這才想起太投入了,竟忘了做飯的事,還沒生火。雖然讓雇工受餓,但段定中采寫的新聞《白族農民段錦生賣牛講風格》獲得了當年的云南省廣播電視政府獎一等獎。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洱源的張文元抱著兩個枕頭,他說,晚上寫稿最怕的就是停電。有時深夜正滿懷激情地奮筆疾書,突然停電,找不到蠟燭,又不愿去敲經銷店的門,便從枕芯里撕一團棉花,搓成燈芯,再到灶房里倒半碗香油,做成香油燈,繼續挑燈夜戰。久而久之,枕頭竟被他掏空了一半。如今回想起來,通訊員有時像孤燈黃卷的苦行僧。
而鶴慶的吳育民身處金沙江邊的山區,條件艱苦,早年不通電,他常常是打著松明火把寫稿。開通訊員會議時,同行們打趣說他臉色微黑是松明煙子熏黑的。有時稿紙用完,顧不上去買,吳育民就用香煙殼寫稿。他的寫稿經歷一直在圈子里傳為佳話。
我寫稿的趣事與同行相比,卻顯得有些尷尬。不過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我筆耕人生中的一朵浪花,對我的家庭和諧、為人處世還是有一定的益處,歷久難忘。
2000年大春農忙結束的一天,一起玩泥巴長大的伙伴們在村中的大青樹下休閑,水煙筒、搪瓷茶缸傳來傳去,天南地北地神侃一些笑話,不時爆發出高原漢子粗獷的笑聲。
一輛小轎車開進村里,戛然停在大青樹下。車上跳下一個人,沖著我喊道:“老高,祝賀你。你的大作在省里獲了獎,為我們縣爭得了榮譽,有空到縣城趕街時,到我辦公室來一趟吧。”他還要下鄉,鉆進小轎車,轟的一聲,丟下一股久久彌漫的灰塵走了。
大青樹下一下子炸開了鍋。有的猜測獎金是幾千,有的說可能上萬。我解釋說,以往小文獲獎也就兩三百的獎金。同伴們哪里肯信,罵我是鐵公雞,不由分說,拖起我就要我請客。我身上沒帶錢,馬上有人借給我300元。
大伙推杯換盞,吆五喝六,直喝得天昏地暗。有幾個醉得被背回家,我忙不迭地灌醒酒湯,還挨婆娘們的罵,說我灌醉了她們的漢子,只有讓我去頂替他們的漢子干活。挨了別人婆娘的罵回家挨自己婆娘的罵,一進門老婆就數落道:“你好大方喲,我看中一套衣服好長時間了一直舍不得買,你倒好,一出手就是幾百元,用來灌貓尿。”當時,300元對于有錢人來說只是一甩手的一次小費,而對于土里刨食的農民來說,得起早貪黑地干一個月。說實話,我也有點心疼,但是面對一起長大的小伙伴們,我能說不嗎?
沒過幾天,我趕緊到縣城領獎,發獎單位卻給我開了一個大玩笑。你猜咋的?只領到一張復印的榮譽證書,那位領導朋友對我說,這次省里頒獎,以精神鼓勵為主,沒有獎金。本來應該由縣里給你發點獎金,但是單位也沒錢,以后再說吧。榮譽證書由單位保存,作為年終考評的依據,給我復印了一張榮譽證書,作為我獲獎的證明。
只領回一張“白條”,怎么向老婆交待?她卻沒有再罵我,只是微笑著說:“以后別亂炫耀稿費,等你那幾文稿費吃飯,還不把我們全家的嘴餓尖了。”說完一狠心,拿出了她賣了一批土雞的錢,讓我還了那頓飯的錢。
為了感激老婆的寬宏大量,我假裝討好地說,今后再也不寫稿了,認認真真跟她到地里干活。老婆急忙說:“不,還是要寫,錢多錢少我不在乎。你經常寫稿,不打麻將,這是我們全家人的福份。再說了,寫稿使你的學識進步不小呢。”
事后,一位家庭寬裕的伙伴知道我領獎的實情后,說最近打牌手氣好,硬塞給我300元,我說啥也不接。因為我的想法跟老婆嘮叨的一樣,再節約在家里節約,在外面該出手時就出手,面子還是要撐起的。
亦師亦友筆耕情
當通訊員那些年,我除了收獲事業以外,最大的收獲就是擁有各行各業的一幫朋友。通訊員之間要么成為文友、摯友,要么成為忘年交。文人相輕的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都是文人相親。在采訪中大多與采訪對象成為朋友。通訊員生活上不算很富裕,但精神都是富有的,除了幾大本作品剪貼本和一摞獲獎證書,還有一大幫朋友成為人生中的一筆精神財富。大家業務上互相交流,生活中互相關心,遇到困難時互相幫助。有些編輯也和通訊員成為朋友。
上個世紀末,報刊電臺編輯部都十分關心通訊員隊伍,除了業務上的培訓指導,在選稿用稿和評獎時都對通訊員公平公正對待,而且盡量給予傾斜。記者和通訊員有相同題材的稿子,優先采用通訊員的。征文獎和年度獎,要么編輯部所有人員和親屬不參加評獎,要么設專業組和業余組,盡量讓通訊員有更多獲獎的機會,并把通訊員的獲獎作品推薦給上一級新聞獎。每年國家級新聞大獎中,通訊員都占一定比例,有幾年曾經有僅在縣級廣播電視站播出后,由縣級選送逐級往上推送的通訊員的作品。
在傳統媒體輝煌的年代,各媒體都辦有聯系通訊員的內部刊物,如《通訊員之友》《通訊員之家》《通訊員園地》《××報通訊》,成了編輯與通訊員之間的橋梁紐帶。內刊除了刊發輔導通訊員的業務文章,通訊員之間也可以互相交流探討。通訊員有什么需要解決的業務問題,可以寫信給通訊員內刊的編輯。共性的問題,編輯會在通訊員內刊上回復;個性的問題,編輯會私信通訊員回復。
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報》副刊編輯張乃光,他是位非常受通訊員尊敬的編輯老師。《大理報》還沒有改版為日報之前,每周在4版有“洱海”“三塔”“萬花溪”3期副刊,“洱海”是刊登小小說、散文、詩歌的純文學副刊,“三塔”主要刊登隨筆、言論,“萬花溪”主要刊登介紹大理旅游“吃住行游”的游記。張乃光老師從事副刊編輯多年,遇到立意好題材新但基礎差的文章,他都會精心修改、潤色,或寫信給作者,提出修改意見。我雖然沒有收到過張乃光老師的信,但我的《無言的求婚》等幾篇民族風情散文,都是經過張乃光老師精心修改后,得以在《大理報》發表的。收到樣報后,我仔細對照原稿,張乃光老師把我用慣的新聞語言都改成了文學語言。現在大理的好幾個知名作家,都得到過張乃光老師的幫助,都是從《大理報》副刊園地步入文壇,走向全省、走向全國。
我曾經無數次聽過,通訊員到州府或省城辦事,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遇到困難就去找編輯部,把編輯部當做是通訊員的娘家。編輯大多會盡力所能及的能力幫助通訊員排憂解難,把事情搞定。有的編輯還盡地主之誼,請通訊員吃飯。
我現在珍藏的幾百封信件中,有一大半是印有報刊編輯部落款的回信。1986年,我急需一本《現代漢語詞典》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材,縣新華書店買不到,托人到下關也沒有買到。情急之下,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我把書款直接匯給《邊疆青年》編輯部,我剛在《邊疆青年》上發了兩篇文章,同時給編輯部寫了一封短信,說明原委,列出幫忙代購的書目。一周后,我收到掛號寄來的書,同時收到編輯部退回來買書剩下的余款和一封短信。信中說他們跑了好幾家大書店,有兩本書還是沒有貨源,建議我直接跟出版社聯系,落款是《邊疆青年》編輯部。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哪位編輯老師幫我買的書。
我至今保持聯系的通訊員朋友還有幾十個,我特別想說的是州文聯的李智紅老師,我與他在通聯工作會上有過一面之交后,時隔20年邂逅依然一見如故。
最初認識李智紅是1987年《大理報》通聯工作會上。會議間隙,我的老鄉洱源作家洪海約我去找永平的李智紅聊天交流。聽到名字我以為是位美女,怦然心動走進房間才知道,“永平美女”原來是一位抱著個大煙筒的彝族小伙子。房間里十幾個寫作愛好者眾星捧月一般圍坐在李智紅周圍。拿現在的話說,李智紅很牛、接地氣。他吸的大煙筒比較粗,一張臉的三分之二都埋進大煙筒的口口里,咕嘟、咕嘟地吸十幾秒,一支煙就燃去了三分之一,然后仰起臉,噴氣式飛機一樣噴出三股濃煙。待煙霧散盡后,在風趣幽默、談笑風生中給大家講創作經驗和投稿技巧。有幾名新手還拿出采訪本記錄。李智紅時不時還講個段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當時,我還是一個剛上道的業余農民通訊員,聽了李智紅大家風范的創作談,得知他的文學作品被國家級報刊發表,一些還在海外發表,這在當時的人群中是首屈一指的,以為他一定是名牌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聽了老鄉的介紹,才知道,李智紅其實根本未圓大學夢,也是農民出身,干過很多行業,不管干什么都業余筆耕不輟,最終靠數十萬字的文學作品和一摞獲獎證書,破格錄取為國家干部,也就是現在的公務員。應該說,李智紅當時的一席話和他的經歷更加堅定了我堅持寫作的信心。雖然我至今沒有像他一樣功成名就,但至少現在還堅持閱讀和寫作,成為充實精神生活的唯一愛好。
和李智紅通聯會一別,各自忙于謀生,竟一別20多年。在這20年中,很想再次聆聽李智紅談創作。但是一些會議他參會我沒參加,我參會他又沒參加,一直沒有機緣。不過,我又隨時都會遇到李智紅,在報刊上遇到。每當看到李智紅的文章,我都會反復咀嚼他那回味無窮的心語,感受閃爍著靈魂感悟的霞光,成了我勞作一天后最高檔的精神享受。直到本世紀初,我被大理電視臺破格錄取,從一名農民通訊員成為一名專職記者,才得以與李智紅再次相逢。
2008年,單位派我到永平采訪,陪同采訪的永平廣電局副局長張繼強得知我和李智紅是有過一面之交的朋友,便給他打電話,約他一起吃飯。他因有事婉拒了,說過兩天他請我吃。采訪完縣領導,得知李智紅已經任永平縣文聯主席,就在縣政府大院上班。與他近在咫尺,離吃飯還有會時間,我就提出到李智紅的辦公室去看看他。20多年未見,當年那個談笑風生的彝家大哥,臉上已經布滿了歲月的滄桑,依然不變的是堅毅的表情和身邊的一個水煙筒,眼神比年輕時更加深邃,就像能看穿一切事物。我們倆都很興奮,寒暄之后李智紅當即改變了之前的預約,要和我小酌兩杯。一開始,我還擔心彝家漢子粗獷豪放,以酒待客、把酒當文化,而我又不勝酒力,會不會喝趴下。沒想到喝了兩杯后,李智紅說他不能再喝了,這幾天患腸胃炎,說完從兜里掏出藥瓶吃藥。李智紅真是酒品如人品,人品如文品啊!患腸胃炎還要陪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文友喝兩杯,讓我激動得獨自干了一杯。
與李智紅相談甚歡,臨別,他送我幾本他的作品集。我最喜歡其中的《靜夜煨茶》,勞累一周后,周末,在陽臺的花草間擺把椅子,慢慢品讀《靜夜煨茶》,真的如品香茗一樣,讓人神清氣爽,回味無窮。故鄉的一片樹葉、一朵白云、一縷炊煙、一口老井、一頭老牛到了李智紅筆下皆能成為一篇美文,看似信手拈來,實則是他熱愛生活、熱愛家鄉、善于觀察、勤于思考、筆耕不輟的結晶。《靜夜煨茶》有的篇章“激情四射,如荒火般熱烈”,有的篇章“溫柔細膩,像月下潺潺流淌的林中小溪,空靈、悠遠,回音清脆”。更重要的是每讀一篇,讓人要么悟出禪意,豁然開朗,要么思出哲理,懂得放下。
后來,李智紅調到州文聯,我們都在同一座城市工作,有更多的機會相聚。我始終喜歡與李智紅一起品茶談創作,喝酒論人生。
大理州知名白族作家楊義龍,也是我在1996年7月,《洱源報》通訊員工作會上認識成為朋友的。那時,他在一所山區小學任教,后來調入《洱源報》任副刊編輯,我的第一篇小小說《閑事》就是他幫我修改編發的。再后來,楊義龍調入州文聯。他雖然比我小幾歲,但在新聞寫作和文學創作上都幫助過我,在我心目中一直把他當老師。
文章就要結束了,我想借用一篇舊作《從農民到記者》(入選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聞背后的故事》)的結尾來做結尾。“不管是當業余通訊員還是專職記者,新聞工作都是很苦很累的,但是,苦中有樂,樂中有趣,趣中有意。”
編輯手記:
《“爬格子”的歲月》作者高正達在成為大理電視臺的專職記者之前,一直以農民通訊員的身份為報刊電臺撰寫新聞和文藝稿20多年,是當時新聞報道不可或缺的“泥腿子記者”中的一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通訊員這個特殊的群體,筆耕不輟,當好黨和人民的喉舌,為大理州基層宣傳工作、報刊電臺的發展、農村文化生活的繁榮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時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品嘗酸甜苦辣,活出了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