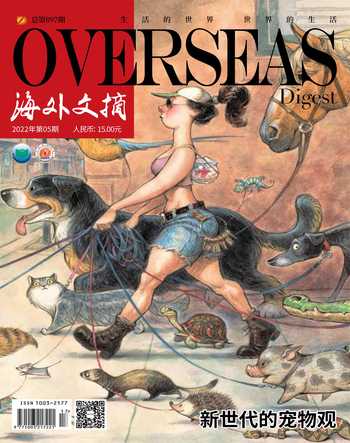仿生機器動物
鮑勃·福爾摩斯

機器隼
蜜蜂通過跳舞引導蜂巢中的同伴找到新的食物源;孔雀魚會與同伴們協商領導權;當隼來襲時,信鴿會進行集體躲避。自從動物行為研究出現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諸如此類的社交互動。如今,他們的研究有了新的變化——研究對象不僅有活體動物,還有機器動物。在研究人員的控制下,這些機器動物會在實驗中與有血有肉的活體動物互動。科學家們希望這樣的實驗能夠從全新的角度揭示:哪些因素能促使孔雀魚成為社交能手?蜜蜂是如何向同伴傳達信息的?以及,動物的社交生活還有哪些其他特征?
這聽起來可能有些不尋常,但事實上,相關研究早已開啟。機器人技術和計算能力的進步意味著工程師可以制造出足夠逼真的機器動物,使動物們將其視作同類并作出反應。“足夠逼真”的逼真程度因研究對象而異。有時機器動物必須外表逼真,有時需要氣味一致,有時它只要能移動就行。
與活體動物相比,機器動物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它們會按照研究人員的指令,一次又一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完成任務。這讓科學家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們的實驗,而其他任何方式都很難甚至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如果你能制造一個機器動物,讓它作為眼線混進一群動物里,而動物們又能接納這個機器動物并把它當作群體中的一員,然后你就可以讓機器動物執行任務,看看真正的動物會有什么反應。”紐約羅徹斯特大學的動物認知研究員多拉·比羅說。
借助機器動物,研究人員可以將各種因素分離開來,例如魚的大小和它的經驗,而這些因素在真實動物身上是無法分離的。他們可以讓真實動物一遍又一遍地接受完全相同的刺激,從而加快實驗進程。有時,他們還可以在完成目標的同時避免動物面對真正的捕食者或潛在的物種入侵風險。
以下是五種仿生機器動物,研究人員正在利用它們研究和控制特定情況下真實動物的社交互動。

潛入蜂巢的機器蜂
著名的蜜蜂“搖擺舞”在60多年前已經為人所知——返巢的工蜂在蜂巢入口附近按照特定路線快速移動并振動翅膀和身體,它們用這種方式來告訴同伴食物的位置。但研究人員仍不清楚它們蜂巢中的同伴們是如何對這些信息進行解碼的。“信號的含義是什么?舞蹈中的哪些部分真正傳遞了信息?哪些只是無心的動作?”柏林自由大學的機器人專家蒂姆·蘭德格拉夫問道。他認為,這些是機器蜂要完成的任務。
蘭德格拉夫制作了一個真蜜蜂大小的模型——一個帶有單翼的蜜蜂模樣的粗糙塑料球——并將其連接到一個機械驅動系統上,以便控制模型移動、振動的位置及方式。將機器蜂放進蜂巢后,蘭德格拉夫發現,機器蜂確實可以引導真正的蜜蜂找到食物源,甚至是它們之前從未用過的食物源。這個結果是對理論的有力證明。
但機器蜂的成功并不可靠。蘭德格拉夫說:“有時蜜蜂會在幾秒鐘內跟隨,但有時卻需要幾天的時間,而我們無法解釋原因。”他意識到,這其中還有一個他從未考慮過的問題——蜜蜂如何從跳舞的工蜂中選出自己要跟隨的那一個,以及怎么決定要在何時跟隨。他想知道,潛在的追隨者們是否在積極尋找有關食物來源的信息,還是舞蹈者必須以某種方式說服它們?是否只有少數具備經驗的工蜂才能明白所有特定的信號?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蘭德格拉夫和他的團隊正在研發一種升級版的機器蜂——它具有更真實的氣味和更可靠的翅膀振動機制,可以進入一個布滿獨特標記的蜜蜂蜂巢——并希望可以借此追溯活體蜜蜂的經歷。盡管新冠疫情延誤了時間,他們最終還是開始了系統測試,只是暫未得到結果。不過,蘭德格拉夫說:“我估計,我們很可能會有一些新發現。”
當隼來襲時,一群鴿子會有什么反應?經典的“自私牧群原理”假設,每只鴿子都會在遇襲時努力擠進鴿群中間,從而導致捕食者帶走其他不幸的同伴。但這個想法并不容易驗證。隼的每一次攻擊都不相同——起始位置的高度及角度都可能不同,而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影響鴿子的反應。因此,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行為生態學家丹尼爾·桑基開始使用機器隼。
“這種可控的方式非常利于研究。”桑基說,“你可以確保在放飛鴿子時,隼總是正好落后20米,并且可以重復操作。”此外,他指出,機器隼對鴿子來說更安全。“據我所知,曾經發生過一只訓練有素的隼消滅了一群鴿子的事。”
一名隼愛好者用他的機器隼幫助了桑基。除了多出一個驅動它的螺旋槳,這只機器隼的外表可謂栩栩如生。桑基反復“攻擊”了一群信鴿,同時通過GPS跟蹤每只鴿子的位置。他發現,與“自私牧群原理”相反,鴿子在受到攻擊時并沒有努力往鴿群中間擠。

機器隼“攻擊”鴿群。
此外,桑基的分析表明,這些鴿子大多試圖與同伴同向飛行,這樣鴿群就能一致躲避攻擊,而不會有任何鴿子掉隊落入捕食者的手中。“這表明,它們可以通過團結協作一起逃離捕食者,并且不犧牲任何同伴。”桑基說。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這表明鴿群可能是有合作精神的,它們并不自私。
魚群里的哪條魚最有可能成為首領?大多數研究表明,體型較大的魚往往對魚群的前進方向影響較大。大魚通常更年長、更有經驗,而且它們的行為也與魚群中的小魚不同。但這些因素中的哪一個對成為魚群首領影響最大?這很難用真正的魚來測試。“你怎么才能讓一條大魚表現得像一條小魚呢?這些都只能用機器動物來測試。”柏林洪堡大學的動物行為學家延斯·克勞澤說。他在2021年的《控制方法、機器人技術和自動系統年評》中與人合作撰寫了行為學研究中有關機器動物的綜述。
克勞澤和他的同事研發了機器魚——一種安裝在磁性底座上的3D打印孔雀魚模型,由水箱下方的電動裝置驅動。兩個與計算機相連的攝像機可以讓機器魚即時對同伴們的行為作出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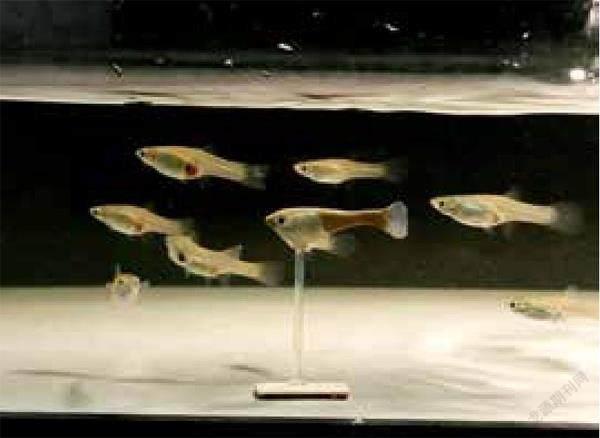
魚群將機器魚視作了同類。
他們發現,只要模型有眼睛并且色彩圖案與真魚大致相似,孔雀魚就會把模型當作普通活體魚,并作出反應。這讓研究人員能夠在保持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更換更大或更小版本的機器魚,以便單獨研究體型大小的影響。他們發現,孔雀魚果然傾向于追隨個頭更大的機器魚首領。該團隊還使用機器魚來研究個體魚的行進速度如何影響群體行為。
團隊還發現了另一個關于魚群首領的令人驚訝的事實:社交禮節很重要。他們早期版本的控制程序會導致機器魚過于靠近同伴,這迫使真正的魚后退以保持距離。“我們有一些機器魚還會追逐活體魚。”克勞澤回憶道。后來,團隊對機器魚進行了調整,以便讓它們保持禮貌的社交距離。而新版的“社交能手”機器魚用事實證明,它們在吸引追隨者方面有絕對優勢。
先前的研究都是讓機器動物進入活體動物群,以刺激活體動物作出反應。此外,還有一種單獨使用機器動物來解析動物行為的方法:對一群機器動物進行編程,使其遵循你所知的真實動物的行為規律,看看它們是否能復刻真實動物的行為方式。
這就是哈佛大學集體行為研究員賈斯汀·韋費爾所采用的方法。韋費爾想了解白蟻是如何建造如此復雜的蟻丘的,這些蟻丘因為入口處的溝槽陣列而聞名。他把研究焦點集中于建造過程中的一個特定步驟——白蟻如何為從蟻丘中挖掘出來的土選擇傾倒地點。這個簡單的判斷決定了蟻丘入口的復雜形狀。
韋費爾和同事們獲得的一些證據表明,白蟻可能會在蟻丘內部高濕度區域與地表干燥空氣的交界處傾倒泥土,這是它們家園邊界的一個很好的標志。但他們不知道白蟻的倒土行為是否也受其他因素影響。
所以他們制作了一群機器白蟻。由于機器白蟻不必與真正的昆蟲互動,它們不必顯得栩栩如生。相反,這些機器白蟻其實是磚塊大小的推車,它們可以在平坦的表面上運送和卸下彩色積木。每只“白蟻”都攜帶著一個濕度傳感器,程序會操控它們在濕度高時攜帶積木,在濕度下降時卸下積木。與此同時,當每只“白蟻”移動時,會有一個倉鼠管道不斷地滴水,以確保機器白蟻占領區的濕度更高。

科學家利用機器白蟻研究白蟻的蟻丘和倒土行為。
“我們知道機器白蟻只關注濕度,因為這是我們給它們的指令。”韋費爾說。事實證明,這就足夠了。因為最終,機器蟻群在它們的“蟻丘”入口卸下了積木,它們甚至像真正的白蟻一樣,在有風的日子里封閉了入口。當然,韋費爾指出,雖然這并不能證明白蟻是完全根據濕度規則來建造蟻丘的,但卻可以表明,這樣的規則足以讓它們完成任務。
仿生機器動物不僅能揭示動物的行為秘密,它們可能很快會被用在特定領域操縱活體動物。
食蚊魚原產于美國南部,現已成為全球百大入侵物種之一。西澳大利亞大學的行為生態學家喬瓦尼·波爾維里諾決定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控制仿生機器動物。

科學家試圖用機器大嘴鱸魚恐嚇入侵物種食蚊魚。
波爾維里諾和他的同事們制作了一種機器魚,把它設計成大嘴鱸魚的樣子。在食蚊魚的原生水域中,大嘴鱸魚是它們的主要捕食者。科研人員對機器魚進行編程,使其氣勢洶洶地游向食蚊魚,希望以此恐嚇入侵物種,同時又不影響到澳大利亞的本土物種。(許多野生動物都會表現出持久的恐懼反應。)
而這正是他們所看到的:每周僅與機器捕食者接觸15分鐘,食蚊魚體內的脂肪就會減少,用來逃生的能量增加,而用來繁殖的能量也相應減少。“它對食蚊魚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其他物種卻一點也不害怕,因為我們復制了一種在澳大利亞不存在的捕食者。”波爾維里諾說。
在將他的人造捕食者投放到現實世界之前,波爾維里諾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的機器魚在實驗室中表現良好。”他說,“不過,這是在附近設有一臺電腦、水箱上方裝有一個網絡攝像頭并且配備了電池的情況下實現的。”
即便如此,他仍決定與昆士蘭州的一個國家公園進行協商,因為在那里小而清澈的水池中生活著兩種瀕臨滅絕的魚類,而最近食蚊魚占領了水池。水池很小,這也許能為首次野外測試提供良好的環境。“目前還沒有作好準備,”波爾維里諾說,“但這件事是可以嘗試的。”
當然,當研究人員試圖將機器動物融入真實動物群體時,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有時,導致失敗的原因一點都不復雜。例如,當比羅試圖制作一只機器鴿來研究信鴿群的集體決策時,該機器鴿的飛行速度卻無法跟上真正的鴿群。盡管如此,以新方式測試動物行為的機會仍然讓她充滿期許,她希望某一天能再嘗試一次。“如果我們能讓這一切都正常運作,那么接下來就會有各種各樣有趣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比羅說,“這正是我一直期盼的。”
[編譯自美國《史密森尼》]
編輯: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