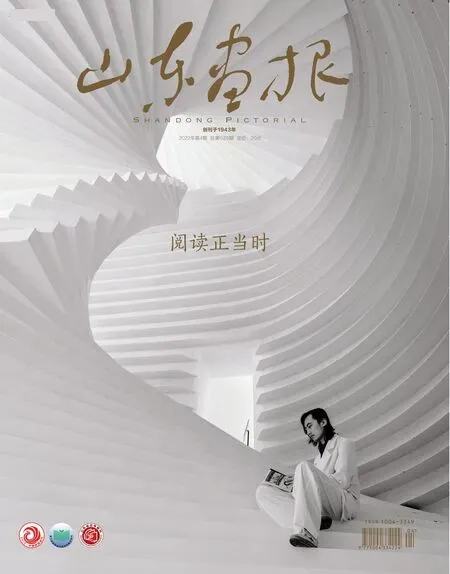“黨的忠實兒子”劉謙初
王立群 范承泰



“謙初是個好同志,可惜犧牲得太早了。他是一個有才能、對黨有貢獻的人,是黨的忠實兒子。他的犧牲,是黨的一大損失啊!”
——毛澤東
東劉莊,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這樣的村名我們大概能找到數十上百個。今天,我們要講述的東劉莊村,位于膠東半島腹地,距離青島下轄的平度市區仍有十公里的路程。村里一棟磚木結構的傳統式平房,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100多年前,房里走出的一名叫劉謙初的青年曾寫下這樣的詩篇:
“少年讀書不用心,不知讀書為黎民。早知讀書為黎民,高掌明燈用苦心。”
為實現“讀書為黎民”這一理想,劉謙初走出村子,走出平度,在36年的短暫人生中,為齊魯大地,為中華民族,為共產主義事業燃盡了一切。
追尋民族救亡之光
父親為劉謙初取了一個小名,叫“光”,而這似乎也注定他的一生,要為尋找“光”而奮斗,為父母,為鄉親,為民族。
1918年春,劉謙初考入齊魯大學,主修文預科。五四運動爆發后,濟南大中學校舉行聲勢浩大的罷課和游行示威活動。在游行時劉謙初帶頭高呼“誓死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等口號。為了防止學校學生繼續游行,齊魯大學校長巴慕德關閉學校校門,逼迫學生離校返鄉。回到家鄉以后,劉謙初創辦夜校,革除陋習,寫了《纏足歌》《放足歌》,為改變家鄉而奮斗。
1923年冬,劉謙初通過山東老鄉路友于介紹,認識了共產黨員方伯務和范鴻劼,并經二人介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后的幾年,劉謙初先后輾轉鎮江、武漢,并加入北伐軍。1927年1月25日,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已加入國民革命軍并擔任政治部理論刊物《血路》副主編,入黨后,他在《血路》上賦詩一首:光明勇向前,安危不顧保民權。兇殘日寇工農敵,黨比娘親勝過天。
1927年4月4日,在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上,劉謙初聆聽了毛澤東同志所做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演講。
1929年初,黨中央調他到山東工作,化名黃伯襄,以齊魯大學助教身份作為掩護,住在濟南東西菜園子街4號。4月,中共山東省委重新組建,劉謙初任省委書記。
短暫一生獻給最愛的“母親”
“望你不要為我悲傷,希你緊記住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好好愛護母親!孝敬母親!聽母親的話!”1929年8月,劉謙初在赴上海途中被捕入獄,他在獄中給妻子留下遺書。
劉謙初的妻子張文秋也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兩人在黃埔軍校相識,并于1927年在武漢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劉謙初知道,妻子會明白他所說的“母親”指的就是黨,而他是黨“忠實的兒子”。
為營救劉謙初,黨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張文秋也獲得了探監的機會,可是就在營救工作露出一線曙光時,情況卻發生了急劇變化。此時,韓復榘脫離馮玉祥部,改投蔣介石,為證明“剿共”有力,向蔣介石邀功,他指示部下將所有在押政治犯一律槍決。
1931年4月5日凌晨,天剛蒙蒙亮,在濟南緯八路侯家大院操場上,槍聲響了。劉謙初等22名共產黨員倒在血泊中。噩耗傳來,濟南僅有的11名黨員在市委書記胡允恭的組織下,化裝成工人、農民或商人,夾雜在人流中,到緯八路刑場向烈士們的遺體告別。富有正義感的律師李化南冒著“通共”的嫌疑,發電報通知了劉謙初的父親劉祿,并且積極幫助處理收殮等事宜。劉謙初的靈柩運回故里后,被安葬在村西南的劉家祖墳。
英雄故里訴說鐵血忠魂
現在的劉謙初故居,歷經數次修繕,依然保留著原始的風貌。走進老屋,正屋迎面墻上掛著劉謙初的大幅照片,照片前方的桌子上擺著一面鮮紅的黨旗。桌子兩側分別放置一個展示柜,里邊陳列著劉謙初學習和工作期間的相關資料,西南角和東南角分別建有一個灶臺。西邊一間為劉謙初父母的臥室,也是劉謙初出生的地方,南側建有一個炕,北側擺放著一張老式桌子,墻上懸掛著劉謙初生前使用過的相關物品照片。
置身故居之中,可以感受到房子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劉謙初的生命氣息,烈士生前使用過的每一個物件,都見證著一個鐵血男兒的錚錚鐵骨,訴說著英烈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不畏艱難險阻、勇往直前的感人事跡。走出正屋,站在庭院里,緬懷先列,撫今追昔,不由得讓人心潮澎湃。
2013年10月,劉謙初故居被命名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1月被命名為第三批山東省黨史教育基地。
如今,平度當地搜集了大量珍貴史料,在劉謙初故居的基礎上建設了劉謙初紅色文化園。文化園綜合運用浮雕、實景、影像等形式,真實生動地還原了劉謙初烈士血灑齊魯的感人事跡和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色家庭歷史。
現在的東劉莊村以劉謙初故居和紅色文化園為依托,已經成為集革命教育、文化體驗、田園觀光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紅色教育基地。劉謙初的革命精神,在新時代更加熠熠生輝。
(平度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圖 ?編輯/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