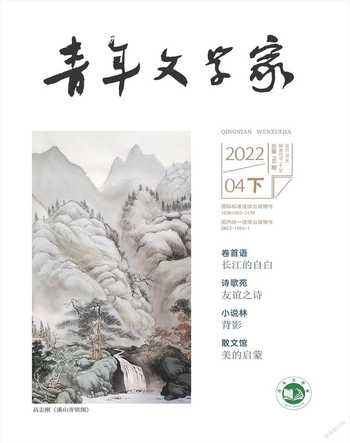圍城重重,何以突圍
詹凱璇
侯老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課上這樣評價《圍城》:這是一本經得起一讀再讀而又不至于失去趣味的書。我對此深有感觸,每每讀《圍城》,書中絕妙貼切的比喻、辛辣俏皮的語言及主人公的荒謬行事總不禁令人發笑。這部在困頓之中“錙銖積累”而成的文學巨著當然不止于趣味,更在于身處那個顛沛流離年代的錢鐘書先生對人類與人性的哲學思索,而要想品出其間的道理,讀者也須“錙銖積累”地讀。我想,經典便是如此,細品方能知其香,愈品香便愈濃、愈烈。
對《圍城》的“圍城”二字,從字面上理解是現實的“圍困的城”,有如錢老創作此書時風雨飄搖的上海。而就更深層次的內涵,“圍城”又可呈現為兩種指向,一是身外之城,也即人親手筑成的一切外物,學業、戀愛、婚姻、職業等皆可納入此城中;一是人性之城,由人的普遍心理特質筑起的內在的城,潛藏欲望、虛榮、權勢以及其他種種微妙心理,自然也包括向善的人性。
有人將方鴻漸的人生歷程形容為一次次的出走與逃離,從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方鴻漸邁出他優渥生活圈子的第一步,便是突圍與陷落的開始。求學不順、專業的頻換、出洋的輾轉,最后不學無術回國,他在學業圍城中幾經徘徊;他的事業也步步維艱,從點金銀行的小職員到三閭大學的教授夢,再到經趙辛楣幫忙聯系的報社任職;而在婚戀上,他更是一步一坑式地跳出跳入鮑小姐、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的溫柔陷阱,被迫困在愛情的圍城里周旋……他處處碰壁的困境人生在無數圍城中循環上演。
“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作為全書的題眼,這句話對小說內容和結構的串聯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以時不時冒出尖兒的潛伏狀態解釋著方鴻漸及他人的下一步行徑。或許是錢老的有意安排,當蘇文紈打趣方鴻漸問他是否知道這句話的由來時,方鴻漸正醉著酒搖頭說他不知道,自我的迷失感使得他鬼使神差地在城中輾轉。但究其事實,方鴻漸每每出城進城又確是有原因的。為什么城外的人想進城?身處城外,自然無法得知城中貌,總以為城里遠比所在的城外要來得更好,故闖入得心甘情愿;而進了城的卻又想著出去,同歸殊途,也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心理在暗暗作祟。
當然,有些城是走得出去的:城市淪陷了逃走便是,工作不想干跳槽便是,桃花劫咬牙狠心也就拒絕了,但方鴻漸卻總在城里城外不斷地走進去走出去,他的“出走”似乎沒有止境。這不禁令人思考,是否有座看不見摸不著卻始終籠罩著的“城”是走不出去的。
在書中,錢老有這樣精彩的描寫:“緣故是一年前愛她的自己早死了,愛她,怕蘇文紈,給鮑小姐誘惑這許多自己,一個個全死了。有幾個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記憶里,立碑志墓,偶一憑吊,像對唐曉芙的一番情感,有幾個自己,仿佛是路斃的,不去收拾,讓它們爛掉化掉,給鳥獸吃掉—不過始終消滅不了,譬如向愛爾蘭人買文憑的自己。”讀懂了這段話,就會明白,方鴻漸能走出一些城,譬如未發生的抑或發生了沒有結果的愛,但始終有些城是永遠無法走出去的。婚姻將過去一切包括婚姻在內的情絲斬斷,但在假文憑這件事已經漸漸被其他人甚至連書外的讀者遺忘時,他卻放不過自己這細枝末節的事。此時這張假文憑已經不是那張用來掩蓋無知的遮羞布了,而是變成了其中一座永遠阻止他逃離的人性之城。
“逃離-陷落-再逃離-再陷落”,欲望促使著人在經歷著如此的循環,看似是從一座圍城逃向另一座圍城,可當這一切是在人性自我筑成的銅墻鐵壁的圍城里不斷上演時,想要真正地逃出圍城便成了虛妄。那可以說,現實中的每個人都是方鴻漸,每個人都走在通向另一座城的路上,卻又被困在城中。就好比婚姻,當一個把束縛視作天敵,把自由視作天性的人,只是將戀愛當作展示自我的一種渴望,而不再將婚姻當作愛情的必由之路時,即使最終走進了婚姻殿堂,在按捺不住的人性欲望的操控下,難免不會有出城的想法。
除《圍城》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有另外兩座享有盛名的“城”,即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與沈從文的《邊城》,且這兩者也都表現出了某種人性的指向。但從人性之城的角度來看,書中的主人公在城里城外卻有著不同的生存狀態。《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離婚后物質的匱乏和親情的殘缺使她本能地沖出現實的城,而又意外地因一座城的淪陷被成全走進婚姻的身外之城,得到欲求的容身之所,使她陷入了以“圓滿”的形式敞開的人性之城,被圍困在自欺的安逸之中的白流蘇,已然喪盡突圍的勇氣。而遠在川湘交界的《邊城》,自然而理想的人性是被供奉或者說是被隔絕在城中的,所展現的人性是未被現代文明侵蝕的最完美的樣子,“是否突圍”在這里甚至成為了一個偽命題。翠翠從未走出過現實的城,也與愛情的身外之城擦肩而過,最后只能在這“無需突圍”的烏托邦式的人性之城里,陷入永遠未知的、朦朧的“等待”。
在這兩座“城”中,人性之城的存在似乎只是作為人性安放的容器,默認了突圍已經毫無意義。白流蘇的“不想突圍”、翠翠的“無需突圍”都囊括在方鴻漸的“無從突圍”之中,一齊最終指向了人性之城“何以突圍”的命題。即使是沖出了一重又一重現實的城、身外的城,也始終走不出人性層面上更堅固的銅墻鐵壁。正是《圍城》對“普遍的對命運的掙扎”這一潛在主題的完整揭示,故事的困境感和人物的悲劇感才得以更加突顯。“何以突圍”就不僅是人們對迷茫現實的質問,更是一種發自靈魂深處的求救,在生存困境中人性的掙扎展現出的荒涼,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正是這種在現代人性牢籠下上演的人性悲劇敲響了警鐘。《圍城》向我拋出“倘若人性本質就是一座圍城,那么圍城重重,何以突圍”的質疑后,也頻頻促使我去觀照現實中這難以突圍甚至無從突圍的人性圍城。但我心里清楚,《圍城》所要達到的,絕非只是表面的揭示,它就如同半夜的敲更人一般,在諸如虛偽、利己、虛榮等陰暗面暗涌時警醒著我,時時提防我莫跌入其中。
我想,《圍城》對我而言便是這人生永恒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