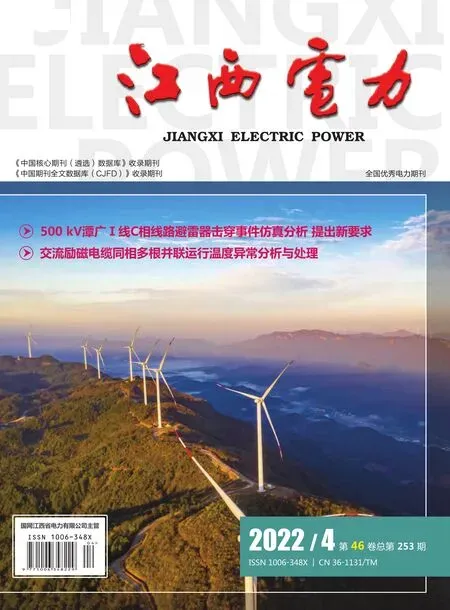汽輪機組定功率變壓運行耗差定量計算模型及應用
萬忠海
(國網江西省電力有限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96)
0 引言
依據汽輪機組原理,部分負荷下進汽壓力的選擇直接影響到機組的熱經濟性[1]。當汽輪機組定功率運行時,其在既定配汽方式與閥門開啟順序下進汽壓力與機組熱耗率之間的數值對應關系,可稱為汽輪機組定功率變壓運行熱經濟特性(下文簡稱變壓特性)[2]。研究汽輪機組變壓特性,不僅在精確確定閥點位置、制定自動變壓運行策略、進汽壓力耗差分析、數值量化調節閥節流調頻能損、數值量化調節閥重疊度本底節流損失等方面具有較為廣闊的工程應用價值,而且,可為煤電機組寬負荷深度調頻調峰運行方式的技術經濟比較以及調頻輔助服務的成本核算提供理論與實踐依據,對于煤電機組轉型有著積極意義。
傳統的汽輪機組運行方式優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求解機組在定功率下熱耗率最小值所對應的進汽壓力,大體可分為理論尋優和試驗尋優兩類。理論尋優的優點在于可采用窮舉法來確定出最優運行初壓,但其計算結果受現有技術能力的限制往往偏離現場實際[3]。試驗尋優的優點在于采用高精度等級試驗儀表對機組實際運行參數進行測試,數據樣本的代表性和準確性均較高。現役汽輪機組實際熱耗率通常在7 000~8 000 kJ·(kW·h)-1范圍,若以試驗結果不確定度±0.25 %為計,機組熱耗率的試驗誤差大致為±17.5~20.0 kJ·(kW·h)-1。仿真顯示,當進汽壓力變化±0.1 MPa 時,機組熱耗率變化±2.0 kJ·(kW·h)-1左右。因此,依據ASME PTC6-2004標準開展現場試驗難以精確辨析進汽壓力小幅變化對機組經濟性的影響;更不必談在試驗儀器、試驗條件等方面存在大幅降級的常規尋優試驗了。部分試驗人員單純地以搜尋最優運行初壓為目標對常規尋優試驗進行了改進。但實踐顯示,閥點尋優法易受調節閥重疊度的干擾,而耗差分析法往往單一看待變壓運行過程中理想循環效率、高壓缸相對內效率以及給水泵耗功對機組熱耗率的影響,忽視參數之間的耦合性。因此,這些改進試驗方法并未實質性地降低試驗不確定度;加之受樣本數量少的限制(通常3~5個),常規試驗尋優不適于研究變壓特性。
客觀而言,定功率運行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當進汽壓力變化時,機組熱耗率的“相對變化量”;至于機組熱耗率“絕對值”,只需滿足一般工程應用要求即可。顯然,對于測試變壓特性而言,熱耗率變化辨析度(即辨析進汽壓力小幅度改變時機組經濟性的相對變化量的能力)比機組熱耗率不確定度(即每一進汽壓力對應的機組熱耗率絕對值的測量誤差)更為實用。文中通過深入剖析汽輪機組定功率變壓特性內在機理及特征變量數值機理,構建出一種基于“機組熱耗率相對比較”的汽輪機組變壓運行耗差定量計算模型(下文簡稱耗差模型),實現了變壓特性的高精度復現,可顯著提升現場試驗的熱耗率變化辨析度。
1 變壓特性機理
1.1 變壓特性內在機理剖析
早期理論研究通過高壓缸內單位蒸汽的吸熱量和作功的綜合比較,并結合給水泵耗功,粗略地比較出再熱機組在部分負荷下節流配汽定壓運行、噴嘴配汽定壓運行以及噴嘴配汽滑壓運行之間熱經濟性差異[1]。文中認為上述方法同樣可用來分析同一機組在既定配汽方式和閥門開啟順序下的定功率變壓特性[4]。
圖1描述了高壓缸在定功率下變工況前、后的熱力過程。由于高排壓力的變化遠低于進汽壓力的變化,可近似認為變工況前、后高排壓力保持不變[1]。首先,假定高壓缸未設置回熱抽汽,變工況后單位蒸汽的高壓缸有效焓降的增益δ(Δh)(下文簡稱增功,kJ·(kg)-1)為:

式中:h0、′分別為變工況前、后的高壓缸進汽焓,kJ·(kg)-1;h1、分別為變工況前、后的高壓缸排汽焓,kJ·(kg)-1。
如圖1所示,當忽略再熱汽焓和鍋爐最終給水焓的變化(一抽壓力變化較小)時,變工況后單位蒸汽的循環吸熱量的增益δ(Δq)(下文簡稱增熱,kJ·(kg)-1)為:


圖1 高壓缸熱力過程
由于高壓缸未設置回熱抽汽,則再熱系數α=1;比較式(1)、式(2)可得δ(Δh)=δ(Δq);這意味著,倘若單位蒸汽由于進汽壓力變化而在高壓缸產生一定數額的增功;那么,必然會在鍋爐產生等額的增熱。從熱功轉換的角度而言,此時單位蒸汽吸收的增熱在高壓缸百分百地轉化為了增功。
由此,可進一步得出:當高壓缸設置一級或兩級回熱抽汽時,再熱系數α<1;此時,單位蒸汽的增熱將小于增功[1],其熱功轉換效率將大于100%;這便是變壓特性形成的內在機理。
1.2 變壓運行特征變量相關性分析
借助德國STEAG 公司EBSILON Professional 電站性能軟件開展汽輪機組在定功率變壓運行下的仿真建模[5]。仿真機型為四閥噴嘴配汽機組(閥門開啟順序為GV1/2 同步→GV3→GV4),額定參數為660 MW/24.2 MPa/566 ℃/566 ℃。受文章篇幅所限,并考慮到660 MW容量等級機組在480 MW負荷下可行滑壓區間[6]進汽壓力變化幅度較大,可有效揭示該機型在定功率下可行閥位區間內不同進汽壓力下機組熱耗率的連續變化趨勢,并展現出其定功率變壓運行的內在固有規律;故而,文中僅給出該負荷下的仿真與驗算情況。
圖2-4分別給出了在480 MW負荷變壓運行(主蒸汽/再熱溫度和背壓均為設計值且調節閥均處于無重疊度狀態)下的高壓缸有效焓降、理想焓降、循環吸熱量、高壓缸內效率、汽泵焓升及機組熱耗率的仿真計算結果。由圖2-4可知,隨進汽壓力的變化,受汽輪機閥點效應的影響,圖中各趨勢曲線均存在若干處拐點。參照相應調節閥閥位,這些拐點恰對應著不同的閥點工況。圖中由左往右出現的第一處拐點對應著三閥點工況;第二處拐點對應著兩閥點工況。文中的閥點工況泛指前序調節閥全開或接近全開(分別對應無重疊度或有重疊度狀態),后序調節閥全關的運行狀態。

圖2 高壓缸有效焓降
由圖2-3 可知,高壓缸有效焓降曲線、循環吸熱量曲線和機組熱耗率曲線受閥點效應影響在相同的進汽壓力下同時出現明顯的拐點特征;各圖曲線以趨勢線拐點為分界點,兩兩呈負相關性。由圖4 可知,汽泵焓升曲線同樣受閥點效應的影響而出現拐點特征(不及圖2 或圖3 般明顯);汽泵焓升與進汽壓力始終呈正相關性;但與機組熱耗率無明確相關性。

圖3 循環吸熱量變化過程

圖4 汽泵焓升變化過程
上述相關性分析進一步驗證了高壓缸有效焓降、循環吸熱量及給水泵耗功均是影響變壓特性的主要特征變量;高壓缸有效焓降的增益(即增功)和循環吸熱量的增益(即增熱)彼此呈正相關性。這里需要指出:對于通流部分結構一定的已投產機組,調節閥閥位的變化是引起汽輪機及熱力系統運行工況和汽水參數發生相應變化的根本因素;同時,在汽輪機組定功率運行下,只有當調節閥閥位的變化引起高壓缸有效焓降增加時,才有可能提升機組的循環效率。
2 耗差模型
2.1 變壓運行特征變量的數值機理
從能量轉換的角度而言,在汽輪機組定功率變壓運行過程中,如能測取單位蒸汽的高壓缸作功增益、中/低壓缸作功增益以及循環吸熱量增益,便可確定出機組熱經濟性的相對變化。
變工況前的循環效率為:

式中:H為變工況前的整機有用功,kJ·(kg)-1;Q為變工況前的循環吸熱量,kJ·(kg)-1。
變工況后的循環效率η′為:

式中:H′為變工況后的整機有用功,kJ·(kg)-1;Q′為變工況后的循環吸熱量,kJ·(kg)-1;δ(HH)為變工況后的高壓缸作功增益,kJ·(kg)-1;δ(HML)為變工況后的中/低壓缸作功增益,kJ·(kg)-1;δ(Q)為變工況后的循環吸熱量增益,kJ·(kg)-1。
依據ASME PTC6-2004,現場試驗不確定度來源有三項:一是流量的測量(含汽水系統隔離),二是功率的測量,三是溫度和壓力的測量。通常,前兩項在不確定度中占比>70%,是試驗誤差的主要來源(尤其是流量測量部分)。現場試驗中,求解主蒸汽在高壓缸中的作功和再熱蒸汽在中/低壓缸中的作功,需要測取包含流量在內的上百個汽水參數,不僅測試復雜,而且測量精度難以保障。
圖5 給出了在480 MW 負荷下的高壓缸作功增益、中/低壓缸作功增益、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以及汽泵焓升增益隨進汽壓力的變化趨勢。由圖5可知,這些曲線均受閥點效應的影響在相同的進汽壓力下出現明顯的拐點特征。其中,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與高壓缸作功增益呈正相關性且趨勢相近;汽泵焓升增益與中/低壓缸作功增益呈負相關性且趨勢類同。經大量仿真研究,“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和高壓缸作功增益”以及“汽泵焓升增益和中/低壓缸作功增益”這種趨勢的相關性是各種不同配汽方式、不同初參數等級以及不同熱力系統結構的汽輪機組的普遍規律。相比求解單位蒸汽的作功而言,求解單位蒸汽的高壓缸有效焓降或汽泵焓升,僅需知道高壓缸進/出口壓力和溫度或給水泵進/出口壓力和溫度等少量汽水參數,測試精度也易得到保障(相較流量測量)。

圖5 定功率變壓運行趨勢
同時,由汽輪機原理可知,熱力過程是因,流量是果。為維持一定的電功率輸出,熵增大的熱力過程需要更大的流量,反之亦然。除汽輪機次末級和末級外,定功率變壓運行的絕大部分熱力狀態點均可由溫度和壓力參數來確定。因此,結合前述變壓運行特征變量相關性分析,在式(4)中,以“易測量的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和汽泵焓升增益”代替“不易測量的高壓缸作功增益和中/低壓缸作功增益”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可行。為了保障計算精度,可引入焓降修正系數和熱力系統修正系數分別對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和汽泵焓升增益進行必要的修正,令二者分別趨近高壓缸作功增益、中/低壓缸作功增益。
2.2 耗差模型
基于變壓運行特征變量數值機理,并充分考慮汽輪機組變工況熱力參數間的相互耦合,引入焓降修正系數和熱力系統修正系數,構建出一種基于單位蒸汽熱耗率相對變化演算的汽輪機組耗差模型。在式(3)和式(4)的基礎上,可進一步求得:
變工況后,汽泵焓升的增益δ(Δτ)為:

式中:Δτ、Δτ′分別為變工況前、后的汽泵焓升,kJ·(kg)-1;
變工況前的循環效率η為:

式中:hf為變工況前的給水焓,kJ·(kg)-1;hr為變工況前的再熱汽焓,kJ·(kg)-1;α為變工況前的再熱系數;HR為變工況前的機組熱耗率,kJ·(kW·h)-1;
變工況后的循環效率η′為:

則,變工況后的機組熱耗率HR′為:

經驗顯示,再熱系數的變化所引起的系統誤差可通過焓降修正系數β和熱力系統修正系數γ來矯正;故令變工況后的再熱系數維持變工況前的數值,以精簡模型結構并減少相關測點數量。因此,式(7)可改寫為:

套用耗差模型時,變工況前的基準工況為四閥全開工況(對應進汽壓力最低),并以此工況各參數作為耗差模型的基準值;同時,再熱系數均維持基準值不變。依據機組在480 MW 負荷下變壓運行仿真計算結果,將相關特征參數代入耗差模型;通過調整修正系數β和γ的取值,觀測耗差模型的復現效果。
2.3 修正系數的取值
對于不同類型汽輪機組而言,焓降修正系數β和熱力系統修正系數γ與機組所處具體運行工況密切相關,難以定量計算。實際應用中,為獲取修正系數β 和γ 的取值需首先仿真計算案例機組的變壓特性(即圖6 中仿真熱耗率曲線);然后通過數值試湊,令模型熱耗率曲線與仿真熱耗率曲線之間的熱耗率最大復現偏差≤±1.0 kJ·(kW·h)-1。由圖5 可知,高壓缸有效焓降增益和汽泵焓升增益的變化和趨勢同樣受到閥點效應的影響。對于仿真機型,隨進汽壓力增大,可按閥點依次劃分為“四閥點—三閥點”、“三閥點—兩閥點”以及“兩閥節流”三段。因此,模型以閥點為分界點,對焓降和熱力系統分別實施分段修正,減小最大熱耗率復現偏差。如圖6 可知,模型熱耗率的變化趨勢與仿真結果一致(尤其是閥點處的拐點特征),說明耗差模型在構架上有效實現了各主要特征變量的有機整合;經分段修正,耗差模型的熱耗率復現偏差≤±0.5 kJ·(kW·h)-1。

圖6 精細修正結果
2.4 重疊度適應性
如圖7所示,重疊度2工況的壓力重疊度略大于重疊度1工況[7],相應調節閥節流損失也略大些,使得有/無重疊度工況之間的機組熱耗升高幅度更大且變化趨勢更為平坦(印證了前文所述重疊度對于閥點尋優法的干擾)。當修正系數β和γ分別維持2.3節無重疊度工況取值時,耗差模型的復現效果并未受到不同調節閥重疊度的影響。圖7(左)、(右)標注分別代表左、右縱坐標。

圖7 有/無重疊度工況復現效果
2.5 試驗工況修正系數和的獲取途徑
在前文的分析中,案例機組的變壓特性(如圖6仿真熱耗率曲線)是借助Ebsilon 仿真軟件通過全面性變工況計算而直接得到的。顯然,通過提取和運用仿真工況部分特征參數,借助耗差模型便可高精度復現出案例機組的變壓特性來(如圖6 模型熱耗率曲線)。因此,可推斷:提取和運用變壓運行全局尋優試驗工況[4]的部分特征參數,借助耗差模型可間接推演出試驗機組的變壓特性。無疑,為實現現場試驗應用,首先必須在無法通過ASME 熱力試驗直接得出試驗機組變壓特性的前提下,確定出合用的修正系數β和γ。由2.4 節可知,修正系數β和γ在不同調節閥重疊度工況下能被拓展應用。文中將這種修正系數和在同一機組不同工況和不同機組不同工況間拓展應用的屬性稱為熱力特征繼承性(下文簡稱繼承性)。為進一步探究修正系數β和γ的繼承性,將調節閥重疊度2 工況視為原生工況。在原生工況的基礎之上,假定汽輪機組的若干參數或指標出現惡化(如加熱器端差、主汽溫度、再熱汽溫、高壓缸內效率、中壓缸內效率、低壓缸排汽焓、給水泵效率、小機效率以及背壓等),由此形成衍生工況。這里,原生工況和衍生工況既可以代表同一機組的兩個不同工況(當主參數變化時),也可以代表兩臺不同機組的不同工況(當設備特性變化時)。
在衍生工況條件下,完成定功率變壓運行全面性變工況仿真計算,得到不同進汽壓力下的熱力系統參數和指標。相比原生工況,衍生工況的機組熱耗率平均抬升2%以上。將衍生工況下的部分特征參數和原生工況的修正系數β和γ(圖6 中數值),一同代入耗差模型,計算得到衍生工況下的模型熱耗率。由圖8 可知,在以上假定條件下,采用原生工況的修正系數和,衍生工況下模型的熱耗率最大復現偏差依舊≤±1.0 kJ·(kW·h)-1。

圖8 修正系數的適應性
經大量仿真驗證,修正系數β和γ具備優良的熱力特征繼承性。故而,可以通過類似的仿真計算,得到與試驗工況熱力特征大致吻合的修正系數β和γ,再應用于現場試驗當中。
2.6 現場試驗案例
與常規ASME 穩態試驗不同,汽輪機變壓運行全局尋優試驗[4]在既定閥序和定功率下,通過DCS 系統協調自動控制功能,采用“窮舉法”按一定速率連續小步幅調整進汽壓力的偏置,令調節閥閥位隨同進汽壓力的單向連續遞增(減)而單向連續遞減(增),實現定功率變壓運行試驗數據的動態采集。在完成試驗工況測試后,首先通過專業仿真軟件或符合ASME PTC6算例的EXCEL程序,確定出與試驗工況熱力特征大致吻合的修正系數和;然后,與相關試驗數據一同代入耗差模型,便可得出不同進汽壓力下機組熱耗率的相對變化量。圖9為某超超臨界機組在480 MW工況(調節閥處于無重疊度狀態)下的變壓特性曲線,圖中以進汽壓力為橫坐標。圖10 為某超超臨界機組在360 MW 工況(重疊度狀態)下的變壓特性曲線,圖中以總閥位指令為橫坐標。

圖9 480 MW變壓特性曲線

圖10 360 MW變壓特性曲線
由圖9-10 可知,耗差模型與全局尋優試驗方法相結合,可有效提升可行滑壓區間內當進汽壓力小幅變化時的熱耗率變化辨析度,使得通過現場試驗來獲取滿足一定精度的汽輪機組變壓特性成為可能。
2.7 局限性分析
耗差模型的局限性主要源自兩方面:其一在于試驗工況下熱力特征的復雜性。在汽輪機組的眾多參數或指標中,有一部分目前還無法精確實測或尚未可知;這將對修正系數和的繼承性產生不可預知的影響。其二在于試驗工況下邊界條件的穩定性。汽輪機組在定功率可行閥位區間內大幅改變進汽壓力,必然引起鍋爐與熱力系統的擾動。因此,為回避以上兩方面對耗差模型復現能力的影響,縮減進汽壓力的變化范圍是最為有效的應用措施。
3 結語
1)文中緊扣變壓特性內在機理,將單位蒸汽的“循環吸熱量”、“高壓缸有效焓降”以及“給水泵焓升”作為特征變量,并引入焓降修正系數和熱力系統修正系數,構建出一種基于“機組熱耗率相對比較”的汽輪機組耗差模型。經驗證,該模型對汽輪機組定功率進汽壓力小幅變化對機組熱經濟性的影響異常敏感,最大熱耗率復現偏差≤±1.0 kJ·(kW·h)-1,可精準地復現案例機組的全面性變工況仿真計算結果,計算精度滿足工程應用要求。
2)該模型結構形式簡易,與汽輪機變壓運行全局尋優試驗方法相結合,不僅能夠精確搜尋出最優運行初壓,而且能夠有效精確辨析可行滑壓區間內進汽壓力小幅變化對機組熱經濟性的影響,獲取較為完整且實用的變壓特性。現場試驗前,應事先運用專業仿真軟件或EXCEL編程,以閥點為分界點分段確定出與試驗工況熱力特征大致吻合的修正系數β和γ,以降低模型的系統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