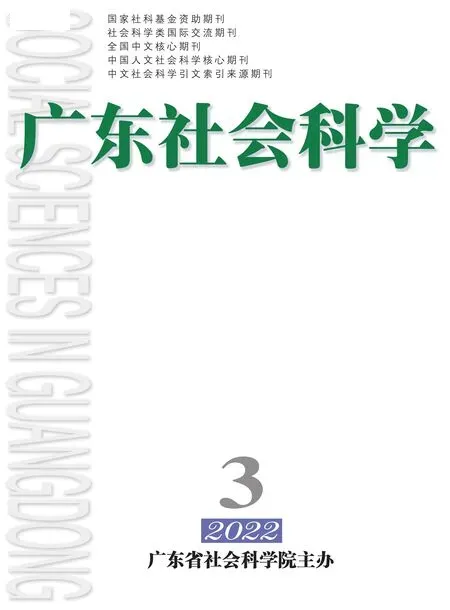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量刑建議的精準化*
楊 炯
自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2018年《刑訴法》”)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式寫入法律,并確立量刑建議制度的正式法律位階以來,理論界對檢察機關大力推進量刑建議精準化給予高度關注,相關研究亦日趨深入。其中,以具體技術設計層面的探討居多,對實踐運行狀況檢視及“精準化”如何界定等方面的實證和理論分析卻不多見。(1)參見趙恒:《量刑建議精準化的理論透視》,《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2期,第122頁。本文擬就此問題予以探討,以求教于同仁。
一、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之實踐考察
據筆者檢索和統計,(2)本文數據來源: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情況的中期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19年、2020年)及所發布全國檢察機關辦案業務數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等統計數據。微觀方面,本文主要以G省和G省的F市、F市的N區三級區域為例,從中國裁判文書網通過高級檢索欄目進行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具體檢索方法為:“全文檢索”關鍵詞設置為“認罪認罰”,“案件類型”設置為“刑事案件”,“審判程序”設置為“刑事一審”,“文書類型”設置為“判決書”,“裁判日期”設置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公開類型”設置為“文書公開”,“地域及法院”分別設置為“G 省”“G 省F 市”“G 省F 市N 區”,并根據網站頁面(每頁顯示10份判決書)等距翻頁取樣。〕各隨機抽樣100份判決書(2021年1?5月每月各隨機抽取20份),同時結合上述地區所發布數據和現場調研收集相關數據。表1、表2、表3數據來源: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G省、F市、N區判決書樣本統計數據。2021年上半年,全國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適用率、量刑建議法院采納率和確定刑量刑建議占提出量刑建議比例分別達到85%以上、95%以上和89%,G 省全省分別達到86%以上、92.57%和94%以上,F 市全市分別達到90.50%、94.67%和96.33%,N 區分別達到91.21%、96.69%和98.74%。可見,單從案件數來看,迄今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確定刑量刑建議已成為我國刑事案件辦理模式的絕對主導類型。對量刑建議具體運行狀況分析如下:
(一)確定刑量刑建議的界定尚未清晰
本文隨機抽樣樣本案件中,提出量刑建議刑罰類型具體包括“主刑”“主刑+罰金”“主刑+緩刑”和“主刑+罰金+緩刑”等幾種組合形式。(1)主刑量刑建議中僅出現確定刑和幅度刑兩種形式;(2)建議判處罰金的量刑建議中,存在僅建議“并處罰金”和提出具體罰金金額兩種情形,樣本中未發現罰金金額為幅度的情形;(3)適用緩刑量刑建議中,存在僅建議“適用緩刑”、提出具體緩刑期限考驗期限及“可以適用緩刑”的模糊表述三種情形,樣本中亦未發現緩刑考驗期為幅度的情形。
在認罪認罰試點期間及全面推行初期,檢察機關優先考慮力推的是主刑確定刑量刑建議,附加刑(罰金、沒收財產)和執行方式(緩刑)等適用是否明確則放在次要位置,相比于主刑的要求較為寬松。從樣本統計情況來看,檢察機關在主刑確定刑已達到較高比例后,則開始注重提出具體罰金金額和緩刑考驗期限的量刑建議。樣本案件中,G省、F市、N區檢察機關提出具體罰金金額的量刑建議分別占建議判處罰金人數的22.64%、52.83%、72.16%,提出具體緩刑期限考驗期限的人數分別占提出適用緩刑量刑建議人數的33.33%、70.80%、84.62%(見表1)。從數據對比來看,雖然G省的F市和N區提出罰金金額和具體緩刑考驗期限的量刑建議占比均達半數以上,但G省全省占比還只約為三成,說明有些地區已將提出主刑和附加刑、執行方式均確定的量刑建議作為提高量刑建議精準化的目標,而有些地區雖然該情形的量刑建議比例有所提升,但仍以主刑是否確定作為精準與否的衡量標準。當前,檢察機關仍是以主刑是否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作為該業務數據的統計標準,附加刑和執行方式確定與否則并不在統計之列。

表1 樣本中量刑建議提出具體方式及占比情況
(二)幅度刑量刑建議幅度差異較大
樣本案件中共檢索出6件幅度刑量刑建議案件(見表2),均屬于被告人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案件。其中,1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的量刑建議幅度均比較小,但量刑建議在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量刑建議的幅度大小差異則較大,且相對于宣告刑刑期,有的量刑建議幅度跨度過大。從法院判決采納情況看,宣告刑刑期與量刑建議幅度中最近值的差距并不大,但其中幅度較大的量刑建議與偏離較大值的差距則比較大。可見,檢察機關在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議上雖已具備縮小幅度區間、提高幅度刑量刑建議準確性的條件,但由于缺乏相應規范的約束和指引,導致有些案件仍采用幅度較寬的量刑建議。

表2 樣本中幅度刑量刑建議對比分析
(三)法院采納量刑建議各有差異
當前,檢察機關僅以主刑量刑建議是否被法院采納作為采納率的統計口徑,但事實上對罰金及適用緩刑量刑建議采納與否也屬于法院采納范圍。單從主刑量刑建議采納情況來看,G省、F市、N區的法院采納率均超過了9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這一比例并未考慮罰金與適用緩刑是否采納情形。實踐中,判處罰金和適用緩刑量刑建議的采納情形相比主刑要更為復雜,樣本案件中分別存在法院完全采納、法院完全未予采納以及未建議判處罰金或適用緩刑但法院判決罰金或適用緩刑、法院判決改變罰金數額或改變適用緩刑考驗期限等多種情形。從采納比例來看,采納罰金量刑建議的比例亦超過了90%,僅略低于主刑的采納率;采納適用緩刑量刑建議的比例則明顯低于其他兩類,樣本中采納適用緩刑量刑建議占比分別為G 省59.57%、F 市87.27%、N 區88.37%(見表3)。可見,檢察機關提出主刑量刑建議準確性最高,罰金量刑建議的準確性也明顯高于緩刑適用的量刑建議。提高適用緩刑量刑建議水平,是檢察機關接下來面臨的主要任務。

表3 樣本中法院采納量刑建議情況
二、量刑建議精準化的理論解讀
“精準”,即“非常準確、精確”。量刑建議精準化,顧名思義就是要推動量刑建議變得更為“精確”。就量刑建議而言,究竟何為“精確”,當前學界還缺乏深入、系統的探討,本文在此作一個粗淺的梳理。
(一)“精準化”的邏輯剖析
根據前述實證分析,從對量刑建議精準化的衡量方法來看,當前實踐中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根據量刑建議的提出方式,即是確定刑還是幅度刑來判斷(幅度刑又要看其區間大小),越確定即越精準;二是根據是否為法院所采納來判斷,從個案來看,完全采納即“精準”,就某段時間某個辦案單位的辦案總量來看,法院采納率高,即更為“精準”。事實上,這兩種方法在邏輯上可以歸結為一個標準,即以宣告刑為參照,量刑建議提出的刑罰與之越接近的就越“精準”。當前,學界對這種實踐方法和邏輯的檢視,并未給予相應的關注。不管是量刑建議采取確定刑或幅度刑,被法院采納與否,還是看其與宣告刑的一致程度等來衡量,歸根結底都是從刑事訴訟程序的角度來進行評價。此類標準,姑且稱之為“形式精準化”或“程序精準化”。與之相對應則是“實質精準化”或“實體精準化”,即量刑建議最終是否實現了刑罰的正當化。當然,在認罪認罰案件中,采取確定刑量刑建議對于實現刑罰目的具有一定的優勢,(3)參見陳國慶:《量刑建議的若干問題》,《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5期,第9—11頁。但從邏輯上來看,“形式精準”并不必然導致“實質精準”,這亦為實踐所證實,比如法院配合和抵觸的雙重背反等情形,完全有可能背離實質精準要求。(4)參見趙恒:《量刑建議精準化的理論透視》,第135頁。
這種邏輯關系,可用邏輯符號演示如下[以下符號僅以主刑和附加刑、執行方式均確定(即絕對確定刑,見后表4分類)、主刑確定但附加刑和執行方式不確定(即相對確定刑)和幅度刑三種情形為例]:
①量刑建議,記為A;
②宣告刑,記為B;
③絕對確定刑量刑建議(量刑建議與宣告刑完全一致),記為A=B;相對確定刑量刑建議和幅度刑量刑建議(即量刑建議刑罰范圍大于且包含宣告刑),記為A?B;實現正當化目標的刑罰,則為B=C;
④將法院采納量刑建議成為宣告刑,以及宣告刑實現刑罰正當化目標,記為推導符號“├”,反之記為推導否定符號“?├”;那么,符合形式精準化量刑建議,記為U(不符合形式精準化量刑建議,記為?U),則U=[A ├(A=B)]∨[A├(A?B)],不符合形式精準化的量刑建議,即量刑建議幅度小于宣告刑及完全偏離宣告刑情形,對應記為?U=[A?├(A=B)]∨[A?├(A?B)];
⑤通過形式精準化實現實質精準化情形,符號化演示為:[A├(A=B)├(B=C)]∨[A├(A?B)├(B=C)];
⑥實踐中,形式精準化并不必然導致實質精準化,符號化演示為:{[A ├(A=B)├(B=C)]∨[A├(A?B)├(B=C)]}∨{[A ├(A=B)?├(B=C)∨[A ├(A?B)?├(B=C)]}。
上述情形,歸納如下圖1所示:

圖1 形式精準并不必然導致實質精準邏輯推演圖
實踐運行情形則為形式精準化與非形式精準化的合集,即U∨?U={[A├(A=B)├(B=C)]∨[A├(A?B)├(B=C)]}∨{[A├(A=B)?├B=C]∨[A├(A?B)?├B=C]}∨{[A?├(A=B)?├(B=C)]∨[A?├(A?B)?├(B=C)]}。其中,[A?├(A=B)]∨[A?├(A?B)]也可以表示為[A├(A≠B)]∨[A├(A?B)]。
可見,形式精準化雖然是實現實質精準化的必由路徑,但是做到了形式精準化,卻并不一定會實現實質精準化,實質精準化需要一并納入量刑建議精準化改革任務之中。
(二)量刑建議精準化的三重釋義
其一,形式精準化與實質精準化相統一的“精準化”。當前實務中提出的形式精準化追求目標,正當性和必要性都不言而喻。(5)參見陳國慶:《量刑建議的若干問題》,第9—11頁。同時,必須準確把握二者之間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相對于實質精準化,形式精準化只是手段,實質精準化才是目的,而且作為手段的形式精準化也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價值。一方面,應當堅定地推進形式精準化改革,將確定刑量刑建議比例和法院采納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形式精準化必須服務服從于實質精準化,即當形式精準化與實質精準化發生沖突時,必須堅持實質精準化標準。
其二,追求全范圍覆蓋的“精準化”。法律明確將確定刑和幅度刑作為量刑建議的提出方式,遵循了法律模糊性的規律,實踐中也應當按要求分別適用。如將“精準化”單一化、簡單化,盲目追求100%,必然適得其反。同時,還需看到精準化的相對性,對確定刑而言,符合適用絕對確定刑時,絕對確定刑更為精準;同理,對幅度刑而言,符合適用確定刑條件時,確定刑當然更為精準;就幅度刑本身而言,幅度越小越精準。因此,“精準化”并非僅僅是指確定刑的精準化,應為包括幅度刑在內的量刑建議提供不同的“精準化”解決方案。
其三,存在限度與梯階的“精準化”。法律的模糊性并不意味著其無法量化,不能追求“精準化”。就刑罰而言,只要達到社會公眾可以接受的一定程度,人們就認為這個裁判是公正的。因此,追求量刑建議的精準化,不是要追求“0”或“1”的絕對答案,而是用定量的方法“在不確定中尋求確定性”,(6)葛洪義、陳年冰:《法的普遍性、確定性、合理性辨析》,《法學研究》1997年第5期,第82頁。這個“確定性”就是社會公眾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圍。模糊數學的模糊集合,可為量刑建議精準化提供量化方法。按照形式精準化與實質精準化相統一的要求,可根據精準化與否及其程度簡要分為如下層次:(1)絕對確定刑量刑建議實現實質精準化情形,即A├(A=B)├(B=C)情形,為精準化程度最高層次;(2)幅度刑量刑建議實現實質精準化情形,即A├(A?B)├(B=C)情形;(3)量刑建議未符合形式精準化或實質精準化要求,但通過調整程序后實現精準化的情形;(4)量刑建議與形式精準化、實質精準化要求存在微弱或較小差距,且該差距可為社會公眾基本接受情形,如用“≈”表示,即A≈B、B≈C情形;(5)嚴重偏離精準化程度的量刑建議,即A├(A≠B)]∨[A├(A?B)情形。
綜上,量刑建議精準化,是形式與實質相統一的精準化,而且前者是實現后者的重要方式,當二者面臨沖突時要以后者為基準。量刑建議精準化,追求的是認罪認罰案件全覆蓋的精準化,不僅體現在確定刑和幅度刑之間的合理選擇上,而且體現在采用確定刑和幅度刑后,如何進一步追求精準的“精準化”。量刑建議精準化,還是一種存在限度和梯階的精準化,對“可接受”的非“明顯不當”的量刑建議,各方都應當保持適當的“寬容”,基于效率等價值的考量予以接納。

圖2 量刑建議精準化程度示意圖
三、“形式”與“實質”并重的改進設想
隨著量刑建議制度的發展,域外也呈現出兼顧“實體上的量刑公正”與“程序上的訴訟效率”的發展傾向。(7)參見石經海:《量刑建議精準化的實體路徑》,《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2期,第12頁。由于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等差異,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量刑建議的價值取向上各有不同。重視實質真實,追求實體公正,在我國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追求量刑實體公正自然是我國量刑建議制度的首要目標。(8)參見石經海:《量刑建議精準化的實體路徑》,第13頁。從前述邏輯分析來看,形式精準化是基礎和前提,做到形式精準化有助于實現實質精準化;同時,基于形式精準化并非必然導致實質精準化,從而需要法院對形式精準化進行審查,并通過審查機制之完善,以實現從“形式”到“實質”的轉變。
(一)規范分類和提出方式
在我國未來刑事訴訟制度中,是否對認罪認罰案件和非認罪認罰案件采取相同的法定類型量刑建議,還需實踐探索。就當前而言,宜將二者區別對待。對于認罪認罰案件,建議未來采取絕對確定刑、相對確定刑和幅度刑三種類型(即表4中的三分法)。雖然從實踐運行來看,有些地區絕對確定刑和幅度刑(即表4中二分法)類型案件已成為主流,但這并不意味著未來即可以一刀切地全部采取二分法的方案。考慮到部分案件的復雜性和新類型案件、新罪名的不斷出現,以及檢察官對罰金和緩刑適用的把握難度等因素,對檢察機關當前只提出“并處罰金”和“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形式予以適當保留。但是,對這種提出方式和適用范圍應予以明確規范,一方面,對當前實踐中的“可以適用緩刑”模糊表述方式應予以舍棄,此種表述方式對法院審查并無太大的實質意義;另一方面,對多數案情簡單的案件,應當提出具體金額和具體考驗期限的量刑建議,對少數案情復雜的案件,則可只提出是否判處罰金或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

表4 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建議分類
從當前實踐來看,采用確定刑特別是絕對確定刑量刑建議,還難以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分案件類型推進。(9)參見李剛:《檢察官視角下確定刑量刑建議實務問題探析》,《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1期,第29頁。實踐中,可根據案件類型對應參照優先適用確定刑及絕對確定刑量刑建議類型。提高幅度刑量刑建議精準化,則可借鑒有人提出的限定幅度范圍的方式,比如要求判處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分別不得超過6個月、2個月、1年,其他有期徒刑的幅度一般不得超過2年等。(10)參見徐漢明、胡光陽:《我國建立量刑建議制度的基本構想》,《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第31頁。主刑為幅度刑時,附加刑和執行方式,原則上也應當按照表4所述分類方式提出。
(二)明細量刑建議的調整尺度
根據2019年“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認罪認罰意見》)第41條規定,存在“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有異議且有理有據的”兩種情形時,法院應當告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對何為“明顯不當”,何為“有理有據”,實踐操作中存在很多的分歧。對于“明顯”的理解,苗生明、周穎提出,“應當從一般人的正常認知角度進行判斷,具體可以從量刑建議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與同類案件處理明顯不一致、明顯有違一般司法認知等方面把握”。(11)苗生明、周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的基本問題—— 《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 的理解和適用》,《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6期,第23頁。這三個方面雖然具有一定方向性的指引意義,但還難以解決實踐操作中的各類問題。未來的制度規范,需要從邏輯上厘清和貫徹實質精準化的要求。不管是前者的實體標準,還是后者的程序性標準,第41條規定實質上都可以歸結為實質精準化的一個標準,即量刑建議是否符合實體公正的要求。如量刑建議能做到罪刑相適應,實現犯罪預防的目的,即便被告人或辯護人提出異議,也無調整必要。結合《認罪認罰意見》第40條和第41條規定來看,如果在前期辦案或提出量刑建議過程中,存在嚴重違反“程序正義”情形,比如第40條規定違反自愿原則及其他影響公正審判情形等,法院應當不予采納后依法作出裁判。可見,這里的“明顯不當”只限于實體上的“不當”。為避免法院隨意啟動調整程序或放棄審查義務的過度“配合”,各地法檢系統之間應當就此統一尺度,比如當“明顯不當”的程度超出一定限度比例時,即應啟動調整程序。當然,究竟多少比例更合理,還需要實踐的探索(參考表5中的“χ%”)。
(三)確立與實質精準化對應的采納方法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法官裁判權的影響,成為該制度推行以來備受爭議的議題之一。與域外辯訴交易制度中法官僅進行程序上的審查相比,(12)參見楊佳:《美國辯訴交易制度與德國協商制度之比較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寧夏大學,2013 年,第42頁。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計中仍然堅守“全面貫徹法官保留原則”,法官享有全面的司法審查權和最終的裁判決定權。(13)參見趙恒:《量刑建議精準化的理論透視》,第129頁。有人擔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特別是量刑建議精準化會侵蝕裁判權,將量刑建議變成“量刑要求”“量刑指令”。(14)參見臧德勝:《科學適用刑事訴訟幅度刑量刑建議》,《人民法院報》2019年8月29日,第2版。從實質精準化角度看,這種擔憂缺乏依據,因為如果量刑建議能夠做到罪刑相適應,實現刑罰目的,法院通過審查予以認可,這相當于是直接給了法官一個正確的裁判結果進行參考使用,不僅不存在權力“侵蝕”,相反還能提高法官辦案效率。反之,如果量刑建議符合不予采納情形,法官依法作出裁判,不僅談不上“侵蝕”,而是更加彰顯法官的裁判權。
因此,真正需要擔憂的不是量刑建議的精準化會導致“侵蝕”裁判權的問題,而是如何要在量刑建議制度中磨合公訴權和審判權的運行機制,以更好地實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及量刑建議制度的價值,這也是實質精準化的意義所在。林喜芬教授認為,2018年《刑訴法》和《認罪認罰意見》對采納模式規定雖然內容相似,但規范結構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推定接受型”,后者是“審查接受型”。(15)參見林喜芬:《論量刑建議制度的規范結構與模式——從〈刑事訴訟法〉到〈指導意見〉》,《中國刑事法雜志》2020年第1期,第3—16頁。不管是“推定接受”還是“審查接受”,指的是法官審查和接受的方法不同而已,“推定接受”也并非意味著可以免除法官的實體審查義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只存在“審查接受型”一種模式。在采納標準方面,形式精準化即量刑建議是采取確定刑還是幅度刑,顯然并不能作為法官采納與否的標準,只有量刑建議實質精準化才具有這一功能。根據實質精準化要求,可考慮參照表5步驟和標準進行審查。
表5中,筆者以χ%來表示一般不當與明顯不當的劃定界限,即當量刑建議刑罰與法官審查測算的刑罰之間的差距大于χ%時,則認為該量刑建議存在明顯不當。對于χ%值的大小,有人提出按照10%的標準來確定。(16)參見黃黔:《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量刑建議》,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19年,第33頁。由于不少罪名案件之間的幅度差異較大,一刀切地采取同一比例恐怕難以做到罪刑相適應。故筆者以為,χ%值的確定宜以實踐探索為依據,即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運行一段時間之后,根據不同類型案件的實踐運行情況來確定,例如通過對全國或某個區域一定時期內的某個(或某類)案件進行實證統計分析,找出實踐中法院對該類案件認定存在明顯不當的比例平均值(或多數案件所采用比例),作為參考標準;同時,χ%值的確定,還需要綜合權衡不同時期社會發展和社會公眾對法治需求的變化,不同時期司法政策和社會公眾對不同犯罪適用刑罰幅度的接受程度,以及適用χ%標準是否會突破責任刑上限和符合犯罪預防目的等因素。由于全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χ%值的確定,不宜一開始即推行全國統一標準,可在確定全國性指引標準基礎上,授權各地根據本地區實踐情況自行確定。

表5 量刑建議“形式與實質”審查及采納方式
結 語
追求實質精準化無疑是量刑建議精準化的邏輯歸宿,但要達成這一目標,同樣離不開形式精準化的邏輯演進。可見,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確立初期,檢察機關從量刑建議的形式精準化切入無可厚非;不過,不能因此而忽視量刑建議制度創設對于刑罰公平正義追求之目標。此外,雖然量刑建議精準化改革主要由檢察機關發起和推動,但是作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個關鍵程序,量刑建議精準化及其功能的實現,亦與辯護、審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密切相關,既涉及司法機關之間的權力平衡,也攸關當事人的人權和權利保障。因此,除控、審之外,其他各方在量刑建議精準化改革中的角色演繹及利益調適,亦需合理權衡,本文借此拋磚引玉,呼吁學界拓展對該領域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