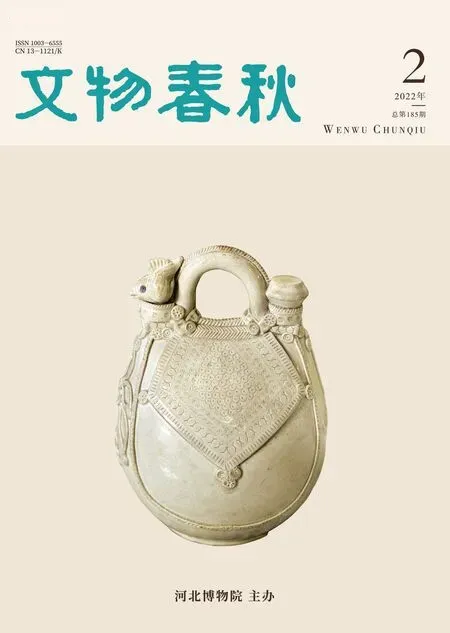談新發現的一類紀年燕陶文
楊 爍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安徽 合肥 230039)
燕陶文指戰國時期陶器上的燕系文字,其完成方式有鈐印與刻劃兩種,主要出土于河北易縣的燕下都遺址,河北任丘、北京、天津、遼寧、內蒙古以及齊國故地山東臨淄地區等也有少量出土,大部分的年代屬于戰國中晚期。燕陶文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涉及戰國時期燕國的職官制度、容量制度、歷史地理、手工業生產、姓名用字等諸多方面,值得對其進行整理與深入研究。


圖一 自怡齋藏燕陶文拓本
于先生文中推測該陶片上第一枚印記內容中“王”字之上殘存筆畫可能為燕系文字“都”字左半“邑”旁,正確可從。從此字出現位置與殘剩字形來看,確為“都”字無疑,“都”字之上應為燕國地名,惜殘缺。此印記的內容可總結為“燕地名+都+王勹(符)”。





近日,筆者又見到木葉堂所藏的一枚燕陶文(圖二)。據悉該陶片采集于燕下都遺址,比較之后可知其陶文內容與于文所錄相似,雖然內容均殘缺,但可以互補,因此可放在一起進行研究。與自怡齋所藏相比,木葉堂藏陶文無第一枚印記,第二枚印記“吳(虞)”字前則多出“□九年”三字,“九”字上部殘缺,另多出一枚“缶(陶)人某”倒鈐印記和一枚凹陷狀乳釘紋。關于燕陶文中出現的職官“陶人”,我們曾有專文討論,可參看。結合木葉堂與自怡齋所藏兩枚陶文的內容格式來看,這是一類由三枚印記組成且包含紀年信息的新見燕陶文。

圖二 木葉堂藏燕陶文拓本


圖三 北京地區出土燕陶文拓本
目前來看,這是一類新見的三璽連鈐紀年類燕陶文,其具體格式可總結為:
1.燕地名+都+王勹(符)
2.紀年+吳(虞)+人名
3.缶(陶)人+人名[此枚印記倒鈐]
這類陶文雖與過去習見的燕“三級監造”類紀年燕陶文內容格式有別,但陶銘旁均鈐有相似的乳釘紋,似乎是同一時期的產物。
最后,談一下此類燕陶文的年代問題。如果我們將北京地區出土的第三枚陶文紀年定為“廿八年”無誤的話,那么第一、二枚陶文中殘去的紀年極有可能就是“廿九年”,這也就合理地解釋了為何其格式與燕“三級監造”類紀年燕陶文不同。戰國中晚期燕王在位年代符合這一條件的只有燕昭王職與燕王喜兩位。《史記·燕召公世家》載:“(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屬燕,六歲。”此時燕國國富民強,達到極盛。而燕王喜“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于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史記·刺客列傳》:“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于遼東。”此時燕國即將亡國,燕都薊城與下都武陽城已處于極度動蕩之中。
綜合紀年所處的時代歷史背景、題銘格式的規范程度以及部分陶文的出土地(專指北京地區)來看,我們認為此類新見紀年燕陶文的年代最有可能是燕昭王時期,其與過去常見的所謂“三璽連鈐監造類陶文”的燕陶文屬于同一時期,只不過其紀年時間偏晚,因此題銘的格式內容發生了變化。
由于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此類紀年燕陶文僅有文中所舉三例,且內容均不可盡釋,因此對于其內容含義與所屬年代還有繼續討論與研究的必要。期待隨著相關出土文獻的增多,相關問題可以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