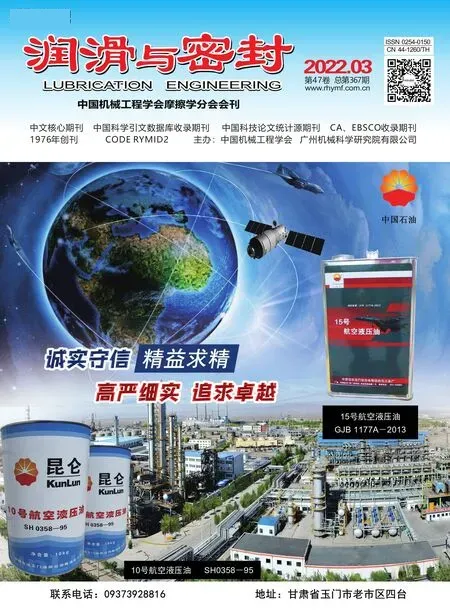高速重載圓柱齒輪彈流潤滑數值分析*
王秋菊 劉振剛 喬恒穩 邢 彬 牟佳信 侯巖錕 胡敦珂
(1.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 遼寧沈陽 110015;2.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航空發動機動力傳輸重點實驗室 遼寧沈陽110015;3.西北工業大學動力與能源學院 陜西西安 710072)
隨著航空發動機向著高轉速、高載荷、高可靠性方向的發展,齒輪系統工作條件日趨惡劣。為了減少齒輪系統因潤滑不佳導致的膠合失效等問題發生,需要對齒輪潤滑效果進行分析,全面掌握齒輪潤滑狀態。目前,彈流潤滑問題數值求解方法主要有逆解法、Newton-Raphson法(有限差分法)、復合直接迭代法和多重網格法[1]。20世紀50年代末,DOWSON和HIGGINSON[2]提出的逆解方法成功地應用于求解線接觸彈流潤滑問題,并提出了被廣泛應用的線接觸Dowson-Higginson膜厚公式。PARK和KIM[3]用有限差分法得到了有限長線接觸等溫彈流潤滑的完全數值解。艾曉嵐和俞海清[4]提出了復合直接迭代法,通過構造一種適用于求解線接觸非穩態問題的迭代格式,得到彈流問題完全數值解。
BRANDT和LUBRECHT[5]首次提出多重網格法計算彈性變形量,很快成為研究彈流問題的重要手段。袁祥等人[6]發現在中重載的情況下,次表面應力隨滑油黏度與卷吸速度增加的變化規律。尹昌磊等[7]求解了線接觸Newton流體熱彈流潤滑特性。GUO等[8]研究了穩態點接觸熱彈流潤滑問題,并獲得了經典的大凹陷形狀。ZHANG等[9]研究發現,隨著兩嚙合表面速度的降低,經典的大凹陷會演化為接觸區中央的小凹陷并最后消失。王明凱[10]發現轉速、潤滑油黏度的變化,均會影響油膜壓力及膜厚分布。劉明勇等[11]發現環境黏度高的潤滑油油膜厚度增加,第二壓力峰值也增大。方特和劉少軍[12]基于彈流理論與熱網絡法求解了輪齒穩態溫度分布。韓強等人[13]發現當速度線性變化時,膜厚基本上也以線性變化,加速度越大,膜厚的變化越快。綜上所述,目前的數值研究主要針對低速或者中低載荷的齒輪油膜計算[14-15],對于高速重載齒輪的油膜數值研究還有待進一步開展。
本文作者從線接觸理論著手,采用復合直接迭代法,對航空發動機傳動系統中高速、重載圓柱直齒輪潤滑狀態進行仿真分析,研究不同功率、不同轉速、不同溫度對齒輪嚙合區壓力、油膜厚度、油膜溫度的影響。數值計算結果可為航空發動機齒輪系統潤滑冷卻設計提供理論參考。
1 線接觸熱彈流潤滑數學模型建立
1.1 當量曲率半徑求解
圓柱直齒輪的嚙合屬于線接觸。對于兩直齒圓柱齒輪的嚙合,通過等效思想可以將齒輪接觸等效為一個圓柱與一個剛性平面的接觸問題,在此基礎上可以利用熱彈流潤滑理論計算齒輪油膜厚度。如圖1所示,齒輪在各自嚙合點處的曲率半徑R1和R2、綜合曲率半徑R分別為
R1=rb1tanα+s
(1)
R2=rb2tanα-s
(2)
(3)
式中:rb1、rb2表示齒輪的基圓半徑;α為壓力角;s為嚙合點距離節點的距離。
1.2 卷吸速度求解
根據當量曲率半徑計算得到2個齒面的絕對速度分別為u1和u2(見公式(4)、(5)),并將兩齒面速度的算術平均值定義為卷吸速度us,見公式(6):
(4)
(5)
式中:n1、n2為主動輪、從動輪的轉速。
(6)
1.3 單位長度載荷求解
齒輪受到的扭矩:
(7)
式中:M為扭矩(N·m);P為加載功率(kW);n為轉速(r/min)。
齒輪所受到的法向力為
(8)
式中:d1為齒輪分度圓直徑(mm);α為齒輪壓力角。
線接觸圓柱齒輪承受單位長度上載荷W(N/m)為
(9)
式中:B為齒輪齒寬(mm)。
2 線接觸熱彈流潤滑理論基本方程
(1)線接觸Reynolds方程如下:
(10)
線接觸邊界條件:
入口區p(x0)=0
出口區p(xe)=0
式中:ρ為油膜密度;h為油膜厚度;η是油膜黏度;p為油膜壓力;u為X方向的速度。
(2)載荷平衡方程如下:

(11)
式中:p(s)為載荷分布函數;w為外加單位線載荷。
(3)圓柱齒輪嚙合簡化為當量彈性圓柱體和剛性平面接觸時,任意點x處的油膜厚度方程如下:
(12)
式中:h0為中心膜厚;R為當量曲率半徑;v(x)為各點沿垂直方向的彈性位移,其表達式如下:
(13)
式中:s是x軸上的附加坐標,它表示任意線載荷p(s)ds與坐標原點的距離;s1和s2分別為載荷p(x)的起點和終點坐標;E′為當量彈性模量;c為待定常數。
(4)連續方程表達式如下:
(14)
式中:w為膜厚方向速度。
(5)油膜的能量方程如下:
(15)
式中:cp是滑油質量熱容;k是滑油導熱系數;β是熱膨脹系數;Φ是耗損函數。
(6)固體區域的能量方程如下:
(16)
對于彈流問題,關注的是固體與潤滑膜接觸表面的溫度而不是固體內部的溫度分布,假設傳熱是穩態。由于齒輪結構體的厚度遠大于油膜厚度,因此將其簡化為半無窮區域,繼而獲得該區域的解析解,從而可以直接建立齒輪與油膜的熱界面方程:
(17)
式中:Ui(i=1,2)表示兩界面在x方向上的速度;下標“s”表示齒輪的相關參數,“1”和“2”分別代表2個接觸面。
(7)潤滑油黏壓-黏溫關系經驗公式[16]如下:
η=η0exp{(lnη0+9.67)·
(18)
式中:η0為滑油初始黏度;T0為環境的熱力學溫度;T為油膜實際熱力學溫度。
(8)潤滑油密壓-密溫關系經驗公式[2]如下:
(19)
式中:ρ0為滑油初始密度。
3 線接觸熱彈流潤滑計算結果及分析
3.1 工況參數
以某型發動機附件機匣內圓柱齒輪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真實工況彈流潤滑效果分析。齒輪參數見表1,齒輪材料選用某齒輪鋼(室溫下導熱率為28.8 W/(m·K),比熱容為470 J/(kg·K),密度為7 980 kg/m3,等效彈性模量為212 GPa,潤滑油選用某航空潤滑油(室溫導熱率為0.161 W/(m·K),比熱容為1 847 J/(kg·K),密度為963 kg/m3,黏度為0.046 Pa·s),計算工況見表2。假設齒輪正常運轉時為富油潤滑,滑油為牛頓流體,文中對圓柱齒輪節點處進行全膜潤滑數值仿真分析。

表1 齒輪幾何參數

表2 計算工況參數
3.2 數值驗證
傳統的彈流潤滑研究中大多針對轉速較低(<10 m/s)的情況,對于高速(>50 m/s)重載情況相關研究還未有開展。文中采用與文獻[7]中圖2、圖3相同的的工況,將數值計算結果與文獻結果進行對比。從圖2中可以發現,壓力、膜厚、溫度的數值計算結果與文獻中結果趨勢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文中線接觸齒輪彈流潤滑的計算結果可信。
3.3 熱彈流潤滑數值計算結果分析
3.3.1 功率的影響分析
以轉速為19 909 r/min、滑油入口溫度為140 ℃的工況為研究對象,分析功率對齒輪彈流潤滑效果的影響。由于油膜在整個齒寬方向的分布趨勢均類似,選擇其中一個截面來分析油膜壓力、膜厚、溫升的變化情況。
從圖3中可以看出,不同功率條件下,油膜壓力、油膜厚度及溫升變化趨勢均相同。同一功率條件下,油膜溫升與油膜壓力變化趨勢相同,在整個嚙合過程中油膜壓力由小到大再減小,出現了第一壓力峰與第二壓力峰。第一壓力峰為嚙合處承受高載荷的區域,對應此時油膜出現了平面形狀;第二壓力峰的位置對應于油膜形狀開始凹陷之處,這種由溫差引起的黏度變化產生動壓的作用,國內學者稱之為溫度-黏度楔效應。當保持轉速不變,隨著功率的增加,齒輪所受的載荷逐漸增加,出現了最大壓力及溫升逐漸上升、最小膜厚下降的趨勢。同時,壓力二次峰會隨著功率的增加逐漸降低,這是由于逐漸升高的載荷抑制了油膜的頸縮導致動壓有所下降。
圖4展示了轉速一定時,油膜最大壓力及最小膜厚隨功率的變化。轉速為19 909 r/min時,隨著功率增加,則總載荷增加,而總載荷的增加導致了最大壓力的增加與最小膜厚的降低,膜厚的降低不超過0.02 μm。轉速為28 442 r/min時,功率的增加導致了最大壓力的上升,而最小膜厚則是先增加再降低,這是由于在當前工況下,極高的轉速要形成油膜需要一定的載荷,隨著載荷的上升油膜逐漸形成,從而出現了油膜厚度有所增加;隨后隨著載荷繼續增加,油膜的承載逐漸升高從而使得最小油膜厚度出現下降趨勢,但是最小膜厚的最大與最小值之差只有0.005 μm。對照轉速為19 009 r/min時膜厚的變化,可以說明高轉速情況下功率的變化對最小膜厚的影響較小。
圖5所示為轉速一定時,最大溫升隨功率增加的變化情況。可見,隨功率增加最大溫升增加;當轉速固定為19 909 r/min時,最大溫升從17.14 ℃增大到28.88 ℃;當轉速固定為28 442 r/min時,最大溫升從19.72 ℃增大到27.05 ℃。這是由于油膜的溫升主要依靠固體界面與油膜的摩擦,當速度保持不變時,隨著最大壓力的逐漸上升,最大溫度也會隨之上升。
結合上述計算結果可以發現,高轉速條件下出現了最小膜厚隨載荷變化不明顯的趨勢,而轉速較低時,載荷的大小也會對最小膜厚產生較大的影響。
3.3.2 轉速的影響分析
以功率為192.5 kW、滑油入口溫度為140 ℃的工況為研究對象,分析轉速對齒輪彈流潤滑效果的影響。從圖6中可看出,不同轉速條件下,油膜壓力、油膜厚度及溫升變化趨勢均相同。同一轉速條件下,油膜溫升與油膜壓力變化趨勢基本相同,油膜均出現了平面形狀及出口收縮凹陷現象。當功率固定時,轉速的增加使得載荷逐漸降低,載荷的降低使得壓力二次峰逐漸升高,這與當載荷極重時第二壓力峰會消失的研究結論[17]相一致。而保持功率不變,隨著轉速的增加,齒輪所承受的載荷會逐漸降低,因此出現了最大壓力及溫升下降、最小膜厚增加的情況。
圖7所示為功率一定時,接觸區最大壓力及最小膜厚隨轉速的變化情況。功率為134.75 kW時,隨著轉速的增加,載荷逐漸降低,最小膜厚從0.276 mm增大到0.390 mm,最大壓力先從1.004 GPa降低到0.949 GPa,而后隨著轉速增加又升高到0.952 GPa。最大壓力升高是由于隨著油膜厚度的逐漸增加,逐漸形成良好的彈流潤滑,油膜承載了更高的壓力使得接觸區油膜最大壓力有所上升。功率為192.5 kW時,隨著轉速的增加,載荷逐漸降低,最小膜厚從0.266 mm增大到0.386 mm,最大接觸壓力從1.142 GPa下降到1.021 GPa。
圖8展示了功率一定時,接觸區最大溫升隨轉速的變化情況。功率為134.75 kW時,隨著轉速的增加,最大溫升先從20.59 ℃降低到20.05 ℃,隨著轉速繼續增加,轉速升高的影響逐漸超過了載荷下降的影響,導致了最大溫升在最后階段又有所上升。功率為192.5 kW時,隨著轉速的增加,載荷有所下降,最大溫升從30.41 ℃下降到27.05 ℃。對比圖8(a)、(b)可看出,載荷對溫升的影響比轉速的影響更大。
當載荷較大時,齒輪線速度超過100 m/s時,隨著轉速的逐漸升高轉速對最大載荷的影響逐漸減小。而低速輕載狀態,隨著轉速的上升容易出現壓力二次峰成為最大壓力值的情況,速度對載荷的分布影響較大。
3.3.3 滑油入口溫度的影響分析
以功率為192.5 kW、轉速為28 443 r/min的工況為研究對象,研究了接觸區最大壓力、最小膜厚及最大溫升隨滑油入口溫度的變化規律。如圖9所示,溫度從125 ℃升高到145 ℃時,最大壓力從1.072 GPa降低到1.007 GPa,最小膜厚從0.460 μm降低到0.367 μm,同時最大溫升也從35.34 ℃降低到24.49 ℃。這是由于滑油溫度的升高使得滑油黏度下降,導致油膜的形成更加困難,則最小膜厚減小,油膜承載力減小。同時,黏度下降會使剪切應力減小,減少了摩擦與生熱,則最大溫升降低。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滑油溫度會使得滑油黏度較低,導致油膜厚度減小以及油膜承載能力的下降,從而增加發生干摩擦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綜合齒輪承載與潤滑情況來進行滑油溫度的確定。
4 結論
基于線接觸彈流潤滑理論,以航空發動機高速、重載圓柱齒輪為研究對象,通過數值計算分析了不同功率、不同轉速及不同溫度對齒輪潤滑效果的影響規律,在計算工況范圍內所得主要結論如下:
(1)隨著功率增加,載荷增加,接觸區最大壓力和最大溫升均增大,最小膜厚降低;高轉速情況下,功率變化對最小膜厚影響較小。
(2)隨著轉速的增加,載荷減小,接觸區最小膜厚增加,最大壓力和最大溫升受轉速和載荷的雙重影響呈現先減小再增大的趨勢。
(3)滑油入口溫度升高時的接觸區最大壓力、最小膜厚與最大溫升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入口溫度升高導致滑油黏度下降,改變了滑油物性。
(4)實際工作中要特別重視低速重載工況,此時載荷很大,容易出現干摩擦;合適的滑油入口溫度可以使齒輪接觸區承受較低的載荷并擁有較厚的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