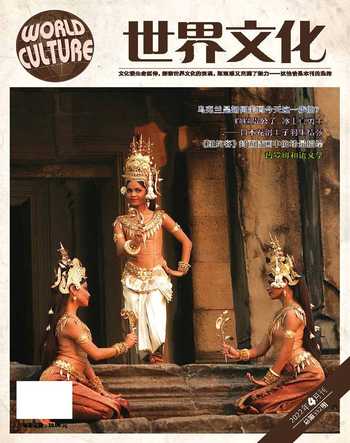與世界不期而遇“勇闖”弗萊(上)
世界很大,總得去看看。
哪個城市曾留下你的足跡?你又曾站在哪片天空下遙望故鄉的方向?
離開時,你舍棄了什么?歸來時,你帶回了什么?
你站在世界一隅,你仍然是你。你已不再是你——你看過的世界都成了你。
上期的馬哥、這期的老孟,全是地道的天津人。連續幾篇文章中滿紙彌漫的津式幽默畫風,不知道會不會讓“天津人平均是相聲演員”的評價板上釘釘,但說到遇事樂觀開朗,天津的哥哥姐姐那是認真的!
老孟作為經歷過唐山大地震的“70后”,在深知年近半百全家移民無異于一次 “人生大地震”的情況下,大大咧咧地率領著先生、兒子拎上四個行李箱,跑到加拿大一個非常“小眾”的地方定居去了。
移民于老孟,原本始于一次“烏龍”事件,但她干脆將計就計地換場生活,“瀟灑走一回”。落地后選房子、定學校、安家落戶的系列操作,彰顯了天津姐姐特有的麻利勁兒;一般人想想都要“頭大”的各種操持,讓英語不怎么靈光卻心大無比的老孟舉重若輕般定下了乾坤。她自己評價說,這是傻人有傻福,但她非凡的行動力卻令人佩服有加。
中年時期事業有成,仍有勇氣薅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從虛名利益中拽出來,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灑脫。但文中未談及此,而將講述的重點落在如何率領全家努力開啟一段新旅程的故事;看似絮叨的日常,藏著中國人“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坦蕩自信,引人會心微笑。老孟以親身經歷說明,接納、順應、努力實現,才是上不封頂的人生。
作為“70后”,我對當年的唐山大地震或多或少還有印象。我至今還記得震發當晚,姥爺抱著我搖搖晃晃地跑進地下室,我的頭撞到門框上,生疼;驚慌中看見從屋頂吊下來的電燈泡蕩來蕩去,大人的臉上驚魂未定……沒想到30多年后,我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二場“地震”——我率領全家遠赴加拿大定居去了。四個行李箱、兩個雙肩背包,外加兒子的一把吉他,是我們一家三口離開時的全部家當。但我著實不太確定,這一次我是否安全。
我們的定居地在加拿大東部,是毗鄰大西洋的紐布朗維克省(英文名簡稱NB省,我們更愛叫它“牛省”)的省會城市弗萊德里克頓,簡稱弗萊。轉機兩次后,我們抵達弗萊,入住當地有著兩百多年歷史的牛省大學(UNB)招待所。這所大學是北美四所最古老的公立大學之一,校園里紅磚綠樹;沒有圍墻,也沒有正式的大門。校園內幾乎看不到人,當時我還以為是暑假的緣故,沒想到后來發現,即便是開學季也一樣沒人,傳說中的地廣人稀是千真萬確的。
牛省是加拿大最初建國的四個省份之一,歷史悠久;也是唯一將英語和法語同時作為官方語言的省份,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使用法語交流。這里擁有北美大西洋海岸線上的第二大河流系統——圣約翰河,主要以林業、農業、漁業和采礦為主。面積大概有天津的7倍,人口卻只有70多萬,而省會弗萊市人口不到8萬,是個名副其實的小城市。

幾乎所有人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你為什么要出國定居?又為什么會選擇弗萊?這的確是個好問題,我也無數次自問。其實,出國定居緣于一次“烏龍事件”:一個好朋友申請加拿大移民時非拽著我和先生“陪申”,我們就抱著湊熱鬧好玩兒的心態答應了,沒想到竟然通過了。我覺得,那倒不如索性換一種“一家三口一條狗”的簡單生活!至于為什么選擇弗萊,那是我經過短暫考察后決定的。這個地方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滿足了我的諸多偏好:四季分明,夏天稍短,冬季多雪(本人怕熱,雪是最愛);自然環境優美,森林覆蓋率高,一條大河橫貫市區(會讓我想起故鄉的海河);生活節奏舒緩,民風淳樸,街上迎面走來的陌生人總會面帶微笑地招呼一聲:“嗨,今天天氣不錯哦!”
顧不上舟車勞頓,我們迫不及待地拿上地圖,去“首覽”一下城區風貌。法國文化遺產和歷史遺跡在弗萊隨處可見,因而這里素有“小渥太華”之稱。以橫貫市區的圣約翰河為界,北部原住民較多,至今保留著大片的原住民自然保護區。政府雖然陸續開發了一些新住宅區,社區配套也很齊全,但大部分區域仍顯得偏僻荒涼。河的南部依山勢走向而建,分為上城區和下城區,上城區以商業區為主,熱鬧繁華;下城區屬于老城區,很多建筑的歷史都超過百年,河邊沿岸一整條街的河景別墅看上去像是一座座古堡,幾乎全被用作民宿在經營著。下城區是文化教育中心,牛省大學就坐落在這里。除了劇院、美術館、圖書館,這里還有不同國家風味的特色餐館。正是夏天,我們就選了一家臨河的餐館坐下來,吃了落地加國的第一餐,算是為我們的異域新生活拉開了序幕。

初到弗萊定居的人,前期無外乎全是買房、買車、上學這“三板斧”。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畢竟有房才有家,有家才有雞飛狗跳——哦不,是母慈子孝的生活啊。我和先生首先開始上躥下跳地看房——上午搜地圖,下午實地考察。我們決定先租個公寓住下來,畢竟對于除草、鏟雪、收拾院子都一竅不通的我們來說,住公寓比較省心——有困難找物業嘛!直到此時,我都不太清楚自己這一腔“勇闖天涯”的豪情與自信從何而來。
兒子上學的問題似乎比較簡單,就近入學么,我們已經給兒子選好了一所位于下城區中心地段的初中學校。可是當我們帶著兒子興沖沖跑去“認領”新學校時,才發現教學樓滄桑陳舊,學校不僅沒有戶外運動場地(此地段寸土寸金),旁邊居然緊鄰墓地,簡直太不可思議了!雖然知道國外一些城市的中心地帶會有墓地,但是緊挨著孩子們每天讀書學習的校園,實在不符合咱們中國人的接受心理。和先生確認過眼神后,我們果斷決定重新擇校。
無巧不成書。晚飯后散步時我們看到一處紅墻碧頂的二層樓房,居然就是一所中學!學校足球場、沙地排球場、壘球場、網球場、籃球場一應俱全,“就是這里啦!”我和先生異口同聲地說。
接下來就是在學校附近選個住處。我們沿著學校前面的小路繼續走下去,迎面看見一棟七層公寓樓,紅白相間的外墻時尚又清爽,樓下綠草茵茵、花團錦簇,還有一個地下停車場——看來冬天也不必清理車上的積雪了。從學校到這里,直線距離不過300米,那叫一個便捷。
接下來,就是體現我超強執行力的時刻了!預約看房、簽合同、付定金、購買房屋保險、置辦家具和生活用品,我全部一手搞定!從飛機落地到拎包入住新家前后不到10天,我就憑著自己半瓶子都不滿的英語水平,居然順利安家了。
每天早上,我會和先生一起到公寓一樓的公共休息廳喝咖啡,用蹩腳的英語和新鄰居們聊聊天。這個公共休息廳是業主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區域,也是鄰里社交的重要形態。大家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些生活瑣事,新移民們會彼此分享初來乍到遇到的各種問題和經驗教訓。公寓的物業管理公司每逢萬圣節、感恩節、圣誕節等都會特意組織五花八門的主題活動,業主們的情誼就在各種信息交換與共度節日時光中連結在一起。
轉眼到了9月,我們去給兒子報名入學,手續簡單到校方只確認我們報英語班還是法語班,向我們要了在國內注射過疫苗的翻譯件,就批準我們“到時來上課吧”。如此這般,我們在弗萊的新生活就水到渠成地開始了。
兒子終于開學了!我們把兒子送到學校大門口,殷殷地給兒子拍照留念,祝賀他順利開啟初中生活。


可開學后沒幾天,兒子突然問我:“媽媽,咱們現在還能回中國嗎?”原來,兒子每天上課都是懵懵的,啥也聽不懂。這確實怪我,在國內時我從沒給兒子報過英語輔導班,只是在出國前兩個月才應急式地三口一起突擊了一下英語,能管多大用呢?不過,這也從某種角度刺激了兒子——爸媽已經指望不上,以后只能靠自己了!我安慰兒子:“別著急,初來乍到聽不懂很正常,兩三個月下來就沒問題了!”兒子很爭氣,兩個月后不僅聽懂了大部分英語授課內容,還在數學上嶄露頭角,在數學競賽中取得了很好的名次,此后又經過一番努力拼搏,居然當上了“學霸”,讓為娘我甚感欣慰。
順利安家、兒子的學習步入正軌后,我和先生迎來了又一道關卡——考當地的駕照。雖說弗萊面積不大,10分鐘就能開出城區,但它地處山區,路面起伏很大,尤其是一到冬季雪天,開車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考駕照這一關讓在國內號稱“老司機”的我和先生著實不敢大意。
于是我們從交規開始認真學起,然后依次準備筆試、路考。交規和中國的基本沒有什么原則上的差別,但筆試中有一道選擇題很有意思:如果在社區或非主路上,前面的車停下來和路上的熟人打招呼、聊天,你應該怎么做?選項有二: A.鳴笛催促; B.耐心等待。答案選B。多么令人費解啊,每個人的時間都很寶貴,怎么能耗費在等候上呢?可是待得久了我才發現,這根本不是問題:一來路上車輛很少,后面很少有車;二來加拿大人似乎從來沒什么急事,一貫不緊不慢的。時間一長我也入鄉隨俗,經常停下車和鄰車寒暄幾句后才道別離開。

筆試簡單,一考即過;路考則是一波三折,真的是經過三次考核才通過的,拿到駕照的我激動不已——這里的駕照含金量高啊!有了駕照等于有了身份證,很多事辦起來立馬方便很多:購買手機套餐、申請大型超市的會員、坐飛機、住酒店,全憑一本駕照就能搞定。人家能“仗劍走天涯”,我可憑“駕照游天下”。
開心之余,我和鄰居們商量舉辦一場potluck聚會以示慶祝。potluck是這里流行的一種聚會方式,參與的每個家庭各自帶上一兩個拿手菜,菜量根據自家到場人數而定,“下有保底、上不封頂”。彼時已經進入12月,是當地的圣誕季,很多業主都開始呼朋喚友地搞起了各種慶祝活動,一樓的咖啡廳頗受歡迎,每天的客人絡繹不絕。到了potluck那天,大家帶著各自的拿手好菜聚在一起,邊吃邊聊……不過大家似乎全然忘記了慶祝我拿到駕照這個聚會緣起,都沉浸在喜迎圣誕和新年的無比喜悅之中。年近半百,在異國他鄉還能遇見這些聊得來的朋友,是何等幸運!真希望時間就此靜止,永遠定格在這溫暖而快樂的相聚時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