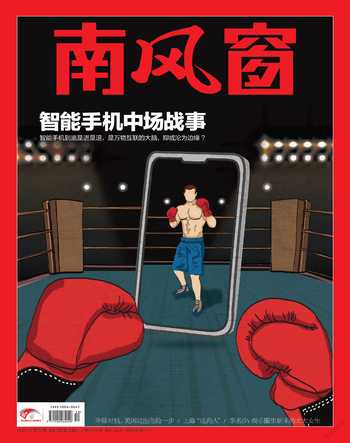種地這件大事
閻海軍
去年冬天,我和同事下沉居民小區做志愿者,一位老者飯后摸進帳篷,問:“疫情啥時候結束?”我說:“西安最近好多了,你看新聞,應該控制住了。”老者沉思一陣,又問:“農民不種地,這個瘟疫啥時候結束?”我啞口無言。
今年春天,我看到很多地方新聞都在報道復種撂荒地,突然想到年前那位老者的發問,他居住在城市里依然操心種地的事,何其憂呀!
清明,疫情原因不能回家祭祖。生活在城市的眾兄弟用微信向留守村莊的大哥問詢有關祭祖的情況。意外得知,其時政府正在免費提供種子號召農民種春小麥。土地撂荒的人不在村里,還在種地的農民大覺為難:一來春小麥種植時節已經有點晚,二來一春無雨,種了也很難出苗。
我的父老鄉親中,老一輩大都挨過餓,種糧從來都很積極,用不著別人催促。免除農業稅近20年,農民種地很自由,種多種少,種與不種都是自己說了算。如今他們突然又被催促種地,多少有一些意外。
1990年代初期,大哥成家立業。大哥分家時分到的土地并不多,那時候他偶爾出去打工,但他實現人生價值的重心依然在土地。那年月,面對農業稅和“三提五統”,每一個農民的負擔在新聞聯播里經常都能聽到。突然有一天,村里有人在自家地塊附近的邊溝坡地開荒,這一舉動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全村和大哥年紀相仿的70后紛紛效仿,過去的荒郊野嶺,迅速都變成了耕地。還有膽大妄為的人,毀掉了部分山林變作耕地。
那時候,奶奶已是80多歲高齡,她一邊看著村里的后生開荒,一邊感嘆說:“挖上梁畔,荒了門洞,你們這些壞蛋都是瞎折騰,總有一天家門口的地都會種不過來。”
1994年,奶奶去世。1998年,中國南方爆發大洪水。接著,舉國退耕還林。我們村被開墾的山林地,又種上了耐旱的樹木。再后來,中國城市化洶涌澎湃,全村的80后、90后,都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大家想盡一切辦法進了城。留在村里種田的80后只有一個,90后操持過農活的為零。70后成了村里最后的種田人。國家因勢利導,出臺了種糧補貼政策。但這筆資金灑向廣大鄉村,形同胡椒面,并未能阻止種田人的減少。因為城里打工的收入遠遠高于種糧賣錢。農民進城,農田撂荒。目下中國,偏遠鄉村大抵如此。
奶奶不是神仙,也不是先哲,但她1990年代初期有關“挖上梁畔,荒了門洞”的告誡,后來真的應驗了。奶奶一生經歷過兩次世人皆知的饑荒,她對土地的依賴無須多言,但她晚年看到的開荒景象,要將村莊原本稀薄的野生植被全部消滅的舉動,讓她意識到了危機。村莊,得有人家、得有田地,還得有荒坡溝臺、野花雜樹。
城市化的年月,出門打工的人普遍比種田的人生活富足。大哥一直留守村莊種地,還擔任了一個階段的村委會主任。他一直說:“任何時候,人要吃糧食;社會咋變,少不了糧食,糧食是根本。”
除了土地撂荒現象,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現象也十分嚴重。
曾幾何時,為了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很多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加威逼利誘,讓農民發展經濟產業。這些舉措,是當年促進農民增收萬不得已的法子。但民以食為天,真正懂國情的人,真正生產糧食的人,都知道,錢重要,糧食更重要。種糧這個事,任何時候強調,都是必要的。除了觀念上的重視,鼓勵農民種糧還要在尊重勞動價值論、順應經濟規律、推動商品等價交換方面,探索制度的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