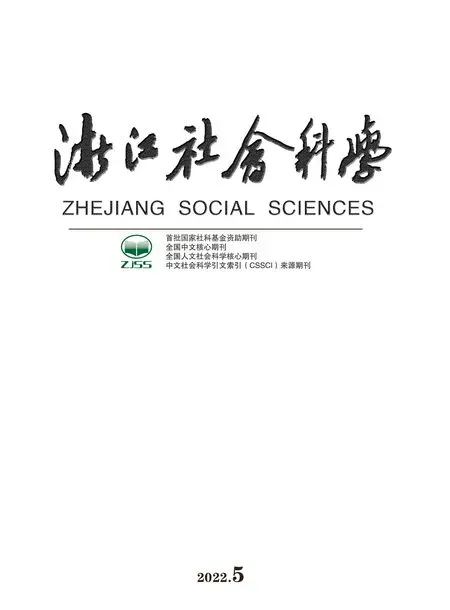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環境治理的多層次分析
□ 吳結兵 錢倩嚴慧
內容提要 推動公民參與共建共治共享,是降低公共服務成本、提高社會治理效能的重要方面,因此,探究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對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本文構建了一個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多層分析框架,基于CGSS2010 和CGSS2013 數據,采用HLM 多層線性回歸模型檢驗了地區層面因素和個體層面因素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公民共同生產行為同時受益于地區和個體兩個層面的貢獻:在地區層面,地方政府的環境宣傳教育對公民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產生了直接的正向影響;在個體層面,個體的共同生產能力與共同生產心理都正向作用于共同生產行為,相較于能力因素,個體的心理因素對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更強。研究結果在理論上擴充了共同生產激勵因素的解釋框架,在實踐上有助于政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激勵政策,推進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創新。
一、問題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政府為主導、 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環境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激勵公民參與共建共治共享是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尤其在環境治理領域,沒有公民的配合和參與,政府和市場都難以完成環境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①。作為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 減少由于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造成資源損失的互補性選擇,推動公民參與環境共同生產是降低公共服務成本、 提高環境治理效能的重要方面。
共同生產理論是目前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基石之一(Osborne et al.,2016)。共同生產強調公共部門和公民共同參與公共服務 (Nabatchi et al.,2017)。一方面,公民在公共服務中的共同生產行為可以促進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益;另一方面,通過發動公民參與共同生產,公共服務將不再依賴政府的高昂財政投入,卻也能夠獲得同等甚至更高的服務成效(Brudney,1984;Bovaird and Loeffler,2012)。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也已經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廣泛關注,生態環境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2018年聯合發布的《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中列明了公民的十條環境行為規范,強調公民應提高生態環境意識、積極踐行環保行為,共建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
盡管以共同生產的方式提供環境公共產品已經成為了政府和學者的普遍共識,但是在現實表現中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實踐并不理想。《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19年)》和《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20年)》都顯示,公民在環境行為的踐行上普遍表現出“高認知度、低踐行度”的現象。然而,相比環境治理中的公民參與,政府部門、 學者似乎更關注企業的環境行為以及政府與企業在環境治理中的多重博弈均衡(參見唐國平等,2013;王斌,2013;金剛、沈坤榮,2018),關于如何激勵公民從事環保行為這一重要議題缺乏必要的理論關注。并且,長期以來我國環境治理體系呈現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模式,在促進公民個人環保行為方面的方式方法亟待突破創新。為此,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公民參與環境的共同生產顯得尤為必要。通常關于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價值規范被假設是理所當然的(Ianniello et al.,2019),而事實上公民并非會自動加入共同生產的行列,在不回避這個隱含假設的情況下,本文從個體層面和地區層面探討公民參與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迄今為止,有關共同生產影響因素的大多數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個體層面因素上(Alford and Yates,2016; Bovaird et al.,2015),如公民的內在價值觀、團隊激勵、自我效能感等(Alford,2002;2009;Alonso et al.,2019)。此外,諸如教育、性別、年齡和居住地等社會人口屬性在相關文獻中也通常被認為是公民從事共同生產行為的潛在因素 (Alford and Yates,2016;Bovaird et al.,2016)。這些研究促進了我們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激勵因素和潛在障礙的理解,但是需要結合更廣泛的研究框架來實證探討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有貢獻的其他變量 (Bovaird and Loeffler,2012)。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服務共同生產理論指出了促進或阻礙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地區層面因素的重要性(Voorberg et al.,2015)。盡管研究關于公民參與公共服務共同生產的學者與日俱增,但很少有研究系統地考察個人和地區因素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Alonso etal.,2019)。對此,本文構建了一個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多層分析框架,探討地區和個體兩個層面因素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力圖從多層次的視角更加全面地分析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
(一)影響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個體層面因素
在有關公民參與的議題中,其參與的基本要素是公民有時間和有能力去進行相關投入(Manes-Rossi et al.,2021),不少學者也曾提出公民對公共服務生產的投入取決于他們在擁有共同生產資源方面的能力(Alford,2002;Whitaker,1980;Percy,1984)。熱衷于為共同生產做出貢獻的公民可能會由于任務太難或缺乏必要的能力而難以行動,這意味著公民需要具備一定的共同生產能力,例如與共同生產相關的知識、金錢、時間、技能、材料、社會資本等。即使在最簡單的任務中,共同生產也需要利用客戶的“隱性知識”,與組織進行互動。例如目睹交通事故的公民可以提供急救和引導救護車到現場,這就需要他們具備一定的急救技能以及如何報告事故的知識,如果公民有一定的工具或設施,他們的投入對共同生產的貢獻往往會增加,如呼叫救護車需要使用電話和電話網絡。Sundeen(1988)論證了受教育程度對共同生產的重要性,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公民會更了解社區需求,也更能表達自己的需求。公民的共同生產可能還取決于他們有多少時間可以利用(Marschall,2004;Percy,1984),人們不得不睡覺、工作、照顧孩子、做家務等等,這給公民可參與共同生產的時間造成了限制。同理,身體健康狀況也是公民共同生產能力的體現,它是其他生活能力、學習能力、工作能力的前提與基礎。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領域,我們有理由相信個體在健康的基礎上才會從事更多的利他行為。因此,我們認為個體健康狀況可能是公民兌現共同生產承諾的因素之一。以往的研究也發現,個體環境知識會對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Hadler,2011),環境素養理論認為環境知識是環境素養的最基礎層次,個體的環境行為的發生是個體具備一定的環境知識、環境意識之后進行的相關行動,已有研究證實了環境知識與環境行為存在正相關關系(施生旭、甘彩云,2017;王琰,2015)。基于以上研究和經驗證據,我們認為以下個體能力與個體的共同生產行為存在積極效應:
H1a:個體的身體健康狀況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H1b:個體的環境知識狀況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具備共同生產能力的公民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加入共同生產的行列,例如“環境知識并不一定能轉化為環境行為”(曾昭鵬,2004),既有研究指出公民參與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并非所有人都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并希望參與(Pateman,2012),我們猜測公民是否致力于共同生產還有很大程度取決于公民是否愿意做出有助于實現公共價值的努力。采取積極的行動往往需要自發的行為,這些行為依賴于公民的貢獻意愿。既有的共同生產文獻已經關注到了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動機和心理(Alford,2009;Van Eijk and Steen,2016),這些心理可能受到不同激勵因素的驅動。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公民之所以參與共同生產,在于他們可以從中獲得物質利益,并且只有在收益超出成本的時候才會參與共同生產。而Alford(2009)認為這些利益是多元化的,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激勵因素可以是物質型的(如用以換取社區服務的抵用券)也可以是非物質型的(成為鄰里守望的一員從而獲得更安全的鄰里環境)。如果是涉及簡單任務的共同生產,物質獎勵可能更合適,而涉及復雜問題或持續性共同生產時,非物質的內在獎勵可能是更強有力的激勵因素。Alford(2002;2009)還提出了三種非物質激勵:有效行動增加的自信心,為公共事業做出貢獻的愿望,關于社會問題的規范性信念或價值觀。
不難看出,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心理因素可能是復雜多變的,這類激勵因素的重要程度會根據不同的公共服務場景以及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感知程度而有所不同。并且,這些因素并非單獨發揮作用,不同的共同生產情景可能有不同的機制組合發生作用。在環境領域,哪些心理類型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公民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呢? 既有研究給出了一些建議。公民環境保護的行動是否發生取決于很多因素,但必要的環境關心水平是行動發生的前提,公民對環境的關注程度可以看作一種基于對環境狀況的心理狀態,個體越關心環境問題,越對良好的環境這一公共產品有更高的期待,從而更愿意從事環保行為(鄭思齊等,2013)。而Bandura 指出 “除非人們相信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產生預期的效果并阻止不想要的效果,否則他們幾乎沒有采取行動的動力”。在一些共同生產的定量研究中,自我效能因素也成為個人和集體共同生產的關鍵驅動因素(Loeffler et al.,2008;2016;Parrado et al.,2013;Bovaird et al.,2016)。公民的自我效能感(Bandura,1997)即公民認為自己可以通過有意義的方式影響公共服務并有所作為的程度。自我效能感越強的公民越容易對公共利益產生共鳴從而激發其參與公共服務的內在動機,先前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關于歐洲五個國家在公共安全、 環境和健康問題上的居民調查數據支持了具有更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更有可能共同生產(Parrado et al.,2013),Alford 和Yates(2016)也預期公民的自我效能感是促進共同生產的一個普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和經驗證據,我們假設以下個體的共同生產心理與個體的共同生產行為存在積極效應,具體假設為:
H2a:個體的環境關注度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H2b: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H2c: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意愿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二)影響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地區層面因素
公共部門的制度設計會影響公民參與共同生產(Andfossen,2020),這個因素主要涉及制度允許公民參與生產過程的程度,可以看作是在給定背景下塑造“游戲規則”。例如,體制安排可能限制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公民投入,而政府倡議可能會增加公民的共同生產。公共組織是否在共同生產方面具有兼容性也被認為會影響公民的共同生產,這里的兼容性是指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激勵公民參與并創造適合互惠和交流的條件,以及是否存在與公民溝通的基礎設施(Voorberg et al.,2015)。
在環境領域,Guagnano 等學者(1997)提出的環境行為預測的ABC 理論認為環境行為(B)是個人的環境態度變量(A)和外部條件(C)相互作用的結果。政府環境行為、環境污染狀況等作為外部條件或對環境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關于環境質量與公民環境行為,污染驅動假說認為公民感受到環境遭受污染會促使他們從事環境保護行為(王琰,2015),這意味著環境質量越差,公民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可能性越高。再看其他外部條件(C),政府環境行為不僅包括為規范市場主體環境行為提供制度安排、 為環境治理及保護事業進行財政支出等硬性措施,還包含對公民進行廣泛的環境保護宣傳、 向公民普及必要的環境知識及環境行為規范等軟性措施。既有研究指出了公民的環境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投入的影響,但對于這些影響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仍存有爭議。例如,有研究發現當地政府治理環境投入越多公民實施的環境友好行為反而越少(高孟菲、鄭晶,2019),我們認為,政府資源直接介入環境并向該領域投入能夠向公民表明對環境保護的力度和決定,同時也會為公民起到示范和帶頭作用,從而激勵公民參與到環境的共同生產活動中。此外,政府采取多種形式的軟性措施,開展環境知識及環境行為規范培訓,組織策劃環境保護宣傳活動,動員群眾積極投身于環境保護事業,理論上有利于公民的環境意識向環境行為轉化,促成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發生。
基于以上研究和經驗證據,我們把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投入、 當地環境質量以及政府對公民在環境保護上組織的宣傳教育納入到地區層面的影響因素進行考量。并且,由于共同生產發揮效用需要確保公共服務組織和公民都能夠做出有效的貢獻,我們猜測以上因素并非單獨發生作用而是與個體層次的影響因素混合發生作用。對此,我們提出地區層面因素對個體共同生產行為存在以下效應:
H3:政府環境治理投入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H4:地區環境質量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負相關關系。
H5:政府對公民的環保宣傳教育與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正相關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區域層面數據來自2005—2013年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資料匯編》、《中國民政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各省的環境治理相關指標。個體層面數據則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持的“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和“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該調查采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完成。CGSS2010 的最終樣本量為11783 個,剔除因變量應答缺失的個體樣本,進入本研究的有效樣本量為來自31 個省級行政區的3615 個樣本。CGSS2013 的最終有效樣本量為11438 個,剔除因變量應答缺失的個體樣本,進入本研究的有效樣本量為來自28 個省級行政區(CGSS2013 本身不含新疆、海南、西藏的數據)的11328 個樣本。
(二)變量測量及操作化
1.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為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CB),在CGSS2010 數據中我們使用與之相關的6 個問題來衡量環境治理中個體的共同生產行為:“您經常會特意將玻璃、鋁罐、塑料或報紙等進行分類以方便回收嗎?”、“您經常會特意購買沒有施用過化肥和農藥的水果和蔬菜嗎?”、“您經常會特意為了環境保護而減少開車嗎?”、“您經常會特意為了保護環境而減少居家的油、氣、電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嗎?”、“您經常會特意為了環境保護而節約用水或對水進行再利用嗎?”、“您經常會特意為了環境保護而不去購買某些產品嗎? ”,這些問項與大部分關于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研究測量相一致(Loeffler et al.,2008;Alford and Yates,2016;Alonso et al.,2019)。經過數據清洗和反向賦值(總是=3;經常=2;有時=1;從不、缺失值=0),題項數據通過了KMO 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可靠性檢驗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4,具有較好的同質性,適宜進行量表累加,于是我們對6 個題項的作答情況根據賦值進行加總來衡量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數值越大表示個體在過去從事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越多。
對于CGSS2013 數據,我們同樣使用問卷中與之相關的9 個問題來衡量環境治理中個體的共同生產行為:“我們想了解一下,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從事過下列活動或行為?1:垃圾分類投放;2:與自己的親戚朋友討論環保問題;3:采購日常用品時自己帶購物籃或購物袋; 4:對塑料包裝袋進行重復利用;5:為環境保護捐款;6:積極參加政府和單位組織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 7:積極參加民間環保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 8:自費養護樹林或綠地;9:積極參加要求解決環境問題的投訴、上訴”。題項數據通過了KMO 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可靠性檢驗中9 個題項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5,與CGSS2010 數據處理方式一樣,我們對9個題項進行加總來表征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
2.自變量
(1)地區層面變量(level 2)
①政府的環境治理支出。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生態環境負總責,環境污染治理支出反映了政府用于環境保護管理事務、環境監測與監察、污染防治、污染減排、監管調查等方面的支出,其變化幅度能更好地體現政府環境治理行為的決心和力度(徐順青等,2018)。鑒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到政府財政對當地環境保護的支持,我們用2010年、2013年政府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的GDP 占比來分別衡量2010、2013年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投入情況。②環境質量指數。該指標隸屬于我國科技部建立的科技進步統計檢測級綜合評價制度的范疇,用來表征自然環境污染危害的情況以及自然環境質量的優劣程度,我們用2010年、2013年各省級行政區平均環境質量指數作為該地區環境狀況的代理變量。③政府的環境宣傳教育情況。為加強對公民的生態環境保護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生態環境意識,地方政府每年都會組織形式多樣的環境宣傳活動,我們用2010年政府開展的社會環境宣傳教育活動次數、2013年政府開展的社會環境宣傳教育活動人數來作為該地區地方政府環境宣傳教育的代理變量。
(2)個體層面變量(level 1)
①共同生產能力。a.身體健康狀況(health):采用CGSS2010、CGSS2013 中題項為“您覺得您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是? ”來進行衡量。b.環境知識(EK):CGSS2010 和CGSS2013 的問卷中都設計了10 個判斷題來對公民的環境知識掌握情況進行測量,題項為:“1:汽車尾氣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威脅;2: 大氣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會成為氣候變暖的因素;3: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會造成水污染;4: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會成為破壞大氣臭氧層的因素;5:酸雨的產生與燒煤沒有關系;6:物種之間相互依存,一個物種的消失會產生連鎖反應;7:空氣質量報告中,三級空氣質量意味著比一級空氣質量好;8:單一品種的樹林更容易導致病蟲害;9:水體污染報告中,V 類水質意味著要比I 類水質好;10:大氣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會成為氣候變暖的因素”。通過對正確答案賦值后的數據進行可靠性檢驗,得到CGSS2010 和CGSS2013 題項數據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795 和0.819,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于是我們對受訪者回答正確的次數進行加總來衡量個體的環境知識掌握情況。
②共同生產心理。a.個體環境關注度(EC):在CGSS2010 中我們用“總體上說,您對環境問題有多關注?”來衡量,在CGSS2013 中我們用“最近一年里是否主動關注廣播、 電視和報刊中報道的環境問題和環保信息”來衡量。b.自我效能感:采用CGSS2010 中題項為“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為環境保護做什么”來衡量,根據題項涵義,我們對答項進行了反向賦值。c.環境共同生產意愿: 采用CGSS2010 中“為了保護環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繳納更高的稅/降低生活水平? ”來衡量,3 個題項的數據通過了KMO 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37,量表題項具有較好的同質性,適宜進行量表累加,我們對3 個題項的作答情況進行加總來衡量個體環境共同生產的意愿,數值越大表示個體從事的環境共同生產的意愿越強。
(3)控制變量
此外,公民的社會人口屬性也會影響公民是否參與共同生產。本文引入性別(女=0;男=1)、年齡、政治面貌(非共產黨員=0;共產黨員=1)、受教育程度、居住類型(農村=0;城市=1)做為該研究的控制變量。

表1 GSS2010 來源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Pearson 相關系數

表2 CGSS2013 來源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Pearson 相關系數?
四、實證分析
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公民是具有獨立特征的個體,更是嵌入到具體制度環境中的個體,加之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的架構下所抽取的個體樣本,這就使得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受到區域層面特征的影響,表現出巢狀、 內嵌的樣本特征。在該情況下使用傳統OLS分析將不同層級變量置于單一的多元回歸中,將會違背變量相互獨立的假設 (Randenbush and Bryk,2002)。若將高層次的分析結果推演至較低層次的現象,易高估了低層次的結論,產生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反之,若將個體層次的分析結果推演至地區層次,即會產生原子謬誤(Atomistic Fallacy),現有統計模型中,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ling)可以滿足我們的分析需求,為了同時考察個體層面和地區層面變量對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我們使用多層線性回歸模型(HLM)依次檢驗零模型、隨機系數回歸模型、完整模型的實證結果。
零模型(Null Model)有助于我們捕捉不同省份之間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是否有顯著差異或非獨立的情況。這一模型可以允許我們計算出組內相關系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以下簡稱ICC(1),該系數越高表明組間差異更能解釋總方差)。我們設置零模型如式(1-1)、(1-2)所述:

零模型分析結果顯示,CGSS2010 和CGSS2013中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ICC(1)值分別為0.142和0.163,呈高度組內相關②,組與組的數據之間不具有獨立性特征。ICC(2)值均大于0.9,信度較高,綜合以上兩個條件,我們認為2010年和2013年的數據均具備跨層次分析的統計合理性和必要性。隨即我們采用僅納入個體層面變量的隨機系數回歸模型(公式略),來檢驗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個體層面因素的影響,而后納入個體層面和地區層面變量,設置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完整模型來同時檢驗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個體層面和地區層面因素的影響,完整模型如式(2-1)……(2-11)所述。

上述公式中,Yij、healthij、EKij、ECij、SEij、CIij、sexij、ageij、eduij、residentij分別為i 地區j 個體的公民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健康狀況、環境知識、環境關注度、自我效能感、環境共同生產意愿、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類型;EPIij、EQIij、GPEij分別為該地區的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投入、環境質量指數、政府環境宣傳教育情況;βij和γij為待估參數項,rij和μij為隨機誤差項,多層線性回歸模型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模型采用Robust 標準誤差來處理殘差的異方差性。

表3 零模型分析結果
隨機系數回歸模型和完整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CGSS2010 還是CGSS2013 的數據中,個體層面的共同生產能力和共同生產心理均對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地區層面變量中政府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對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余地區層面變量不顯著。

表4 多層線性回歸結果
具體來看,在個體的共同生產能力方面,健康狀況(γ10(2010)=0.15,p<0.05;γ10(2013)=0.09,p<0.01)、環境知識(γ20(2010)=0.25,p<0.001;γ20(2013)=0.13,p<0.001) 對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顯著為正,H1a、H1b 假設在CGSS2010 和CGSS2013 數據中皆得到支持。在環境共同生產的心理方面,環境關心(γ30(2010)=0.66,p<0.001;γ30(2013)=1.56,p<0.001)、自我效能感(γ40(2010)=0.29,p<0.001)、環境共同生產意愿(γ50(2010)=0.19,p<0.001)對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也都顯著為正,H2a 假設在CGSS2010 和CGSS2013 數 據中皆得到支持,H2b、H2c 假 設在CGSS2010 數據中得到支持。同時,我們意外的發現,在個體層面共同生產心理的影響效應普遍大于共同生產能力的影響效應。
在地區層面,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環境質量對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H3、H4 假設未得到支持。政府的環境宣傳教育活 動(γ01(2010)=0.22,p<0.05;γ01(2013)=0.16,p<0.1)對個體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回歸系數顯著為正,H5 假設在CGSS2010 和CGSS2013 數據中皆得到支持。
數據分析還表明,在社會人口特征中個體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呈現明顯的人群差異,具體體現在女性、年長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參與環境共同生產的傾向越高。在這些因素中,居住類型似乎是影響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特別強的決定因素。與前人的研究一致(Bovaird et al.,2015),居住類型被認為是影響個體共同生產行為的統計顯著因素,即與農村相比,城市居住者更可能在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
五、結論與討論
環境的公共產品屬性及其外部性特征導致市場在提供環境公共服務時面臨市場失靈的風險,政府作為公共利益受托人對環境保護有著天然職責,而傳統單一行政中心的公共服務提供模式已不能滿足公民的有效需求,加之政府在環境保護與治理上面臨著持續的財政壓力,促使我們需要以更經濟的方式來保護和治理環境,公民參與環境的共同生產不失為財政約束條件下提高治理效能的互補性選擇。公眾參與已經成為我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環境保護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有賴于公民的積極參與,探究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更顯必要。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地區因素和個體因素的多層分析框架,運用HLM 模型驗證了一些影響公民從事共同生產行為的因素,主要結論包括:
首先,本文嘗試將共同生產能力和共同生產心理的分析框架應用于個體層面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研究,研究發現公民從事共同生產行為是個體的共同生產能力與共同生產心理同時作用的結果。正如Alford(2009)在理論上指出的那樣,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兩個關鍵先決條件是有能力和有意愿為改善公共服務做出貢獻,我們的實證研究表明個體的能力和心理與公民的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緊密相關,能力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會對共同生產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從共同生產的能力方面看,健康狀況良好、環境知識掌握情況好的公民更傾向于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我們發現是否具備共同生產的能力是影響公民共同生產行為重要因素的同時,個人的共同生產心理也對公民的共同生產行為產生著正向影響,實證中主要體現在對環境關注度高、 自我效能感高以及共同生產意愿強的公民更傾向于踐行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由此可以確定的是,在一項公民參與的共同生產活動中,公民具備一定的能力和心理成為發生共同生產行為的基本要素。
其次,相較于能力因素,個體的心理因素對共同生產行為的影響更強。能力通常被視為個體一種穩定的特性,相較于心理短期內不易改變,而個體的心理則相對帶有不確定性。然而,通過以上實證結果我們發現,無論是CGSS2010 還是CGSS2013的數據,心理因素的影響系數均大于能力因素的影響系數,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相較于個體能力的大小,公民是否從事共同生產行為似乎與個體心理有著更強的關聯。這一研究結果為強調內在激勵的共同生產理論提供了支持,與個人態度相關的內在激勵可能對人們的共同生產行為更有價值。鑒于此,未來有必要關注和理解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心理或行為方法(Voorberg et al.,2018),從動機激勵的角度探討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有效策略。
最后,除了檢驗可能影響共同生產行為的個體層面因素外,本文還試圖檢驗地區層面因素是否可以進一步解釋公民參與環境共同生產活動的可能性。通過把多個地區層面變量納入多層次模型,我們發現政府對公民環境宣傳教育的投入有助于解釋公民參與環境的共建共治共享,政府環境宣傳教育活動越多的地區人們從事環境共同生產行為的可能性更大,這也完善了既有文獻對影響共同生產行為的地區層面變量的解釋。盡管許多共同生產文獻都強調了地區層面因素的重要性(Voorberg et al.,2015;Alonso et al.,2019),但很少有研究系統地評價地區層面因素與公民共同生產活動之間的聯系。我們的分析表明,公民共同生產行為同時受到個體和地區兩個層面因素的影響。
這些發現也為我國政策制定者帶來一些啟示。環境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的實現路徑離不開對公民參與能力的培育,同時,外部環境政策只有轉化為行動者的自覺意識,才有可能切實體現在行動的改變上。鑒于政府環境教育對公民共同生產行為的積極影響,政府應更加重視對公民生態環境理念、環境友好行為的培育,加大全社會環境保護的政策導向。更重要的是,讓有共同生產能力卻對政策議題不了解或不感興趣的人參與共同生產、 或是讓了解和關心政策議題卻參與能力不足的人參與共同生產都會浪費寶貴的個人資源和公共資源(Loeffler,2021)。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在共同生產中政府可以通過向公民提供相關資源,或減少對公民參與共同生產的能力限制,或頒布激勵公民共同生產的政策舉措來增加公民共同生產的潛力,如在組織內部建立邀請公民參與的組織結構和程序 (Bovaird and Loeffler,2012;Sicil ia et al.,2016),建立和完善與公民溝通的相關基礎設施(Thomas,2013;Meijer and Torenvlied,2014),以及更好的溝通也會增強公眾參與共同生產的動力(Lember et al.,2019),這為政府制定激勵共同生產的政策提供了啟示,政府在激勵公民的共同生產行為時需要同時考慮個體能力因素和心理因素,在提高公民環境保護知識、增強個體環境保護共同生產能力的基礎之上,更要注重與公民的溝通對話,營造環境保護共同生產氛圍,激發公民關注環境治理,提升公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效能感和意愿。
注釋:
①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2010)顯示,生活污染源約占污染源總數的1/4。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2020)顯示,生活污染源約占污染源總數的1/5。從水污染排放情況來看,生活源污染排放遠遠高于工業源污染排放量。
②ICC(1)的值由τ00÷(σ2+τ00)計計算得到。根據Randenbush 和Bryk 對ICC(1)數值的劃分:ICC(1)<0.059 為低度組內相關;0.059<ICC(1)<0.138 為中度組內相關;ICC(1)>0.138 為高度組內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