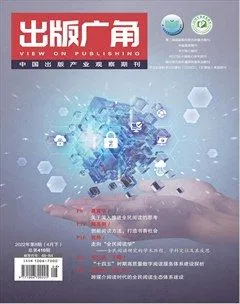如何提高世界出版能力
何抒揚?何明星
【摘要】筆者通過梳理德古意特和施普林格兩家德國出版社的國際化發展史發現,德國出版所發揮的專業化組織作用非常關鍵,對西方知識與文化的全球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涉及世界出版能力建設。世界出版能力指的是跨語種、跨文化的出版內容,跨國家、跨區域的出版市場,跨國籍、世界化的出版隊伍。世界出版能力建設是中國出版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可敬、可愛、可信的中國形象的關鍵。
【關? 鍵? 詞】知識生產;國際傳播;世界出版能力
【作者單位】何抒揚,北京語言大學;何明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
【中圖分類號】G239.3【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8.009
毫無疑問,出版作為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承的行業,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國際傳播起到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那么,西方跨國出版機構在西方知識與文化逐步占據當今世界主流文化地位的歷史進程中,到底起到哪些作用?這些作用是如何發揮的?學術界對這方面的探討多是一些概括性的研究,如對德國出版業的宏觀研究有張克非的《集團化、網絡化、國際化——德國出版業發展的重要趨勢》[1],研究美國出版業的有陳明瑤的《美國圖書出版業的發展軌跡》[2]。近些年出現了一些相關成果,如華中師范大學邢來順教授的《近代德國有組織的知識生產與文化科技發展》[3],總結了德國近代知識生產從宮廷到大學再到專業化平臺的三個發展階段,但是忽略了出版機構的作用。武漢大學賀鈺瀅的《知識生產與傳播——跨國學術出版集團角色定位與功能分析》[4],從知識開發平臺的角度考察了愛思唯爾(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約翰威利(John Wiley & Sons)、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Group)四家學術出版集團所作出的努力,但主要是對數字化傳播技術與知識生產流傳、方式的探討。可見,專門研究和深入總結西方出版機構在西方知識與文化全球傳播過程中所發揮作用的文章并不多見。
筆者作為《德古意特出版史:傳統與創新1749—1999》的譯者,發現以德古意特、施普林格為代表的一大批德國跨國出版企業的國際化過程,和西方知識與文化的全球傳播歷程幾乎同步。如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200年間,德國跨國出版企業不僅推動德國化學、機械、醫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出版物走向全世界,而且將費希特、尼采、歌德、席勒等哲學、文學大家推廣到全世界。其中,德國出版人是西方知識與文化全球化的組織者、推動者、傳播者,德國出版機構起到了“發動機”的關鍵核心作用。筆者不揣淺陋,以德古意特、施普林格為例,探討德國出版機構在推動西方知識與文化全球傳播方面發揮的作用,以此為提高中國的世界出版能力提供借鑒。
一、德國世界出版的發展歷程
出版機構作為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承的專業機構,是推動一個國家、民族的知識與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保障,這涉及世界出版能力的建設。所謂世界出版能力,指的是:以某一語言為主要載體的圖書、期刊、數字化以及影像產品的讀者群,至少要包含兩個以上國家、民族的讀者;出版該語言文化產品的出版傳媒機構,至少要在兩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展開出版活動;該出版傳媒機構的人員,至少來自兩個以上或更多的民族、國家。概括來說,即“三跨”,跨語種、跨文化的出版內容,跨國家、跨區域的出版市場,跨國籍、世界化的出版隊伍[5]。就某種程度而言,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須要有從文化母體中走向世界的國際化出版機構作為保障,否則國家、民族文化的世界影響力提升便無從談起。國際化出版機構是世界出版能力建設的基礎。筆者梳理構成德古意特出版聯盟的賴默爾、戈申、維特、特魯布納四家出版機構以及施普林格的發展歷史,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面對急劇變化的國內外時局時采取的經營策略,都是在主動或被動地提升世界出版能力。
1.出版語言的選擇轉變
世界出版能力建設首先體現在德國出版人在德語、英語兩種出版語言的選擇轉變上。在二戰之前,德國出版機構一直堅持使用德語出版。例如,德古伊特聯盟之一的特魯布納出版社,創始人特魯布納就是出版人,同時也是德語文化的保護者、生產者和組織者,堅持出版了一系列德語語法、德語辭典等圖書。如其于1883年出版了德語語言學家弗雷德里希·克魯格(Friedrich Kluge)的《德語詞源詞典》(Etymologisches W?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收錄了大約5000個德語關鍵詞,截至1995年,該辭典已經出版了23版,德語關鍵詞已擴充到1.3萬個,并增加了大量特殊目的用詞和外來詞的解釋[6]。1888年,特魯布納與斯塔拉斯堡大學研究浪漫文學領域的教授古斯塔夫·戈洛博(Gustav Grober)編著了《藝術語言學概論》(Outline of Romance Philology),這些德語圖書確立了特魯布納出版社“語言學領域開拓者”的圖書品牌。但在二戰后,隨著美國繼英國之后主導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格局的逐漸確立,英語的世界地位大大超過了德語。擁有大量自然科學技術優勢的德語出版物必須面對保持德語出版還是改變為英語出版的巨大挑戰。雖然當時德語在東歐和北歐等部分國家依然是學術語言,但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已把英語當作國際通用語言。這就意味著德國出版機構不可能像從前一樣用德語出版所有科學領域的圖書。對德國出版人而言,這是一種痛苦的轉變。
施普林格掌門人費迪南德二世,就曾經貫徹“把德國科技用德語出版物推廣到世界”的理念。曾經服務于施普林格的員工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我不止一次地建議費迪南德二世先生,給癌癥研究的德語期刊加上英語介紹,但他一直不為所動,并認為推廣德語是德國出版機構的擔當。”特別是當時還有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對德語科技圖書的咨詢,使費迪南德二世更相信“德語出版物還會東山再起”。1964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得主,德國生物化學家費奧多爾·呂嫩(Feodor Lynen)的研究成果在英文刊物《生理評論》(Physiological Review)上首發,按照規定,該文無法在施普林格的權威德文學術刊物《生理學》(Ergebnisse der Physiologie)再次發表。即使是該文的德語版,因為不屬于首發,所以施普林格也不會采用[7]。類似這樣的現象,在當時的施普林格屢見不鮮。78709D71-B1AF-434B-87A9-F4A4D72D24AA
世界的發展趨勢是難以改變的。當一些年輕的德國科學家于美國學成返回德國后,他們發現德國高校規定學術文章必須要用德語發表,便干脆直接用英語在美國發表了學術文章,這讓德語期刊陷入了一種更加不利的處境。在各種壓力下,施普林格下定決心適應世界學術語言的變化。在20世紀60年代末,施普林格確定秉持“通過英語出版物,讓德國的科學更為世人所知”的新出版理念,從而吸引優質的作者,擴大施普林格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為此,作者主動將大量德語圖書譯成英語,施普林格雇傭英語為母語的人做編輯,以便檢查和提高德語譯稿的文字水平。這種從德語到英語的選擇轉變,不僅維護和保持了德國自然科學領域的權威地位,還鞏固了其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德語醫學出版物在日本醫學領域影響很大。二戰后,大部分日本科學家已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而熟諳德語的學者逐步減少。施普林格此時將大量德語圖書主動翻譯為英語,成功改變了德國出版物在日本市場停滯不前的局面。與此同時,施普林格積極進軍美國出版市場。在航空航天領域,施普林格也把自己擁有版權的同類作品主動翻譯成英文,如《飛行模擬器:國際航空研究的歷史軌跡》(In Flight Simulators and Fly by Wire/Light Demonstrators: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Research)等,同時邀請美國作者撰寫相關領域的圖書。這樣,施普林格就成為德國出版機構中較早以英語為主要出版語言的出版社之一,同時開啟國際化發展道路,奠定了發展為跨國出版集團的基礎。
2.跨國家、跨區域的出版市場布局
在跨國家、跨區域的出版市場方面,德國出版機構歷經了從實物圖書出口到開展本土化出版合作的發展歷程,其在中國市場業務模式的改變十分鮮明地體現了這種轉變。施普林格與中國出版界的接觸始于1956年,中國派出國際書店(現為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參加德國萊比錫國際書展,但是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后雙方才真正構建實質上的合作關系。1974年,施普林格派出銷售代表與剛剛組建的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交流,此后與中國科學院、南開大學、同濟大學、湖北醫學院等相關科研機構、高校廣泛合作,主要出口德國相關的自然科學領域實物圖書。根據施普林格的統計:德國圖書出口到中國市場的份額,在1974年僅有19.6萬馬克,1986年就迅速增加到123萬馬克;德國期刊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從1974年的13.6萬馬克,增長到1985年的133.2萬馬克。施普林格在1978年出版了“世界斷肢再植之父”陳中偉的《顯微外科》英文版,1982年出版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數論導引》英文版。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等翻譯出版的施普林格的《機械學工程手冊》,迄今為止仍是中國機械專業的通用教材[7]。
施普林格依托自身在全世界圖書、學術期刊等領域的國際化市場渠道優勢,與中國相關出版機構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這種合作從20世紀80年代的實物出口升級為渠道合作,即開創了一種“中國模式”:不僅用自己在世界上的渠道優勢幫助中國出版的英文學術刊物發行,還幫助中國學者熟悉和掌握世界英文學術期刊的規范、體例進行撰寫、編輯等。施普林格早在1984年就與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展開合作,使英文《中國電子科學學刊》(Journal of Electronics:China)在中國學術界首次采用世界同行的匿名評議方法。1997年,施普林格與科學出版社就《中國科學》雜志的5種英文期刊《中國科學:數學》(Science China Mathematics)、《中國科學:生命科學》(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等開展合作。為了順應中國政府倡導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等號召,2006年,施普林格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就8種學術期刊《中國歷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國哲學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等開展合作。2008年,施普林格與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合作出版了《出版研究季刊》(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及介紹中國出版業的特刊《中國出版業研究》。2020年,施普林格與復旦大學合作,出版了《復旦人文社會科學論叢》(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8]。在施普林格與眾多中國相關機構合作的系列學術期刊中,于1997年與科學出版社合作的5種學術期刊,目前《中國科學:技術科學》(Science China Technological Sciences)已經停刊,其他的4種期刊仍在出版。
除了期刊,在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工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等中國政府翻譯資助的工程支持下,施普林格等西方跨國出版機構成為中國出版機構的重要合作伙伴。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合作出版中國主題圖書成為西方跨國出版機構在中國市場上的大宗出版業務。筆者依據施普林格數據庫(Springer Link)的統計,有關中國主題的學術圖書已有19359種(檢索時間為2021年10月29日,網站為https://link.springer.com/,檢索關鍵詞為“China”)。這些高質量的學術圖書,絕大部分是西方跨國出版機構與中國相關出版機構合作出版的。這些學術英文圖書的合作出版,與施普林格和中國學術期刊的合作模式一樣,有的是側重渠道合作,有的是側重英文編校質量,有的還有版權方面的合作。
3.加強國際化出版隊伍建設
在跨國籍、世界化的出版隊伍建設方面,德國出版機構歷經了從德國本部派人到聘用不同國籍的出版人才開展本土化出版的轉變。如施普林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德國格廷根、海德堡、慕尼黑等設立辦公室,之后在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法國巴黎、中國香港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十家分支機構。在大規模的兼并和重組之后,施普林格逐步擴大了海外分支機構的數量和規模,并逐步成為全世界商業、自然科學、工程和社會科學等領域的領導者。2015年,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組建,在世界各地設有分公司和辦事處,擁有1.3萬名員工,當年營業額為15億歐元。78709D71-B1AF-434B-87A9-F4A4D72D24AA
德古意特出版社與中國的業務交流遠遠晚于施普林格。直到2011 年,德古意特出版社才在北京成立代表處,并聘用中國本土出版人開展亞太地區的出版業務。德古意特出版社于2011年與科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簽署框架合作協議,2012年與商務印書館簽署戰略合作協議,2014 年與清華大學出版社簽署框架合作協議,2017年與南京大學出版社舉行科技類圖書戰略合作簽約儀式。德古意特出版社還與國防工業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和化學工業出版社等多家專業出版社、大學出版社開展合作。2021年,德古意特出版社利用自身優勢,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合作出版了由北京外國語大學相關學者主編的9種國際刊物,這是德古意特出版社在中國開展本土化業務的新拓展。
二、中國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是關鍵
上文通過梳理德古意特、施普林格兩家德國出版機構世界出版的發展歷程發現,出版社在推動德國科學知識與文化的國際傳播過程中承擔了組織者、推動者的核心作用,出版人是不斷自我革新的“發動機”。德國出版機構的發展歷程給中國出版機構帶來的啟示在于如何進一步提高世界出版能力,具體有如下兩點。
1.提高中國圖書及學術期刊出版的國際化水平,多語言出版能力建設很重要
中國出版的編輯生產、加工以及發行等全產業鏈條上,每個環節都有完整的政策、法規、規范,從人才、隊伍建設到漢語出版物的質量檢驗、評估,諸多層面的管理規范都已高度成熟。但是除漢語以外的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其他語種的出版物,發展水平相對不高,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中華文化世界影響力提升的發展瓶頸。中國出版機構在提升世界影響力方面,與二戰后德國出版機構面臨的問題相同,即部分能夠用英語撰寫學術研究成果的中國學者,只選擇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和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等排名靠前的英語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中國漢語學術期刊陷入一種兩難境地。2019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科學技術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部門聯合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為中國出版機構出版的英語期刊提供資助。這是中國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為推動中國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建設,從頂層設計方面采取的舉措。
2.中國出版機構要加快開拓跨國別市場,開展本土化出版業務步伐
目前已有相當一批中國出版機構在相關國家、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中國主題圖書編輯部,有的已經取得了較好的嘗試。但從總體上看,其仍然處在初期階段,特別是2019年底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一些國際化業務處于停滯狀態,大部分國際化項目仍是以接受中國政府翻譯資助工程為主的單本圖書、單個翻譯,世界出版仍然處于不成規模的初級發展狀態。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實力舉足輕重的國際背景下,業界迫切需要站在中國歷史、文化視角上對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新中國成立70多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發展模式和成功經驗進行理論總結,破解歐美學術界、輿論界“闡釋中國”過程中的曲解、誤讀和有意的“妖魔化”,實現從“闡釋中國”到“中國闡釋”的轉變。這就需要中國出版人發揮知識生產的專業組織作用,特別是具有國際視野、國際學術人脈資源的中國出版人,能夠組織歐美等世界發達國家的知名學者撰寫相關著作、召開相關學術會議,從而使相關學術研究成果進入歐美發達國家的主流市場,實現在世界視野下推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創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目標。21世紀以來,除了中國兒童文學、中國科幻文學出版取得了一定的國際影響力,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出版成功案例還不是很多,這需要中國出版人奮起直追。
總之,中國出版機構要更好地發揮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作用,其中的核心是世界出版能力的建設。這里涉及三個層次:首先是跨語種的出版能力,即中國出版機構的圖書、期刊、數字化產品不僅能夠滿足本土中文讀者的需要,還要能夠被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們接受和喜愛;其次是跨國家、跨區域的出版市場拓展,即未來中國出版機構不再以中國為單一市場,還要面對世界不同國家、地區的讀者需要,在出版對象國有針對性地開展出版活動;最后是匯聚世界化的出版人才,所謂世界化的出版人才,就是未來中國出版企業需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編輯、出版和發行人才。因此,中國出版走出去,未來主要努力方向是如何提高中國出版機構的世界出版能力。
|參考文獻|
[1]張克非. 集團化、網絡化、國際化:德國出版業發展的重要趨勢[J]. 大學出版,2002(1):63-64.
[2]陳明瑤. 美國圖書出版業的發展軌跡[J]. 中國出版,2011(6):74-76.
[3]邢來順. 近代德國有組織的知識生產與文化科技發展[N]. 光明日報,2021-08-30.
[4]賀鈺瀅. 知識生產與傳播:跨國學術出版集團角色定位與功能分析[D]. 武漢:武漢大學,2018.
[5]何明星. 中國的世界出版能力現狀與發展契機[J]. 出版發行研究,2018(12):85-90+45.
[6]ANNE-KATRINZIESAK. De Gruyter Publishers: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since 1749[M]. Berlin:De Gruyter,2012.
[7]SARKOWSKI,HEINZ,GATZE. Springer-Verlag:History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House 1945-1992[M]. Berlin:Springer Verlag,1992.
[8]王睿. 走近德古意特出版社[J]. 出版人,2017(8):88-89.78709D71-B1AF-434B-87A9-F4A4D72D24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