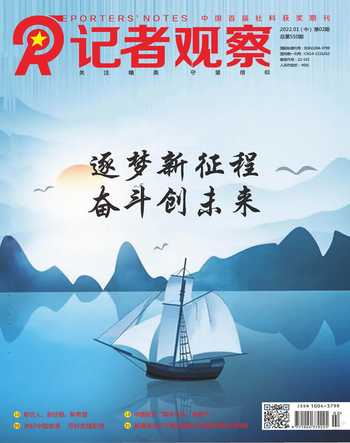煨冬
平川
煨是從前慢,也是天倫樂。
“煨”在現代,多被用指食物的烹制。是將質地較耐煮的食材,加入調料和湯汁,用小火長時間加熱至熟爛的意思。
用煨這種烹調方法,做出來的菜,主料酥爛,口味醇厚。
在福州地區,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詞匯,叫“煨鋪”。鋪,是床鋪,鋪蓋。煨鋪,類似于焐被窩的意思,焐在被窩里取暖。
聽到“煨鋪”二字,很多人會想起兒時的情景:漫漫冬夜,為了取暖,或者節省一些炭火,老人孩子便早早地上床煨鋪,將被窩慢慢煨熱。
屋外寒風呼嘯,屋內其樂融融。昏黃的油燈下,老人講古,婦人拉呱,家人煨坐,燈火可親。“煨”,是從前慢,也是天倫樂,是一個非常動人的詞匯。
“幸有和林酒一樽,地爐煨火為君溫。”火可以煨人,自然可以煨食物。古代人喝酒,喜歡溫著喝,中國歷史上,跟溫酒有關的橋段很多,都極具草莽英雄的豪情,比如,關云長溫酒斬華雄。
溫酒,需要專門的溫酒器,耶律楚材詩中的“樽”,就是溫酒器。但平民百姓沒有那么講究,用炭火的余溫直接煨酒。范成大《冬日田園雜興》詩曰:“撥雪挑來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榾柮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
菘是白菜,春韭冬菘,是古人眼中的美味。
文火煨出來的白菜特別甜。白居易寫經霜的白菜:“濃霜打白菜,霜威空自嚴。不見菜心死,翻教菜心甜。”豆腐煨白菜,放入幾粒大干貝,鮮而綿軟。豆腐白菜,湯白,汁濃,就這點素白鮮美,可以勾起味蕾的前世今生。
范成大詩中提到藕。
湖北湖南人待客,蓮藕煨排骨是必備菜品,藕香與肉香融為一體,咕嚕咕嚕一碗下肚,從舌尖暖到肚里。若是你去了武漢,武漢的朋友會交代你:今晚你莫安排其它事情了,我屋里煨了湯在,晚上到我屋里喝湯去。
這湯,八成就是蓮藕煨排骨。
武漢人用來煨湯的,是粗陶器,叫砂銚子。因為粗陶透氣,煨的時候,可以把油膩滲走,這樣剩在銚子里的都是不膩人的精華。
白蘿卜古稱萊菔,也適合煨。宋人林泳說,“折項葫蘆初熟美,著毛蘿卜久煨香”。菊后的蘿卜豐盈肥美,瀅潤多汁,最適合煨著吃。宋人姜特立詩曰:“爛爊萊菔甜如蜜,細點豬臁滑似酥。”
這樣的詩句,讀著便覺得好吃。這是用時間慢慢釀出的美味,也是古人恬適自得的生活理念,有一種古樸的詩意。
從烹飪上說,煨,相當于小火慢燉。用砂鍋煨菜,火候只有燉菜的一半,所用的時間,卻是燉菜的兩倍。但比起炒、炸、煎等烹飪方法,煨出來的菜肴,所含的脂肪少,很大程度保存了食材的營養。從健康角度看,也是一個可取的烹飪方法。
在我的家鄉,舊時冬天漁閑季節,漁民會利用這段時間,為來年的漁事做準備,修船,補網,染帆。染帆需要燒水的,修船也要熬桐油,打桐油灰。
他們在野地里支一大鐵鍋,燒水,浸染,或者支鍋熬桐油。頑皮的稚童,一看到支鍋,就預備好紅薯、芋頭。等火熄的時候,將紅薯、芋頭埋在紅紅的火堆下,慢慢地煨。
文震亨《長物志》稱:“御窮之策,芋為稱首”。禪門中有“芋頭禪”的說法,比喻清苦的修行生活,八大山人以芋頭入畫,平淡中自有意味。出身于江南名門的文震亨,自己也愛食芋。因此才有詩的下一句:“寒夜擁爐,此實真味。”
袁枚是清朝第一大老饕。他在《隨園食單》介紹一款“芋羹”:“芋性柔膩,入葷入素俱可。或切碎作鴨羹,或煨肉,或同豆腐加醬水煨。徐兆璜明府家,選小芋子,入嫩雞煨湯,妙極!”
硬的食材猶如嚴冬,都適合于煨。小火煨得三冬暖,煨出來的食物,恰如金燦燦的陽光爬進窗戶,連身子骨都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