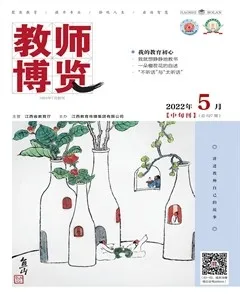我以我心寄明月
鄒星旺
一
當我背著行囊走進師范學校時,我心里清楚,其實那不能算是我的選擇;真正選擇做一輩子老師,是在我走上教師崗位若干年以后。
20世紀90年代初,農村娃上大學還是稀罕事,對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能放下鋤頭吃上公家飯,無異于鯉魚躍過了龍門。所以得知我能上大學,家人高興得整天都合不攏嘴,哪還挑三揀四的,于是志愿一般都由班主任代填。蒙頭蒙腦地,我就這樣讀了個師范。
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一所農村中學,開始了“孩子王”的生涯。一切看起來都還順利,雖然有時不免被氣得抓狂,但工作熱情卻頗高漲,經常“開夜車”都要把當天作業批改完。那時花費心血最多的是批改學生日記,一篇篇看,一篇篇批改,絕不走馬觀花寫一個“閱”字了事。我的認真換來了學生們的認真,更可貴的是收獲了孩子們的真心:在日記中他們不僅呈現奇思妙想,更多的是傾訴他們的喜樂哀愁。一個個小小的秘密,一份份真誠的信任,使我不敢有絲毫懈怠,只能更加走心地一一批改。通過日記,我和孩子們的心緊緊連在了一起。我發掘了文字特有的力量,并享受到了它帶來的快樂:傾訴,溝通,濡染,傳播。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這文字的交流中,一點一滴地成長。
這成長當然也包括我自己,以至于許多年以后——直到現在,我仍感激那時的自己,有那么一份單純的熱情,投入到那么一項單純的工作中。其給予我的最大回報,就是讓我愛上了教育。
我仍然記得,一個夏日的午后,我的發了小財的發小站在我面前,眉飛色舞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地勸說和邀請我“下海”的模樣,但我已忘了自己是怎么拒絕他的,因為按理我沒有理由拒絕他:當時的我既無榮譽加身,更無職位虛待,每月工資區區二百余元,還往往被拖欠著不發;那時很多年輕老師連討老婆都成問題,不少人因此告別了講臺。
我那時肯定是動了心了,但結果居然是拒絕了他。我想這一定跟那些我批改過的日記有關,跟課堂上的歡聲笑語、課后學生們的簇擁有關,跟學生畢業后寄來的一沓沓信件、打來的無數個電話有關……
這樣的誘惑之后當然還有很多次,但那次,我在心里其實已認命:好好教我的書吧!物質上不能富有,至少精神上不能貧窮。
二
但好好教書又談何容易。
“學生需要一杯水,老師要準備一桶水”,隨著從教年頭的增長,我發現要準備這“一桶水”竟是越來越難了。當時互聯網還不發達,鄉鎮尤其閉塞;圖書資料奇缺,學校能提供的就只有課本和配套的一本教參。我知道自己已是那井里的青蛙,只是還有點自知之明罷了。
一課本、一教參、一粉筆、一輩子,這樣下去似乎亦無不可,但我捫心自問,此非我之所愿。苦惱、糾結一番后,我終于決定了要考研。那一年,已是我從教的第七個年頭了。
最大的挑戰是英語,幾乎是從ABC重新開始學,每天規定自己背單詞和短語不少于四十個,做閱讀理解不少于兩篇,務必弄通吃透……此后我告別了心愛的吉他、圍棋、籃球和電視劇,除了吃飯睡覺,基本手不釋卷。其間,我被選調到了一所省重點中學,但并未因此而停止考研,因為我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兩年多后,我終于如愿以償,考上了。
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我考研的初試成績名列前茅,可復試之后卻排名靠后,這充分暴露和印證了我專業知識的薄弱,我需要補的課太多!
時隔多年,能夠再次做回學生,這種幸福一般人不會懂。我當然知道該如何享用這幸福,不會忘卻為何身居此處。三年讀研,孜孜以求,自不敢說飽讀經書,但也算是眼界大開。光是撰寫畢業論文,我就花了近兩年時間,翻閱了二百多部書,做了五大本筆記。在老師的悉心指導和自己的努力下,知識和能力有了一點可見的進步。
無論如何留戀與不舍,畢業終會如約而至。我幾乎毫無遲疑,選擇回到家鄉的一所中學任教。在我放棄編制、錯過評職稱、窮盡辛苦求學之時,有人以為我肯定是想要上天;結果我折折騰騰兜兜轉轉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這在他們眼中簡直成了笑話。對此我只能一笑置之。他們或許不會明白,不拋棄一些外在的鎖鏈,如何贏得心靈上的自由?犧牲一些無足輕重的東西,能夠更坦然、更從容地站上講臺,那是多么值當。
三
樹欲靜而風不止。當時代的風潮裹挾著教育生態急遽地變化,每一個教育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挑戰與困擾由此層出不窮。何去何從?成為老師們一道必答題。
身處其中,我又豈能例外。
最大的困擾,是應試環境下的分數教育。當分數成為評判師生的唯一標準,它自然就成為教學追求的終極目標,教育的變異也就勢所必然。我看見生源大戰年年上演,狀元宣傳鋪天蓋地,培訓機構人滿為患;我看見學生睡眠嚴重不足,考試刷題層層疊疊,課堂灌輸從始至終……憂心,揪心!但我又能做些什么?
我當然有可以做的事。我不能左右大環境,但從不缺乏影響小環境的機會。我的班級、我的課堂,不能百分之百由我做主,但百分之五十的做主機會豈可放棄?唯一值得擔心的仍是自身的能力不足,魅力不夠,因為有的學生雖然功利,但可塑性極大,只要你足夠鮮活,他們就絕不會死板。
為了讓課堂鮮活起來,課堂外少不了要多下功夫。備課要充分,“一桶水”備足了,課堂上才能游刃有余、收放自如;與學生彼此尊重和信任,不高高在上、居高臨下,于是思想發生碰撞,教學自然相長;豐富學習方式和途徑,各種小組建起來,各項活動搞起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便得以激發;及時地反思總結,不斷地學習提高,先讓學生崇拜老師,再讓老師崇拜學生……
可喜的是,這些探索與付出產生了一些成效。這成效不是指學生取得了不錯的分數,也不是指相關成果獲得了什么獎,而是指孩子們從沉悶壓抑中走了出來,他們意氣風發、彬彬有禮、健康陽光,呈現出年輕生命該有的模樣。
教育的本質不是求分,而是教人求真、求善、求美,如果不能讓人本身變得美好,教育便沒有價值和意義。
2019年,我稍稍變換了一下個人的從教環境,從體制內跳到了體制外,我渴望遇見些不一樣的人,感受些不一樣的教育,但不變的是那顆追逐教育本真的心。此身不知將向何方,此心卻從來未曾流浪。
2021年,“雙減”政策出臺,全國上下大刀闊斧進行教育整頓和改革,我國的基礎教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前方任重道遠,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把握教育本質,堅守教育初心,我們的路就會越走越寬、越走越亮!
(作者單位:江西省南昌市民德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