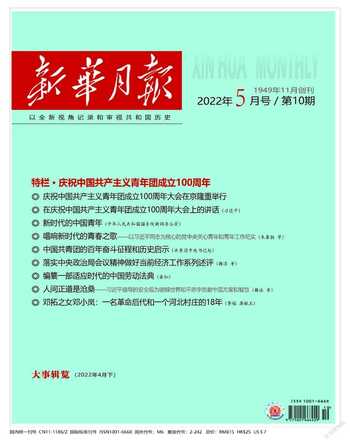林爭平:心里至少上千個畫家,才敢站在那兒
孫凌宇

在各樣導航APP日漸精進的今天,大概沒幾個人能抵擋住出門在外依賴手機的誘惑。但不知是出于對智能時代的負隅頑抗,還是自信與生俱來擁有不一般的腦容量,反正過去幾十年,林爭平都是這么犟著過來的。
他是“行萬里路”的忠實信徒,年過六十,仍北極南極地跑,疫情前2019年還去格陵蘭島爬冰川。他對各地的文化藝術癡迷,至今走訪了120個國家。沒人給他布置任務,說起來都是些不趕時間、自顧自的“文化考察”——哪怕到了瑪雅文化的發源地尤卡坦半島也不請向導,出門前,把地圖“印”在腦海里,不留余地地出發,鉚足了勁地觀察。
不求看全但得深鉆,他身上保留著過去一類旅人有所側重的作風。“事先我對美術都了解,比如說看魯本斯那幅《搶奪留希波斯的女兒們》,在慕尼黑。我到了博物館,就是要看這畫來了。如果是看勃魯蓋爾,要不就是布魯塞爾的皇家美術館,要不就是奧地利。(看的時候)我細心了,花心思了,態度認真了,所以就記得住。要帶著問題,或者帶著這種理解和綜合的歷史觀美術觀,和走馬觀花就不一樣。”
憑借過去幾十年腳踏實地的積淀,如今他的腦海里隨時能攤開一張藝術地圖,“巴黎有七個火車站。去吉維尼的莫奈故居是圣拉扎爾,你要去瑞士是東站,去荷蘭是北站”,甚至形成了獨有的搜索引擎。聊到具體的作品,他從創作始末到收藏脈絡,直至如今存放在哪座美術館都能脫口而出。
“昭陵六駿的那兩駿,1914年被盜賣到國外,在賓大博物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里面,沒在大都會,也沒在華盛頓。
“梵高的《向日葵》,就不說那小的,大的《向日葵》一共就四幅,兩幅15朵,兩幅12朵,15朵的一幅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還有一幅在倫敦國家美術館,那個美術館不在大英,在特拉法加廣場,特拉法加就是當時英國跟法國兩個艦隊——還是帆船時代——打仗,英國人贏了,經此一役建立了海上霸權。廣場立的大柱子上面就是當時的艦隊司令納爾遜將軍,后邊那一片樓就是國家美術館。英文的畫廊和美術館是一個詞,gallery,你不能翻成國家畫廊,這不對的。
“還有兩幅12朵的,背景不是黃色,而是藍色,一幅就在費城,不是在賓大,是費城的博物館,還有一幅在慕尼黑。還有一幅拍賣了,日本的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公司買的,但那幅有爭議。歐洲的一些專家聯名發表過一個聲明,說他那幅是贗品。
“我去東京仔細看過,就擱在新宿西邊安田火災海上保險大廈的美術館里。仔細看了以后會發現,它的筆觸沒有那么自然,有描的感覺。而且那四幅全有簽名,他簽名不是梵高,梵高是姓,他簽的文森特,日本這幅的花瓶上沒字。當然不能說沒字就不是(真跡),這不能是唯一的證據。況且他也是拍來的。20世紀80年代拍了幾千萬(3900萬)美金,當時聽著我都暈菜了,80年代中國人才掙多少錢?三四十塊錢養一家子!”
“拍賣會上買的也不排除有假?”
“這話說起來太復雜,”作為國內1997年拍賣法頒布后第一批考取資格證、從業二十多年的拍賣師,林爭平笑道,“就這一件事咱能從早上聊到晚上。我們這一行挺有意思,好玩,一直到老了你看多有意思。咱倆就隨便一聊,這剛聊出來小手指尖都不夠。”
“他再無知也不能挖苦諷刺他”
早些年為了避免拍到仿作,有人到了拍賣場只買圖錄的封面作品。林爭平解釋,“封面不就是臉嗎?肯定不會是假的,假的不就打臉了是吧?而且肯定是精品,升值空間有保障,這是從商人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買封面肯定不會錯。”
競拍者思路不一,愛好各異,臺下揣手坐著的,有財大氣粗的商人,也有功力深厚的藏家,這就要求臺上負責簡短介紹藏品的拍賣師,既不能太淺薄,又不能太驕傲。“我們可以點一點基本的年份,鼎盛時期之類的,但是你不能說太多,而且得根據現場的氣氛臨時決定說什么,沒法彩排,也沒法做功課,只能靠你的功底。”
有一回林爭平主持拍賣一張齊白石的畫,“齊白石、張大千,都是拍場上最常見的,大概80%以上的拍賣圖錄都印齊白石,但也有少部分印齊璜,我們這行里誰說齊璜?我就說下一件123號齊白石《群蝦圖》。底下一個人,立馬說拍賣師,念錯了,這是齊璜。你想這種事它能發生嗎?它就能發生。”
“按說我就應該損損他,連這都不知道,你還上拍賣場,回家去,先學去。但是你不能損他,他再無知也不能挖苦、諷刺他,來的都是客人,都是上帝。我就說對不起,先生,因為齊白石是1864年的,那都是清代的了。過去這些古人跟咱們不一樣,他們有字有號,齊白石有好幾十個號,白石只是其中一個。還有很多這方面的知識,我們下邊有業務經理,請他來跟您解釋。說完不到5秒,那人便知趣地離場了。”
一口發自丹田的京腔,一雙丹鳳眼笑意盈盈,不論遇到什么情況,作為拍賣師的林爭平時刻謹記“一定要客氣”。2021年12月,在他主持的北京華辰秋季拍賣會上,幾個小時下來都是這副親切做派。
在這場金錢游戲中,人們既體會到了數字飛漲的刺激,同時又享受著和煦的氛圍,沒有壓迫感,但這在林爭平看來,不過是拍賣師外顯的風格,真正的內核在于,“沒有這底子你上哪兒親切去,你就全說的外行話,全踩不到點上是吧?”
主持拍賣絕非在臺上喊個1234那么簡單,林爭平曾見過一些電視臺出身、得過金話筒甚至主持過春晚的主持人嘗試拍賣,很多時候都沒有那么得心應手。原因就在于主持拍賣需要長年的準備,“拍書畫,張大千、齊白石都分不清,怎么拍呀,心里至少上千個畫家,才敢站在那兒。從陶到瓷、青銅器、家具、雜項,你全得知道。瓷器,那少說從唐代開始都差不多1500年了,玉器都8000年了,從紅山就開始了,明清的古典家具也600年了,你得裝多少知識?”4150D57C-C51C-4700-8F08-C18A603A0091
“還得學歷史,因為它那東西都跟歷史掛著,漢代就是有漢代歷史氛圍的東西才那樣,唐代人都胖,所以它東西都是胖的。拍古琴,你至少仲尼、伏羲、蕉葉你都明白吧?你以為是松木做的,以為是榆木做的,以為是黃花梨做的,但它們都是梧桐木的,你都別提,那知識量太大了。這行不允許胡說八道,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裝不了,沒法假裝。瞎侃,你侃不了。”
1997年他去上海參加國內第一屆拍賣師資格證考前培訓,那年一共舉辦了三次,共計幾百名考生,到現在還在做拍賣師的寥寥無幾。“這個行業難度比較大,因為它知識量太大了,別人一說齊白石一張畫一九六幾年畫的,你還說這畫不錯挺好的,但齊白石1957年就去世了,你全得知道,要不然你會出錯的。聊天都沒法聊,你就出局了。”
“稍一走神,準錯”
國內如今拍賣師資格考試的通過率僅為百分之十幾,考試內容仍然是四門,三門理論加一門實際操作,唯一的變化是以往理論部分(拍賣基礎、拍賣案例、經濟基礎)的最后一項取消了(由于涉及簽合同,經濟基礎包含了消費法、合同法等條規以及GDP、GNP等經濟概念),換成了拍賣常識。
拍賣分為藝術品和資產兩個大類,房地產、破產企業、海關罰沒,包括冠名權、知識產權都可以拍賣,還有汽車等物資。依據物品性質不同,拍賣速度的快慢也會有所變化,其中藝術品拍賣相對而言速度最慢。
林爭平模仿起在東京碼頭看過的拍賣金槍魚的場景,魚從漁船上拿下來拍完就得進冷凍庫,太陽曬一會兒就曬化了,因此必須快,叫價時嘴皮子幾乎都沒空隙合上,“1000、2000、3000,下一個。”
從第一次在國外走進拍賣場,拍賣師就給臺下的林爭平留下了“機智、聰慧、口才一流”的印象,至今過了近30年,他少說看過幾千場。2015年大收藏家安思遠去世,在紐約持續了一個星期的拍賣他也沒錯過。
藝術品拍賣雖不至于像其他品類那般火急火燎,但拍賣難度卻有增無減。商品依據起拍價所在的區間在競拍舉牌過程中需要拍賣師按照不同的階梯公式計算。一般國內現在通常分為三個階梯,佳士得和蘇富比則是四個等比階梯:1-2之間是1,2-3之間是2,3-5之間是2、5、8,5-10之間是5,意思是起拍價在10萬-20萬之間的藝術品,臺下每舉一次牌就代表著出價增加1萬;起拍價在20萬-30萬之間的藝術品,臺下每舉一次牌就代表著出價增加2萬,依此類推。
拍品的出場順序并非按照起拍價的高低依序排列,相隔拍品間的價格差異往往很大,需要不斷調整計算方式,而且不同公司的拍賣會可能規則還不一樣,都需要敏捷的反應。在拍賣協會做培訓師時,林爭平偶爾會遇到外語系出身的學員,即便英文能力扎實,但面對英文的數字拍賣瞬間還是反應不過來。“一磕巴自己就慌了,一慌那就全亂套了。”
出錯是拍賣師的大忌。幾小時甚至十幾小時不間斷的拍賣中,拍賣師不僅要維系外部形象——站姿不能七扭八歪,身體得板著,拿著個勁;嗓子不能喊5分鐘就劈了,“即使別著無線麥克風,但如果用的是平日說話的聲音,會太薄,沒有穿透力,打不出去。得用類似美聲的發聲方式,且語音至少得有抑揚頓挫。”林爭平的基本功訓練是念詩歌,“宋詞比唐詩好,沒那么規整,有助于對語言、詞句的掌握和控制”;最后一點,“喝水還得不上廁所。”
這些體力的考驗相對而言可能都算是小事,拍賣師面臨的最大難關是絲毫不敢走神,“稍一走神,準錯。”不但要高速計算,而且全部的器官都得高度集中,時刻關注臺下競拍者的神態,“下邊好幾百人,有些老行家,誰給你拿一牌老老實實舉著,有的號牌都不舉了,手指一晃,從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犄角旮旯,你都得及時看見。”
畢竟拍賣不是單方面的表演,“我得知道他們的心態、舉止,比如一幅張大千的山水畫,通過對當今藝術市場的了解,假設值1000萬,那么從100萬起拍的時候,就叫得很輕松,快到八九百萬的時候,則要開始引導,他們要考慮,要給他們充分思考的時間。買家里北方人南方人都不一樣,北方率直,南方細膩,琢磨的事情多一點,山西的商人跟浙商能一樣嗎,所以拍賣時還得時刻把握人的心態。”
“只預測下限,往上能拍多少價,不知道”
置身藝術品交易的第一現場,身為拍賣師如何看待不同作品天壤之別的命運、抽象的價值如何被赤裸的價格定義,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就林爭平而言,一方面他直率地坦言,個人喜好上他對于時下涌現的新藝術確實欣賞不來。他稱Kaws的作品為“叉叉眼”、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代表裝置為“大氣球狗”,“我可能理解稍微差一點,原來我們看什么破塑料,一百塊錢我都不要,現在上萬了。班克西(Banksy)的作品全是涂鴉,現在都上億了”。這種破除崇拜的態度倒是和藝術家本人的嘲諷態度不謀而合,Banksy2021年在直播中被燒毀轉化成NFT、賺足眼球的數字藝術作品名稱便是:I cant believe you morons actually buy this shit(真不敢相信你們這些白癡會掏錢買這種垃圾)。
但另一方面,林爭平也完全能理解這些作品的走紅以及市場的追捧。疫情開始以后,傳統行業受到沖擊,多個短視頻平臺都曾前來找他入駐,希望他開個人頻道講藝術類的內容。在溝通的過程中,有負責人就表示,“我們這行三十多歲都算老的了,40歲早退休了。”
因此,在林爭平的觀察和理解里,“現在出來一批有錢的全是二三十歲的人,他們對傳統那些東西不感興趣了,所以買叉叉眼了,買大氣球狗了。時代在變化,保利現在也在辦潮玩展了。”
杰出藝術作品的觀念不是自然出現的,而是一套繁復體系造成的結果,其中涉及資助關系、意識形態、金錢與教育,又受到大學課程與美術館的支持——我們認為什么樣的藝術作品特別值得注意,都受到這些因素的引導。
林爭平分析,“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全在博物館里,你怎么炒盤?市場還得活躍,它得維持流動,因為經濟它得轉,你沒東西它怎么轉?所以之前市場最主要的就是印象派的東西,印象派再往前,你看市場上就很少出現了。莫奈1926年才去世的,離咱們還不到100年,所以他這些東西市場保有量還相對多,但現在印象派也賺得差不多了。你得不斷有新東西,印象派再往后,就是安迪·沃霍爾、巴斯奎亞等等,包括現在的Kaws、昆斯。”
1997《拍賣法》剛頒布的那年,北京一年也沒有幾場正式的拍賣。九幾年林爭平剛入行時聽到拍出100萬,都覺得“我的天”,“齊白石當時幾萬塊錢一張,好一點的十幾萬就不錯了。現在少說幾百萬,稍微好一點就賣上千萬了。保證金如今也水漲船高。最開始只需要交一萬塊錢,后來就5萬、10萬,現在如果你要拍5000萬的東西,提前交一兩百萬都很正常。”
到了2003年下半年,他切實感受到中國藝術市場的紅火,“騰的一下,活兒太多了,一年大概我多的時候要拍100場,等于三天就拍一場,全中國大概除了西藏沒去,我基本都去了。”見證了從無到有以及瞬間的爆發,2005年,他主持拍賣的傅抱石的《雨花臺頌》成交價為4600萬,創下當年全國最高紀錄,再之后出現2009年的峰值,國內藝術品拍賣市場進入“億元時代”,他便覺得沒那么意外。
“我們這個行業一般只預測下限——最少能拍多少錢,往上不知道。社會在發展,它和人均GDP有關系。”
二十多年前入行時,他看到的是藝術品升值的巨大空間,“西方的藝術品基金,人家玩了至少一百多年,清代人家就開始玩了,一切都有跡可循。那些東西他們當時買的多少錢,現在多少錢,翻了一萬倍!100年一萬倍,一年10倍!”
到現在吸引著他仍然站在臺上的,更多的是藝術世界的魅力,“為什么我現在愿意干這個?這個行業有意思,也沒有退休這一說,經常拍的時候看到一個之前不知道的,你活到100歲,到100歲也學不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第6期。作者為該刊記者)4150D57C-C51C-4700-8F08-C18A603A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