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杰出學術獎”獲得者與美國的誤區
肖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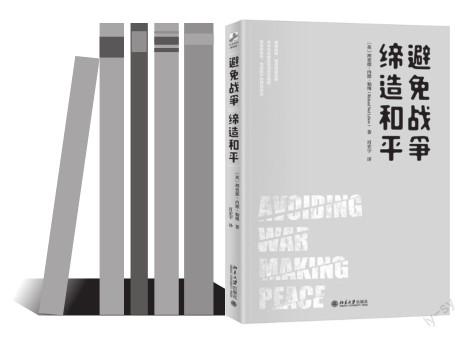
《避免戰爭 締造和平》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國際關系學者理查德·內德·勒博于2018年出版的著作。他在國際關系研究、沖突管理、政治心理學和戰爭研究等領域耕耘多年。在書中,他運用整體分析的方法,展現了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沖突和沖突管理研究,他強調要從跨學科角度加深對國際關系和國際沖突的理解,要重視沖突中的不同因素互動效應的研究,重視檔案等第一手資料、新的史料發現和相關歷史研究新成果的運用。在沖突研究領域,該書被視為是繼托馬斯·謝林的《沖突的戰略》和亞歷山大·喬治與威廉·西蒙的《強制外交的局限性》之后的第三部重要著作。該書在2019年獲得了英國杰出學術獎,中文譯版于2021年4月面世后不到一年即售罄,2022年1月第2次印刷出版。
該書是作者將歷史和心理學引入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一部佳作,同時也是一位有良知的西方學者出于愛之深責之切之情,對美國決策者的委婉建言書。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出于對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挫敗感,他才把研究的注意力轉向了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問題和國際政治秩序的本質問題。在他看來,美國在冷戰結束后“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下,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日益驕橫,逐漸成為一個國際“霸凌”者,消耗了自二戰結束后所建立起的文化吸引力和道義感召力。在新的國際局勢下,美國外交有重拾冷戰時期的“威懾與脅迫”戰略的傾向,這種戰略目的是維護美國既有的霸權地位,遏制正在走向全面現代化的中國。
在書的開頭,作者明確指出,威懾論在當代美國的回潮是美國固有霸權思維的體現,但“霸權與美國利益和全球秩序背道而馳”。作者希望通過該書的分析,“為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確定一個更現實的位置”。他從政治學和心理學兩個角度展開對威懾理論的批判,作者認為美國將威懾戰略運用于后冷戰的世界是一個錯誤。作者指出了威懾理論的預設前提存在重大缺陷,該理論假設,國際沖突對手一方的決策是根據某種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而做出的,從而威懾方可以通過提高行為的實施成本,來嚇阻對手放棄實施不受歡迎的行為。作者認為,政治、心理、實踐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將使得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幾乎不可能,故直接的常規威懾難以成功。
縱觀全書,作者重點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20世紀30年代,認為美國把從這個歷史時期吸取的外交政策教訓“不受質疑的決心遏制挑戰”運用于冷戰,夸大蘇聯的軍事威脅和意識形態分歧,導致威懾遏制理論的流行。在他看來,要批判地看待歷史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領域,因為國際政治常常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情境因素;在制定國際戰略時要秉持開放的心態,要“運用多種相互競爭的視角和相關歷史證據,承認人的能動性和情境的重要性,避免將過去和現在進行簡單的類比”。
與此同時,作者在剖析有關國際沖突的典型歷史案例的基礎上,對作為一種手段的威懾進行了經驗的批判。比如他側重對威懾失敗的歷史案例的分析,指出失敗的原因是威懾方難以避免的在“信息收集、評估、歸因和決策上”的錯誤。通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特定歷史細節的分析,他指出任一簡約的戰爭理論都不足以解釋戰爭的爆發,戰爭的直接原因很可能與深層次原因沒有任何關聯,而且對不恰當目標的關注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可能偏離本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再如他重點剖析了冷戰給沖突管理帶來的教訓,并指出,作為一種手段,威懾的運用在國際沖突中司空見慣,只是在冷戰時期,美國才開始把威懾當作一種戰略使用,但總體威懾在很大程度上對大國是無效的,因為大國往往是“自我威懾的”。冷戰的結束并非威懾的結果,而是蘇聯自身內部變化的結果。
在著作的結論部分,作者指出,批判威懾論不是徹底否定威懾論,而是聚焦于國際危機的管理與沖突的解決,著眼于可行性建議的提出。他并沒有否定威懾在沖突管理中的作用,認為要加強對威懾戰略的能動性、情境因素和心理機制方面的研究,使對威懾戰略的運用要更加準確、謹慎和克制,要同增信釋疑和傳統外交結合起來,才能確保沖突可控。增信釋疑是指通過對等原則、不可撤銷的承諾、自我克制與謹慎、實施有限的安全機制等來澄清意圖,減少因“緊張關系升級帶來的恐懼、誤解和不安全感”,促進沖突的緩和。而作為國與國關系的傳統外交更是不可或缺,因為正是在國與國關系出現分歧或沖突的時候,才是外交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也是發揮人的能動性的時候。外交能確保溝通的存續,減少誤判,防止關系的惡化,避免“相互傷害的僵局”的形成。但是,他也提醒說,外交政策制定者要警惕“認知一致性”,防止在固有信念上犯錯,避免被特定問題轉移戰略目標。
簡而言之,無論是在理論建樹上,還是在實踐經驗上,理查德·內德·勒博都有資格也有能力就當代國際關系的走向以及他所擔憂的美國外交政策建言獻策。他勇于質疑追求簡潔化和學科化的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批判基于理性成本計算的威懾戰略,重拾古典政治研究的傳統概念,把精神、欲望、理智視為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一方面他很像《怪誕行為學》的作者美國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里,對理智能否約束精神與欲望存疑;另一方面他又對人類社會的精神進步、人的能動性的發揮抱有信心。他拒絕悲觀的現實主義沖突論,相信只要做出努力,解決沖突不一定要靠戰爭手段。他指出,威懾、增信釋疑與外交的綜合運用取決于具體情境中的能動性的發揮。理論或經驗只是理解現實問題或者前瞻性預測的出發點,不是決定因素,而情境和人的能動性才是決定因素。對于持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的中國學者來說,這種觀點并不新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是對情境和人的能動性的最佳闡釋。
他擔憂美國政府過度倚重實力導致的霸權政策在削弱美國自身的同時,也破壞了世界的和平,他提醒美國當政者要保持對時代變化和世界發展趨勢的敏感,他提醒美國過多倚重武力或“大棒”的行為與現代文明的期望和規范相悖,指出“同現存倫理規范相一致的外交政策更可能成功,而同現存倫理規范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則可能失敗”。他明確警告說,人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極度抗拒改變”。但時任總統奧巴馬的話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國霸權思維的固化:“如果中國十多億人口都能過上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將會是全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無法承受。”在勒博看來,美國這么做是徒勞的,大國安全的最大敵人不是來自外部,而是自身。對此,他充滿擔憂。他從理論和經驗層面對傳統威懾論的剖析與批判,在今日的美國不受歡迎,這使他感到痛心和焦慮。
此書也間接地提醒我們,中國在走好自己路的同時,要以智慧的方式展示中國現代化發展與世界進步相互成就的過程,展示中國人對“和而不同”理念的堅守和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我們要有“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底氣與信心;面對霸權的欺凌與挑釁,我們不僅要進行有力有理有節的斗爭與反擊,而且要與世界其他正義力量攜手維護與促進世界的公道;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做事節奏,盡最大可能不隨著他國起舞;要不計較一時得失,防止意氣行事,警惕決策被似是而非的大眾情緒所裹挾。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