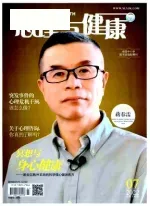“物稀為貴”的治療理念

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總體原則
2006年3月,臺灣的張文和教授在上海進行了“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三五原則”的演講,隨后將演講內容整理發表于《中國新藥與臨床雜志》同年第6期。所謂的“三五”原則是指:一是選藥的“五要”原則,即有效、安全、便宜、方便及易換;二是確保安全的“五不要”守則,即避免錐體外癥候群、高催乳素血癥、并用抗精神病藥物、與抗膽堿能藥物聯用及體重增加;三是必須停藥(或換藥)的五種“要不得”意外,即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癥候群、粒性白血球缺乏癥、急性心肌炎、心室性傳導障礙及新發II型糖尿病。張文和教授所倡導的藥物治療原則的核心,如“五不要”守則和五種“要不得”的嚴重不良反應,來源于英國精神醫學研究院的抗精神病藥物處方指南,即早期版本的《Maudsley精神科處方指南》。
現將2021年最新版《Maudsley精神科處方指南》的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總體原則推介如下:
第一,應使用盡可能低的劑量。對于每個患者,劑量應滴定到已知有效的最低劑量;只有在用藥1~2周后患者明顯表現出療效不佳或無效才應增加劑量。(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除非改變劑量或藥物,否則2周時無效是后期不良預后的有力預測因素。)
第二,定期給予長效注射劑,即使劑量沒有變化,血漿水平也會在啟用后至少6~12周內上升。因此,這段時間內的劑量增加是難以評價的。首選的方法是確定口服藥物在特定劑量下的療效和耐受性,然后以長效注射劑形式給出該藥物的等效劑量。如果這是不容易做到的,那么個人長效注射劑的目標劑量應該是在臨床試驗中確定的最佳劑量(盡管對于早期應用的長效注射劑并不總是有這樣的數據)。
第三,對于絕大多數患者,建議使用單一抗精神病藥物(聯用或不聯用情緒穩定劑或鎮靜催眠藥物)。除了特殊情況(如氯氮平與其他抗精神病藥物的合用增效治療),抗精神病藥物多藥合用一般應避免,因為不良反應負擔增加,與QT延長和心源性猝死相關的風險增加。
第四,只有在單一抗精神病藥物(包括氯氮平)療效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才應使用聯合抗精神病藥物。在這種情況下,應仔細評估和記錄聯合用藥對目標癥狀的效果和不良反應。如果沒有明顯的療效,治療應恢復到單一的抗精神病藥物治療。
第五,一般來說,抗精神病藥物不應該用作“必要時”的鎮靜催眠藥物。建議使用有時間限制的苯二氮?類藥物或鎮靜催眠藥物(如異丙嗪)。
第六,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的療效和不良反應應使用臨床認可的評定量表和患者病歷中的記錄進行評估。
第七,對于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者應密切監測身體健康(包括血壓、脈搏、心電圖、血糖和血脂)。
第八,當減停抗精神病藥物時,以先多后少的雙曲線方式緩慢減少劑量,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停藥癥狀和反跳性精神病的風險。
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的步驟與近期發展
關于精神分裂癥的合理用藥,首先應當嚴格遵循上述藥物治療原則或藥物治療指南。這是藥物治療的合格門檻和規范化。盡管各類精神分裂癥治療指南或藥物治療流程不盡一致,藥物治療一般都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即初始治療均推薦單一抗精神病藥物治療,激越/攻擊或失眠可短期加用苯二氮?類藥物或鎮靜催眠藥物。第二步,療效不佳或無效者換另一個單一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第三步,至少兩種單一抗精神病藥物足劑量足療程治療仍然療效不佳或無效,即針對難治性患者一致推薦單用氯氮平。第四至五步,單用氯氮平無效后才考慮聯用其他抗精神病藥物或加用其他精神藥物增效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治療流程非常簡潔實用,但實際臨床工作中執行質量仍有待提高。
精神分裂癥合理用藥的近期發展主要體現在藥物基因組學技術的應用,由此推動了藥物治療的個體化或精準化。與藥物相關的基因多態性,涉及四個環節:藥物腸胃吸收轉運的P-糖蛋白,藥物肝臟代謝的細胞色素P450酶,藥物血腦屏障轉運的P-糖蛋白,藥物靶位點的多巴胺受體、5-羥色胺受體等。
其中,藥物肝臟代謝酶的基因多態性資料最為充分,并且可以將某些細胞色素P450酶(如CYP2D6酶、CYP2C19酶等)劃分為正常代謝者(extensive metabolizer,EM;即快代謝者或廣泛代謝者;占75%~85%)、中間代謝者(intermediate metabolizer,IM;占10%~15%)、慢代謝者(poor metabolizer,PM;占5%~10%)和超快代謝者(ultrarapid metabolizer,UM;占1%~10%)。不過,細胞色素P450酶的遺傳多態性存在人種差異。
例如,CYP2D6酶慢代謝者在白種人中占5%~10%,在黃種人中不足1%;CYP2C19酶慢代謝者在白種人中占3%~5%,在黃種人中占15%~20%。黃種人包括中國人群還存在60%高頻分布的中間代謝型CYP2D6*10亞型,這也是解釋多種藥物如普萘洛爾、普羅帕酮、氟哌啶醇等日劑量低于白種人的原因。目前,抗精神病藥物的藥物基因組學檢測已經非常普及,但檢測報告的解讀仍有需要進行不斷的完善,相關知識的培訓也應加強,從而提高對臨床應用的參考價值。

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的最高境界—— “物稀為貴”
精神分裂癥合理用藥的理想或最高境界是極簡化,換一句話就是“物稀為貴”(Less is more)。2014年在柏林召開的歐洲神經精神藥理年會上,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Lieuwe de Haan教授闡述了精神分裂癥的低劑量和有時限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策略,強調了“物稀為貴”的治療理念。這一治療理念與“應使用盡可能低的劑量”和“初始治療均推薦單一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等總體原則和治療流程非常契合。充分領會這一治療理念,可以促進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的規范化。
精神分裂癥的藥物治療中存在一些值得關注并應盡力糾正的弊端,這些弊端正是倡導“物稀為貴”的治療理念所亟待克服的。
首先,多個抗精神病藥物聯用以及其他精神藥物加用治療甚為普遍。多個抗精神病藥物聯用并未獲得充足的循證支持,反而有文獻報道與住院率、住院時間、不良反應、用藥劑量、治療費用以及死亡率的增加有關。臨床相對廣泛的多個抗精神病藥物聯用既是為了提高療效,也是為了響應臨床需求如控制紊亂行為、逐步交叉換藥以及氯氮平難治患者的增效。對于難治性患者,治療指南一致推薦單用氯氮平,單用氯氮平無效后才考慮聯用其他抗精神病藥物或加用其他精神藥物增效治療。因此,精神分裂癥的臨床實踐中,單一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仍然是主要的治療原則,從而體現用藥品種的“物稀為貴”。
其次,高劑量甚至超高劑量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屢見不鮮。高劑量往往也是多個抗精神病藥物聯用的必然現象,也是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臨床應用遺留的弊端。高劑量更易帶來藥物不良反應是毋庸置疑的,超高劑量抗精神病藥物的臨床獲益也缺乏循證支持。目前臨床應用的抗精神病藥物均為阻斷多巴胺受體的藥物。這類藥物所致的較高腦紋狀體多巴胺D2受體占有,與更糟的主觀體驗、更嚴重的陰性癥狀以及抑郁有關,也是藥物治療不依從的主要原因。de Haan教授的研究表明,腦紋狀體多巴胺D2受體占有在60%~70%之間具有最佳的主觀體驗,進而挑戰了學科領域普遍認同抗精神病作用的D2受體占有在65%~80%之間。受體的過度占有會出現受體上調,從而可能產生對高劑量的耐受和適應,并導致后續減量或停用的艱難。精神分裂癥患者是神經發育性障礙,包括突觸可塑性功能的失調或低下。現有的多數抗精神病藥物不利于突觸可塑性的改善,高劑量應用時更有可能帶來無法挽回的突觸可塑性損傷。因此,抗精神病藥物的給藥劑量常常需要比常用劑量更低,這是值得倡導的用藥劑量的“物稀為貴”。
最后,抗精神病藥物的長效注射劑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應用。長效注射劑極大地減少了給藥頻率,在提高藥物治療依從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有利于保持患者的病情穩定,穩定的病情有助于患者的功能康復。然而,需要密切觀察遲發性運動障礙的早期征象,如口舌頰三聯征即“兔唇綜合征”,做到盡早識別、盡早處置。長效注射劑的應用可以實現用藥頻率的“物稀為貴”。
抗精神病藥物的過早減停是患者和家屬的不當期望,也是部分醫生的“好心辦壞事”。目前,國際精神病學界已形成共識,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需要無限期治療。人們熟知并樂于接受高血壓和糖尿病等是慢性疾病,在充分控制病情基礎上仍需要終身治療。精神分裂癥則是起病于青少年和成人早期,多數病程遷延,功能受損程度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盡管大約20%患者疾病和功能恢復良好,有可能逐漸減停抗精神病藥物,但是目前尚無有效指標預測患者結局的好壞。如果在精神分裂癥患者初始治療中貫徹“物稀為貴”的藥物治療理念,就有可能減少治療藥物帶來的損傷,患者的功能重建和回歸社會才有希望,將來的減停藥物才有可能順利,至少可以在部分患者中實現有時限的治療。

總之,精神分裂癥的合理用藥包括三個層面:貫徹藥物治療指南,提高用藥的規范化;識別患者個體差異,追求用藥的精準化;最高境界“物稀為貴”,合理用藥需極簡化。用一個成語來概述精神分裂癥的合理用藥是實現“至臻至簡”,“至臻”是追求完美,即規范和精準;“至簡”就是“物稀為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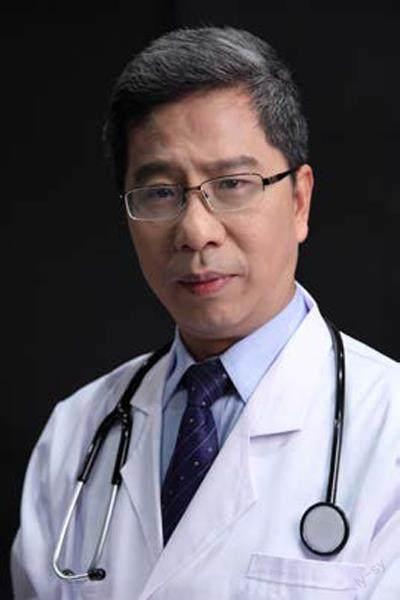
王傳躍,博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精神分裂癥專家團隊領銜專家。現任中國藥理學會藥物基因組學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醫師協會神經調控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精神衛生分會委員、北京藥理學會理事、北京藥學會藥物安全評價委員會委員等,《中華精神科雜志》《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臨床精神醫學雜志》編委,《國際精神病學雜志》和《精神醫學雜志》特約編委。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癥的藥物治療和生物標志物研究。至2022年9月,主持或參與國家級課題17項、省部級課題14項、局級課題10項。參與教材和專著編寫43部,發表論文398篇,其中SCI收錄論文20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