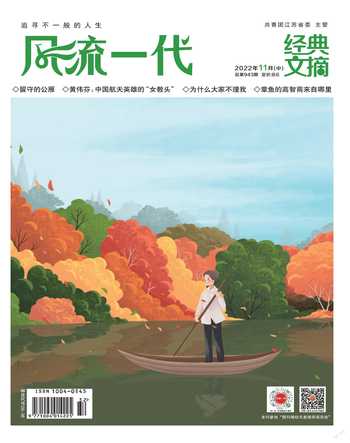大話中國藝術史
意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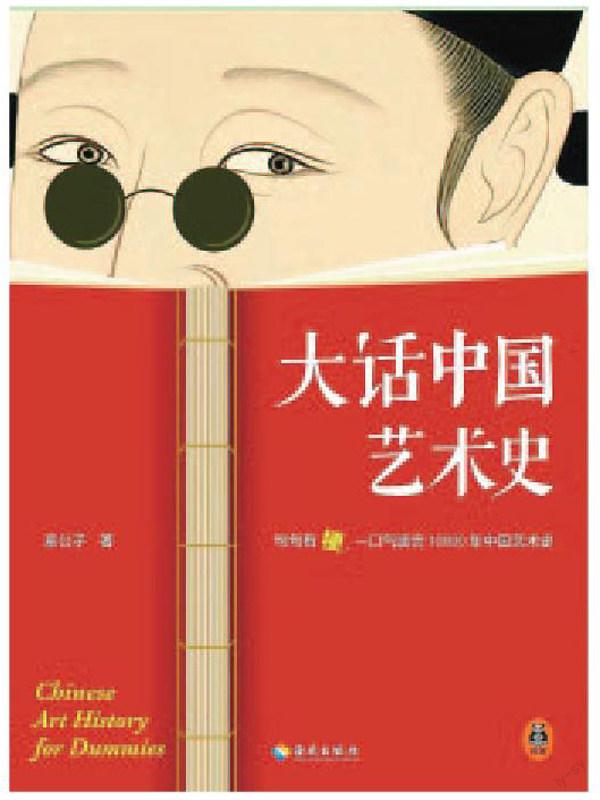
【內容簡介】
熱門藝術書籍《大話西方藝術史》姐妹篇,句句有梗,打破藝術高冷的刻板印象,一口氣讀完10000年中國藝術史。本書從原始社會的陶器說起,內容涵蓋了青銅器、草書、山水畫等多種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150件中華藝術品,45位藝術名家,32個讓你意外的藝術故事,作者以獨有的視角,帶你走近文化自信的根源,解碼中國藝術的深沉內涵,給你博物館式沉浸體驗,感受中國這片土地獨有的藝術色彩。
3000年前的吃貨太講究了
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評出一個最會吃的朝代,那么非周朝莫屬。周人以食、貨、祀、司空(管理居民)、司徒(管理教育)、司寇(管理盜賊)、賓(管理朝覲)、師(治理軍務)為國家施政的8個方面。其中,“食”被排在了第一位。
“民以食為天”,無論是原始時代,還是青銅時代,吃飯都是天大的事兒。
你一定想象不到,在吃這件事上,周朝人講究到什么地步。光是蒸、煮、燜、烤等多種烹飪方式已滿足不了他們那顆吃貨的心。每一樣食材用什么煮,拿什么樣的餐具盛放,甚至都有明確規定。
而他們的餐具不是別的什么,正是我們在歷史書上讀到過的國之重器——青銅器。
腦洞大開一下,假如你今天受邀參加某周代貴族的飯局,那場面很可能會是這樣的:
入座以后,只見大廳中央一口大“鼎”正咕嚕咕嚕地煮著肉。肉香早已蔓延開來,有人從里頭撈出煮好的肉,切成小塊,分到你面前一口小的升鼎里,就像是單人小火鍋一樣。而邊上的“豆”中,放著各種口味的醬料,甜的、咸的、辣的,統統都有。夾塊肉再蘸點醬,頗有我們今天吃涮羊肉的感覺了。主食是“粟”,也就是小米。粟可蒸可煮,想吃干飯就用“甗(yǎn)”蒸,想吃稀飯就用“鬲(gé)”煮,一頓飯也能吃上滿滿一大“簋(guǐ)”。渴了的話,桌上的“斝(jiǎ)”和“壺”里已經裝滿了酒。如果你想喝點熱的,斝還可以拿來溫酒。吃飽喝足,讓我們高舉起“爵”為友誼干杯。
雖然想象中的場景可能遠沒有真實歷史中貴族飯局的奢華,但這些青銅器卻實實在在發揮著各自的作用。飯桌上從煮肉的鼎到當調料盤的豆,從煮飯的甗和鬲到裝飯的簋,從裝酒的斝和壺到酒杯爵……說白了,青銅器直接承包了古人的一整套餐具,跟我們今天用火鍋涮肉、用電飯煲煮飯,有飯碗、有酒杯是一樣一樣的。
根據不同的烹飪方法、不同的食材,再配以專門的青銅餐具,這只不過是周代一個普通貴族的一頓飯而已。
那我們普通小老百姓能用什么呢?別說用青銅器吃飯了,水煮菜先了解一下。
青銅的出現是個意外,但把青銅鑄造成器物卻是個有意而為的大工程。
經過備料、洗泥、制模、夯范、雕刻花紋,還有制芯、焙燒、合范、澆鑄、打磨修整等一系列工序,一個青銅器才算基本完成。乍一看除了工序多點,這青銅器的制作好像也沒什么特別的啊?如果你是這么想的,那就錯了。
制作青銅器的每一個環節都不簡單。單就雕刻花紋來說,那都是有講究的。
哪怕只是一尊酒罐令方彝,都裝飾了10只饕餮、16只鳳鳥和4只虎頭雙身龍,再用整齊精細的回形底紋填滿整個銅器平面,可以說是從頭“武裝”到了腳底,才算完成雕刻花紋這一步驟。而這還只是青銅器在外觀上的小設計。
在青銅器上還藏有更大的“彩蛋”——銘文饋刻。少則幾十字,多則幾百字,記錄下這件青銅器所有者人生中的高光時刻:昨天被天子冊封,今天出征打了場勝仗,還有兩大家族聯姻等各種大事記。對于那時候的貴族而言,青銅器就像是紀念碑一樣。他們把重大事件或文書記錄下來,并鑄刻在青銅器上面,好像這樣自己也能隨著青銅器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數量眾多的青銅器分類齊全,用料極其奢侈,帶著一身繁復的花紋,用鐫刻的銘文定格著一段段歷史。這時候,你還覺得青銅器僅僅是周朝天子、貴族餐桌上的一個小小餐具嗎?
《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中國古代禮制的開始,就來自我們日常的一餐一飯。只有吃飽喝足了,禮儀禮節才會成為人們下一步的追求。
在3600多年前的商周,貴族們用一整套青銅器完成了在“吃”這件事上的儀式感。觥籌交錯之間,開啟了這個鐘鳴鼎食的青銅時代。朝堂之上,鼎依舊咕嚕咕嚕地煮著肉,而有一種樂器也正在被敲響,它的名字叫,曾侯乙編鐘。
這個黑科技產物,
是給上天聽的聲音
為了能夠“有檔次”地吃頓飯,古代貴族們可以說是極盡所能地“搞事情”,甚至不惜花重金打造了一整套豪華餐具。你以為,這已經夠有儀式感了?不,他們還想來點音樂。
如果回到戰國時期,曾國的宮廷之上,有這么一位叫作乙的諸侯王或許會在宴席上這樣命令道:“來呀,接著奏樂接著舞。”
于是下一秒,曾侯乙編鐘的金石之聲響徹整座宮廷。
據說,這聲音是演奏給上天聽的。有人甚至說,如果音樂有鄙視鏈的話,那么編鐘就應該在這鄙視鏈的頂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那么曾侯乙編鐘就是頂端中的頂端,是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舉世無雙的樂器。
2400多歲的曾侯乙編鐘,有5噸重,兩面墻這么大。在中國目前出土的編鐘里頭,它是眾多紀錄的保持者——數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廣、保存最好、音質最高、做工最精細……同時,曾侯乙編鐘還被稱為“鎮國神器”。
它的出現直接改寫了世界音樂史。
因為在以前,整個學界都以為中國的十二平均律,也就是C大調,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但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卻告訴世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們中國就已經有了自己的十二平均律,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
整套曾侯乙編鐘足足有65口之多,分成3層8組懸掛在銅木結構的鐘架上。
即使放在今天來看,要制作完成這樣數量龐大的編鐘也是個不小的工程。它需要制作者掌握包括音樂、化學、物理學、鑄造學、數學等學科的頂尖知識,同時還得有美學和藝術素養。
因為制作工藝太過精湛,有人甚至對曾侯乙編鐘產生了懷疑:難道這是現代科學家穿越回去制作的?否則憑那時候的生產條件,怎么可能制作出如此氣勢恢宏的編鐘呢?
對啊,曾侯乙編鐘到底是怎么做出來的呢?
首先,它是一組青銅器。青銅器非常講究青銅合金的化學成分,制作非常復雜。而曾侯乙編鐘作為樂器,每一口鐘的構型、幾何尺寸、音樂性能等的設計和安排對鑄造技術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其中大點的編鐘高度超過1.5米,光是制作這樣一口大鐘,就需要用136塊陶制的模具組合成一個鑄模,然后在里面灌上將近1000℃的銅水。一口鐘就這么費勁了,更別提這一整套下來需要花費多少年。
關鍵是,曾侯乙編鐘還不是普通的青銅器,它跟別的青銅器不一樣,作為樂器它得發出樂聲。所以在鑄造過程中,工匠們需要嚴格把握好銅、錫、鉛3種金屬的配比,讓它們達到一個黃金比例。
后世科學家們經過反復實驗后發現,當含錫量在13%~16%、含鉛量在1.2%~3%時,編鐘發出的音色渾圓飽滿,且鐘聲能快速衰減,聲音和聲音不會混雜在一起,是最適合進行演奏的。
想象一下,2400多年前的古人沒有精密儀器,要讓每一口大小不一的鐘都能達到演奏水準的黃金比例,唯一能靠的也就是自己的實踐和經驗了。
而且光是這樣還不夠。為什么說曾侯乙編鐘了不起呢?
史料記載,在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其實都有過鑄鐘的實踐,但它們所鑄造出來的鐘都是圓形的。無論你怎么敲,鐘只能發出一個音,而且延音很長,根本不能做成樂器。
但是,中國古人卻做到了讓鐘成為樂器。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曾侯乙編鐘有的鐘表面有些凸起的“疙瘩”。這些“疙瘩”的準確名字其實是“鐘枚”。它的用處就在于減小聲音的擴散,防止編鐘擴音太久,發出更加渾厚的低音。這樣,我們就能把鐘當成樂器使用了。
這還不是最厲害的地方。我們不僅讓鐘變成了樂器,而且可以讓一口鐘發兩個音。
古人巧妙地把編鐘做成了“合瓦形”,把鐘分成瓦狀的兩塊板拼在一起,這樣敲擊正面和敲擊側面時,就相當于敲擊不同的板。并且,鑄鐘的工匠們為了能更好地區分一口鐘的兩個音,還把編鐘的振動塊分離開,在鐘體里面挖隧道隔音。
一鐘雙音,這是中國先秦時期編鐘的獨門手藝。
不夸張地說,曾侯乙編鐘稱得上一件集音樂、美學和科技于一身的藝術品。當時制造編鐘的難度之高,遠超我們今天的想象。即便是在曾侯乙編鐘出土之后的1979年,我國考古、音樂、機械等方面的眾多專家一起研究復刻“曾侯乙編鐘”,也投入巨資,歷時5年才最后成功。
“堂下之樂,以鐘為重”,想象一下,在群山之巔的祭祀大典,在金戈鐵馬的出征現場,在國君宴請使臣的殿陛之間,樂師們手拿著敲鐘槌撞向編鐘。一時之間,鐘鼓齊鳴,“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鑰,似星辰日月”。天、地、人在這一刻渾然一體,這個聲音仿佛就不是人間會有的……
有四方,才有中國
三星堆遺址距今約3100—4800年,比古希臘文明(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要早得多。這是一處古蜀國的文化遺址,是中國20世紀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各種青銅造像。
在它們身上,有太多的謎團至今難以破解——
在銅礦產量不多的四川,要制作數量這么多的青銅器,原料是從哪里來的?
如此高超的青銅冶煉技術和青銅文化,是自己發展出來的,還是外來之物……
要弄清楚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是得從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入手,比如青銅神樹——三星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三星堆遺址一共出土了8棵青銅神樹,其中修復最完整的一棵有近4米高。要不是最上面的部件已經缺失,這棵青銅神樹的高度能有5米左右,也就是快兩層樓那么高了。
我們說過青銅器的冶煉制作過程,在商周時期,應用最廣的青銅器鑄造方法是范鑄法,也就是先做模具,然后把液態的銅水澆注到模具里,等到冷卻之后再扒掉模具進行修整。但這棵青銅神樹,它有很多細細的枝杈,枝杈上還站著太陽神鳥。且不論這個模具制作有多么復雜,光是把銅水灌進模具這一步,就無法實現。因為銅水凝固速度太快了,倒進模具后還沒等它流到枝杈末端就會凝固,更不用說枝杈上的太陽神鳥了。
那三星堆的古人是怎么做的呢?
科學家曾經研究過三星堆青銅器的成分,發現其中居然還有磷元素。這不僅與中原地區的青銅內部元素不同,也完全顛覆了世人的認知。
在大眾的認知里,磷元素是1669年德國商人布朗特在尿液中提煉出來的,難道遠古時期三星堆的先民們早就發現磷了嗎?
更讓人驚奇的是,他們居然還能精準地計算銅和磷的比例。因為銅的熔點在1000℃以上,而紅磷的熔點只有590℃。在當時,主要燃燒材料還是木柴,木柴的燃燒溫度在800℃上下。三星堆的先民把磷摻雜在銅里,就降低了金屬的熔點,也降低了燃燒的難度,從而在澆注銅水的過程中讓銅水在模具內能流得更快,順利流到枝杈末端,流到太陽神鳥的部分再凝固。
太厲害了,你不得不佩服幾千年前古蜀人高超的技藝!
除了青銅神樹,三星堆還出土了眾多的青銅造像。令考古學家好奇的是,從古至今,四川就不是盛產青銅的地方,那這些青銅原料,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學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金正耀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做了系統的鉛同位素分析和研究,發現在這些青銅器中含有一種名“高放射成因鉛”的物質。這個物質并不產自古蜀之地,而是與中原殷墟(今河南安陽)所用的主要青銅礦料來源相同。
那問題又來了,三星堆現在已經出土的青銅文物就已經達到一噸以上的重量。數量如此巨大的原料,究竟是怎么被運到古蜀國來的呢?
至今,人們也沒有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而這個問題,還不只是出現在青銅文物身上。
三星堆遺址里還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部分象臼齒經過科學鑒定屬于亞洲象。我們知道,并不是所有雄性的亞洲象都有象牙,這么多的象牙,那得多少頭大象。而這么大規模的象牙又是來自哪里,都是古蜀國本土的嗎?有不少學者傾向于,三星堆的象牙是來自異域,比如緬甸、南亞或者印度。
在三星堆出土的這些非本地“出產”的象牙和青銅器,無一不在告訴我們,幾千年前的古蜀國有著豐富的對外交流活動。
李白在《蜀道難》里寫道:“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也許,在遙遠的古蜀國,有著一條連李白都不知道的神秘通道。而就是這條古道把古蜀文明、中原文明甚至更遙遠的異域文明連接在了一起。
今天我們走進三星堆,不只是走進一個遠古文明,更是走進一個個巨大的謎團。而一次次揭開謎底的過程,更是充滿了驚喜,并且具有非凡的意義。
三星堆的存在,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曾經,我們以為它的緣起是“站中國,雄踞四方”,但是三星堆文明告訴我們——有四方,才有中國。
中華文明,并不是發源于一地,然后傳向四方的,而是從一開始,就如點點繁星,在中華大地各處誕生、發展、綻放光輝。
(摘自海南出版社《大話中國藝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