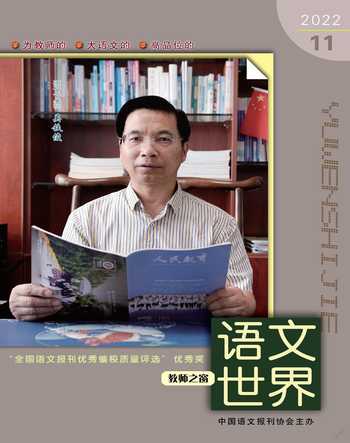孔子的“詩教”
葉水濤
孔子很有美學素養,也非常重視審美教育。孔子的美學情懷與審美追求是與他的政治理想連在一起的。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周代,其實是上古時代的社會。上古時代的社會是充滿原始色彩的,人們對外在世界充滿著好奇,對大自然既感到神秘又懷著深深的恐懼,有限的認知能力常常需要借助想象的幫助。于是,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是未分化的世界,主觀和客觀的分界不那么清晰,萬事萬物都被視作是有生命的,是能對話和共同生活的。因而他們的想象非常的大膽、新奇和豐富,具有泛審美化和泛藝術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孔子時代尚未完全消失。孔子則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是特別具有藝術與審美氣質的人。
梁漱溟先生說,中華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他舉例說,同樣面對屋子漏雨,西方人的直接反應是,哪兒漏了,為什么漏的,怎樣讓它不漏;中國人則是另一種反應,屋子漏了一時不能修復,那就承認這個現實,“留得枯荷聽雨聲”,從滴滴答答的漏雨聲中,獲得一種審美的愜意;印度人有一種虛無化的“空”,無所謂漏雨或不漏雨,可以選擇無視它。這種文化視角的分類,到底有多少科學和嚴謹性姑且不論,但中華文化有其早熟的一面,主要是詩性的早熟,而非全面的成熟,或許是合于歷史事實的。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這在今天看來有點奇怪。“不學詩”怎么就不能講話,或不會講話呢?但在那時,“詩”是一種“普通話”,在政事和外交中廣泛應用,所以,不學習詩歌就難以用語言交際。詩歌語言可以喚起別人更多的想象,作為外交辭令也就具有它的豐富性,讓對方思而得之,心領神會。詩歌語言是藝術化的語言,具有審美的感情色彩,在外交場合能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這是最恰當的表述,也是富有解釋張力的表述。明乎此,就能理解為什么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意味著不會搞政治,不適宜搞外交。孔子非常深邃地看到,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詩歌作為一種藝術語言,它審美化的表達方式蘊含著巨大的認識溝通的意義。
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對于非音樂的耳朵,再美妙的音樂也不成其為音樂。對詩歌藝術、對藝術審美,孔子之所以推崇備至,是因為孔子首先是一位有精湛造詣的藝術家,是藝術審美的行家。孔子在齊國聽《韶》樂,竟然達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感慨說:“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他平時經常操琴鼓瑟,擊磬歌詩——“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甚至周游列國處于危急之境仍“弦歌不衰”。
孔子在教學中經常談論藝術,讓學生學詩習樂,他將“詩教”和“樂教”作為教導學生的重要課程。“吾與點也”,孔子的這一感慨之詞,處于《論語》中最長的一段記述中,也是描寫最為細致與具體的一段,其中心在對詩意人生的向往,對藝術審美境界的贊嘆。
在孔子看來,美育就是一種情感教育 。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在孔子看來,“詩教”有倫理道德教化與認識的功能,但首先是一種情感教育。“興”,孔安國注為“引譬連類”,朱熹注為“感發志意”;“觀”,鄭玄注為“觀風俗之盛衰”;“群”,孔安國注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為“和而不流”;“怨”,孔安國注為“怨刺上政”,朱熹注為“怨而不怒”。
在“興、觀、群、怨”中,“興”是藝術的審美本質,意指在聯想和想象中表現情感,這就規定了孔子的“詩教”是一種情感教育。“觀”,指詩的認識功能;“群”,指詩的倫理凝聚力;“怨”,指詩的悲劇精神。因此,孔子的“詩教”在情感教育的旗幟下,強調了美育對于提高人的認識能力,尤其是人們倫理道德自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