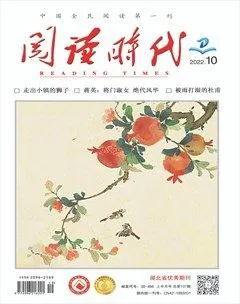品讀孟郊
梅贊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孟郊的這幾句詩,我們耳熟能詳。但再往下,我們卻對孟郊其人其詩知之甚少。其實,在燦若星辰的唐詩星空里,孟郊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詩人。
《唐才子傳》中說孟郊(字東野)“性介,不諧和。”正是這種性格鍛造了他的詩風。孟郊所處的中唐,唐朝已褪盡它的雍容華貴,開始從云端急速墜下。唐代的詩風也在迅忽的流變,從“重粉澤,應試及交際”到“脫于試帖習氣”(曹慕樊語)轉變,而孟郊則是“力背時流”,開一代詩風之先行者,也是中唐韓孟詩派執牛耳者。韓愈比孟郊小十七歲,是孟郊的小迷弟。他這樣夸贊孟郊“……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馀,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洋溢的詩情,熱烈地鼓吹,從出身、為人,際遇、詩才等方面為孟郊站臺。
詩歌是生活的投影。孟郊一生不得志,四十六歲考中進士,五十歲任溧陽尉,這與“修齊治平”期望值有著巨大的落差。因此,孟郊“閑往坐水傍,命酒揮琴,裴回賦詩終日”,不問政事,終日作詩。自然“曹務多廢”,于是,“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如此,工作丟了,孟郊只能“辭官家居”,因而“一貧徹骨,裘褐懸結”,后仕途一直不順,貧病交加,又經歷了老年喪子,但一直“未嘗俯眉為可憐之色”,保持著一個詩人的骨氣,也正是這樣的生活經歷,才使孟郊的詩風,與人迥異。
《唐才子傳》說孟詩“工詩,大有理致”。說到詩中的議論和哲理,多指宋詩。錢鐘書認為,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而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然而,孟郊的詩恰恰以理見勝,不見或少見盛唐詩人那種汪洋肆恣的意興。所以南宋著名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

縱觀孟郊的一生,他奮斗過、失敗過、失望過、貧窮過,就是沒有發達過,可以說是在激憤中度過一生。可想而知,一個渴望入世的詩人,一個滿懷為君盡忠,為民解難的官吏,面對郁郁不得志的現實,怎么會不流露出激憤的詩情呢?這在孟詩中表現得尤其特別。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是詩人少有的快意人生,那種狂喜、激情是噴發出來的,用峻激來形容真是準確而形象。而《擇友》:“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里生荊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茍且得。若是效真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吝色容,心無詐憂惕。君子大道人,朝夕恒的的。”罵人夠厲害吧,哪像讀儒家經典追求中庸之道的謙謙君子?但是不是讓人讀了感到痛快?現實社會里人面獸心的東西還少嗎?該不該罵?活該。當然,孟郊的這種憤懣的怒斥式的直抒胸意的激憤詩在古代詩人中還真是不多見。所以他是個另類。
唐人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孟郊的詩歌風格正是如此,他追求一種奇、冷、澀的詩風。
先說奇。韓愈在《貞曜先生墓志銘》說孟郊“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掏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這哪里是寫詩的風花雪月啊?說實在的,我以為好詩就是抒情,字詞語皆唯美。而“劌”“鉥”“刃”“鉤”“棘”“掏”“擢”,字字像在拿手術刀,叮叮咚咚直響,是不是與一般的詩詞用字太不同?如孟郊的《游終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起句一個“塞”字,給人就有一種奇異的感受,接著“日月石上生”,石上生日月,怎么個生法?一般人是不敢有這種奇特的想象的,而孟郊敢。而且句式上也打破常規,以古文名法入詩,也是一種創新。全詩真是“盤空出險語”(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而且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也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宜昌黎一生低首也”。僅僅一句,就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一生俯首,對孟詩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但孟郊卻是配得上的。
再說冷。孟郊自評自己的詩是“清峭”,清且峭,冷也。蘇軾在評論孟詩時也說過“郊寒島瘦”,寒,冷也。前面說過,孟郊一生在貧困中度過,由是他的詩也是冷色調的,是生活在他詩思中的投影。如《秋夕貧居述懷》:“臥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井不供飲,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是不是有一種蒼涼撲面而來?世態炎涼,人情紙薄,通篇一個“冷”字了得。再如《苦寒吟》:“天寒色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天寒、北風、桑枯、冰厚、冷光……這一組冷色調,是不是構成了一片寒徹骨的冰雪世界?是不是一個“冷”貫穿周身?在孟郊的詩中,這些冷、寒的意象絕不是個別的現象,比比皆是。
最后說澀。《唐才子傳》說孟郊“多傷不遇,年邁家空,思苦奇澀,讀之每令人不歡,如‘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如《謝炭》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獨有夜燭見,一紙鄉書淚滴穿,如《下第》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之類,皆哀怨清切,窮入冥搜”。這幾乎給孟詩下了“澀”的定評。后世的一些評家,大都沒有脫離這個窠臼。像北宋與東坡同時代的詩人王令在《還東野詩》里說,“童子請我愿去燒,此詩苦澀讀不喜”。言之鑿鑿東野詩之苦澀。嚴羽在《滄浪詩話》中也說,“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何為刻苦?除了他的奇、冷外,那就是澀了。縱觀孟郊的眾多詩篇,極少數像“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那樣快意的詩作,而大多與苦澀結緣。如《寒地百姓吟》:“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騷。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搥鐘飲,到曉聞烹炮。寒者愿為蛾,燒死彼華膏。華膏隔仙羅,虛繞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為游遨。游遨者是誰?君子為郁陶。”讀罷,是不是沒有絲毫的輕快和流暢?而滿是蒼涼和苦澀,讓人感到剜心的痛。
澀且苦,是生活的磨難給孟詩的投影。老來喪子,給孟郊的詩更平添了沉重的一筆,一組《杏殤九首》,曾引無數人潸然淚下,“但是洛陽城里客,家傳一本杏殤詩”。如“地上空拾星,枝上不見花。哀哀孤老人,戚戚無子家。豈若沒水鳧,不如拾巢鴉。浪鷇破便飛,風雛裊相夸。芳嬰不復生,向物空悲嗟”。其狀之慘,其情之憐,其命之苦,躍然紙上。
孟郊的言貧詩以及他的詩奇、冷、澀,理致和激憤,歷史上爭議頗多,“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苦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十八》)。雖然偏頗,但如指孟郊詩之苦吟,講求煉字鑄句,窮其一生,只剩得詩歌一事來說,將其作為詩的囚徒,也不為過,竊以為還很形象。正是這種精神,成就了孟郊詩歌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詩囚孟郊,他終將和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佛王維,詩狂賀知章,詩魔白居易,詩鬼李賀,詩豪劉禹錫一樣,永遠懸垂在唐詩的星空里。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責編:王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