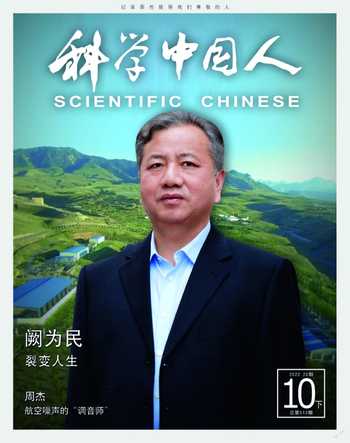爭做中國醫藥創新之“先鋒軍”
周晴晴
“我很開心他有了擴展人工智能的能力用在藥物設計和醫學方面的打算,特別是他想到了使用我的計算方法去嘗試添加新的研究元素,將生物機理和動力學信息引入傳統的藥物設計中去。這個想法目前還沒有被制藥行業使用,我認為它有很大的成功機會……當疫情結束,我一定會親自去我們在杭州的公司,幫助分析、指導動力學和機理上的研究。我衷心祝愿晨佇(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支持它的人都能夠取得巨大成功!”一段來自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里耶·瓦謝爾(Arieh?Warshel)教授的祝言為這個名為“晨佇科技”的“新生”醫藥科技企業帶來了莫大的肯定與發展的自信,其中提到的藥物設計的前沿手段也為我國生物醫藥領域變革謀求了一種新的可能。而“他”這一代稱,指的則是晨佇(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晨佇科技”)創始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生命健康學院助理教授,廣東省珠江青年拔尖人才,深圳市孔雀人才——白晨。即便眾多“標簽”在身,但當走近他時會發現,他是一位純粹的創業者、科研工作者。
晨佇科技的創立絕非偶然或沖動,而是白晨在領域內多年沉淀,深思熟慮而結出的碩果。目前,我國醫藥產業通過數十年的蓬勃生長,已經逐漸從“跟蹤模仿”穩步邁向“原始創新”。在如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于化學領域求學數年、在生物化學結合領域積極實踐的白晨,從“健康中國”戰略指引的前行方向中精準捕捉到了其職業生涯的發展機遇。他決心帶領團隊將藥物靶標的機理、動力學研究創新性地與AI藥物設計相結合,在“晨”光熹微之際,打造出一條全新的AI藥物研發路線。
博觀而約取
與阿里耶·瓦謝爾教授的相遇還要追溯至白晨“初出茅廬”的科研成長時期。在此之前,上海交通大學的求學經歷已經為他在神經網絡算法和計算化學方面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后在美國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University)度過的5年時間更讓他開闊了科研視野,進一步完善了對行業的認知。其間,他不僅在導師朱迪斯·赫茲菲爾德(Judith?Herzfeld)教授的指導下開發出了一種全新的亞原子力場——LEWIS系列第三代,“它使用顯式電子,可比隱式電子更高效地被賦予極化性和反應性”;還成功推動了第一代LEWIS的落地應用,并將其推廣至水合氫離子和氫氧根離子的表面傾向、自電離和電中和的研究之中。
而階段性成功的短暫欣喜遠不足以使白晨停下挑戰自我的步伐,“博士畢業后,我對用計算方法研究復雜生物大分子機器這一課題很感興趣,因此選擇加入了阿里耶·瓦謝爾教授的團隊”。正是這種無懼跳出科研舒適圈的拼搏與努力,讓白晨收獲了這位科學巨匠的高度贊譽:“白晨曾經在南加州大學長期從事我的研究助理工作,在那里,他展示了深刻的思想和對生物醫藥的濃厚興趣。”這也同時為成功邀請諾獎得主擔當晨佇科技的重要支撐力量埋下了伏筆。而白晨自己也在博學精思之后,逐漸開啟了大尺度生物分子機器的多維度建模和計算模擬與藥物開發方面的研究。
2020年11月,白晨正式回國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課題組。“我們課題組致力于對各類重要大分子生物體系開展結構、功能、機理和藥物開發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時以這些機理研究為驅動力,結合人工智能技術,開展創新小分子、大分子藥物研發工作。我希望能夠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實現產業化,又不想‘假手于人,所以在今年注冊成立了晨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創新藥物的研發工作。”這是公司的創立宗旨,也是白晨的科研決心。
厚積而薄發
“機理研究是理解靶點蛋白工作過程以及藥物分子如何影響這個過程的基礎,創新藥物研發是分子機理研究的延伸。”這是白晨奉為圭臬的科研方針,也是其在公司埋首研發時,對合作伙伴常掛在嘴邊的諄諄叮囑。有此感悟,仍是源自其深厚的學術積淀。
白晨發現,如果不搞清楚蛋白活化的機理,則極有可能在制藥過程中導致嚴重錯誤。對此,他解釋道:“傳統的AI藥物設計主要關注提高小分子與靶標蛋白非活性態和(或)活性態這兩個穩定狀態的親合力繼而對以此為AI模型的核心數據進行訓練,而忽略了藥物分子對過渡態能量及能壘的影響。這樣的后果就是,蛋白的活化工作過程就是一個‘黑盒子,而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錯誤。”但礙于科技的發展水平,過去人們疏于注意這一點實為“情有可原”。
首先,對蛋白質過渡態的捕捉和機理研究都非常難。過渡態構象在實驗層面是無法獲得的,其存在時間往往只有幾到幾十飛秒(10-15秒),業內普遍采用的XRD和cryo-EM技術來不及對其進行捕捉。此外,在計算模擬方面,一個靶點蛋白一般包含幾萬個氨基酸原子,在如此大的自由度下進行構象從非活化到活化態的轉化和采樣,無疑是為科研人員提出了巨大挑戰。最后,如何將伴隨構象轉化過程的物理、化學事件(例如ATP水解、ADP解離等)與構象變化耦合起來得到完整的工作路徑,又是一個令學界冥思苦想的難題。“無論何種研究,其得到的結果必須經得起同行評議的檢驗和推敲,并且理論預測的結果要能和實驗符合。能把這件事做好,絕非易事。”白晨補充道。
“要攻克這些關卡,機理研究就需要和AI技術相結合。”在本質上,藥物分子設計是要去探索一個化學空間,找到有藥效的分子。但因為藥物分子的化學空間過于龐大(約為1060),相當于宇宙中所有原子的總和,所以只有使用AI技術才能夠充分探索。那么,訓練數據的好壞就成了影響人工智能模型性能的決定性因素。確定這一點后,白晨率領團隊創新性地引入了分子對靶標蛋白機理影響的動力學信息,通過這些數據提高了AI訓練的“天花板”。“對此我可以自信地說,晨佇科技目前是世界范圍內第一家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的藥物研發公司。”白晨堅定道。
另外,據白晨透露,這一科研思維已經得到了眾多行業專家的認可。他們不僅在公司內部構建了志同道合的創業團隊,除瓦謝爾教授外,還吸納了許多教授級科研人才。在他們的支持下,晨佇科技聚力打造了一個從靶點發現,靶標蛋白出發,經歷機理研究、AI藥物(大分子、小分子、偶聯藥物)設計,從而得到先導化合物,進行實驗檢測的創新藥物研發平臺,并在此基礎上開啟了多條研發管線。“我們選擇的靶標蛋白類型豐富且極具代表性,目前包括了酶、離子通道、G蛋白偶聯受體等,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藥物靶點。其中,進展最快的管線已經完成了前期的藥物分子設計,即將進入分子合成及臨床前生化實驗驗證階段。”這意味著,晨佇科技的第一個化合物可能不日產出。
雖然鋒芒初現,但一款創新藥物從研發到成功上市,絕對是一個長期且持續的攻關過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因此更需要業內多家公司、眾多有識之士的勠力同心、通力合作。白晨也深諳此理,他說:“晨佇科技將始終堅持以創新為本,專注于整個流程最前期的藥物發現階段,致力于為業內提供更可靠的先導化合物,做好原創醫藥的‘先鋒軍,然后再不斷提高自身的研發實力,向更重要、更難的藥物靶點發起沖鋒。只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我和我背后的團隊能夠和業內同仁一起推動國內原研藥的成功,為更多人的健康事業保駕護航。”
(責編:關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