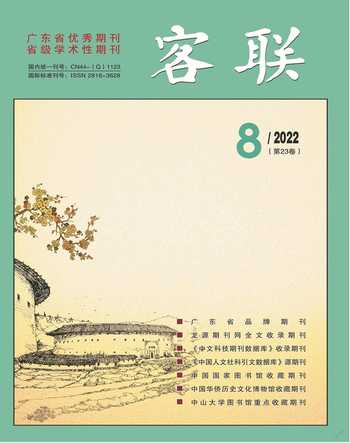澳門刑法中的必然故意
林磊鑫
摘 要:澳門刑法對于犯罪故意的分類不同于我國內地刑法犯罪故意的分類。內地刑法將犯罪故意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兩種故意模式,而澳門刑法則將犯罪故意分為三種,即直接故意,必然故意與或然故意。學界中對于必然故意的規定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內地刑法中也有必要引入必然故意的概念,區分明知危害結果必然會發生而積極追求的直接故意與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而消極地接受,以此來區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的不同。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明知危害結果會發生對這一結果所持心理態度就不可能是消極地放任其發生,只能是積極追求的心態,因此必然故意實則就是直接故意。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內地的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理論下,必然故意無法被涵蓋在現有的兩種故意類型中,因此必然故意實際上是第三種故意形態。本文通過厘清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中犯罪故意的異同,討論必然故意究竟是屬于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的一種類型,還是屬于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中的第三種故意形態。
關鍵詞: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必然故意;放任
比較內地與澳門的刑法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地皆承認明知行為必然或可能會造成危害結果,積極追求結果發生的是直接故意;對于行為人明知行為可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對這一結果的發生持消極放任的心理態度在內地被劃分為間接故意,在澳門的規定中是或然故意;對于明知行為必然會造成危害結果,且放任結果發生的這一心理態度在澳門是必然故意,而在內地刑法中并沒有明確劃分,學界仍然有不同的聲音。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刑法學界對于“明知必然發生而放任”這一故意的不同觀點進行梳理和總結。
一、不同學說之比較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學界一致認為“明知必然發生而放任”是一種故意而不可能是過失,因為過失犯罪要求行為人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發生是排斥的,是違背了行為人的意志的。而“放任”的心態即意味著行為人對結果持的是一種可發生可不發生的心理,結果發生了并不違背行為人的意志,這里與過失有明確的不同。因此內地刑法學界對于“明知必然而放任”主要的討論是這一心理態度究竟是屬于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還是一種介于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中的第三種故意形態。
(一)直接故意
內地主流學說認為必然故意也就是直接故意,在這其中不同的刑法學者因為解釋的理由不同又可以分為兩種學派。
1、認識和意志相互影響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不存在“明知必然且放任”的心理態度。因為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并不是獨立存在的,意志因素以認識因素為前提,反過來,意志因素的內容又限制認識因素的內容。這就意味著持“放任”意志的行為人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僅僅只會認識到其可能性而不可能認識到必然性。因此這類學者認為在“明知必然”時,不可能存在“放任”的心理狀態。
2、不影響結果發生
另外一類學者認為必然故意持有的是放任的心理狀態,但這種放任并不會對危害結果的發生造成什么影響。因為結果必然會發生,所以行為人主觀上是“放任”還是“希望”并沒有什么差別,都屬于直接故意的范疇。我們可以從中推斷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只要是行為人認識到結果必然發生即是直接故意,也就是說,這類學者認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別在于認識因素,而意志因素方面是積極地追求還是消極地放任對故意的分類并無影響。
(二)間接故意
支持必然故意可以歸類為間接故意的學者們認為區分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的標準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所持心態是積極希望還是消極放任。這類學者指出中國內地刑法條文中 “希望”和“放任”才是區別兩種犯罪故意的標準。而在認識因素層面,對于行為人只需要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結果即可,無論這種結果的發生是可能的還是必然的都不會影響行為人是故意的認定。
(三)第三種故意
還有一些學者另辟蹊徑,他們認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是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雙重標準共同決定,將“明知必然且放任”的心理狀態歸入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都不能很好地進行解釋,那么就開辟一種新的故意模式,將這種介于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間的故意獨立出來,即澳門刑法里的“必然故意”也有學者稱為“容忍故意”或“準直接故意”。這類學者認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間應當有第三種形態的故意,這種故意的主觀惡性大于間接故意但小于直接故意,如此區分有利于法官在實踐中更加準確地量刑,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二、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之獨立性
前文提到一部分將必然故意歸類為直接故意的學者認為故意的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直接會相互影響,聯系緊密。在這一部分,筆者將分別討論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獨立性,對這類學者的觀點進行反駁。
(一)認識因素
必然故意的認識因素的具體內容是“明知必然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必然”是指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一種客觀規律,而刑法犯罪故意中的“必然”有別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指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概率為百分之百,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的相同點是二者都是客觀事實。“明知必然”是一種心理狀態,就是指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概率為百分之百這一客觀事實的心理狀態。很顯然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發生概率的認識只與行為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本身有關。認為意志制約認識的學者忽視了認識因素的獨立性,將“放任”推定為明知危害結果可能發生并不符合邏輯。
(二)意志因素
必然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放任”,澳門刑法中的用詞是“接受”。無論是“放任”、“接受”、還是有些學者說的“容許”,都是指行為人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發生不排斥也不追求,的一種心理態度。意志是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之所以會被刑法評價為罪過,受到刑法責難的主要因素。 “放任”雖然沒有積極破壞法律,但也表現了行為人對法律秩序的冷漠。那么違反法律的事實一旦發生,行為人這種對法律秩序的冷漠也需要被刑法譴責。
(三)獨立性
筆者并不否認甚至十分贊成如張明楷教授所說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但也必須承認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有其獨立性,而不是時時刻刻都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比如張三與李四有仇,看到李四在獨木橋上,便想要砍斷獨木橋,此時橋上還有無辜的王五。明知砍斷獨木橋必然會導致王五和李四死亡的結果,但張三出于仇恨,不顧王五的死活,砍斷了獨木橋,導致王五和李四的死亡結果。若我們只看到了認識與意志具有關聯性,那么此時張三明知王五會死,對王五所持心理態度就不會是“放任”,而是“希望”,張三對于王五的死亡結果的主觀惡性和對李四的死亡結果的主觀惡性一樣大。作為社會一般人角度來看,也會覺得這并不合理。這恰恰說明了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之間有一定的獨立性,“明知必然”和“放任”這兩種心理事實可以同時存在,那么“明知必然而放任”這一心理到底該如何評價呢?。
三、必然故意與直接故意、間接故意之關系
要評價必然故意首先必須明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區分標準。目前學界主要的討論是“意志說”與“雙重標準說”。
(一)意志說
支持“意志說”的學者認為意志是決定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之間主觀惡性不同的關鍵。因此這類學者將“明知必然而放任”歸類到間接故意范疇下的一種類型,他們認為澳門刑法中將間接故意細分為了必然故意和或然故意。但目前理論界的通說認為間接故意必須發生了一定的后果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否則就不能對行為人進行定罪。因為在間接故意的情形下結果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如果行為人中途停止行為,危害結果沒有發生,那么處罰這種行為就沒有可操作性。對于前文中張三殺死李四與王五的案子,如果張三出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了犯罪行為,他對于李四的直接故意還需要處罰未遂,而他對于王五的行為是不是就無法定罪了呢?筆者認為張三對于王五的生命法益也造成了直接危險,因此不能按照間接故意理論認為其對王五不構成犯罪。
(二)雙重標準說
另外一部分學者認為簡單地以“認識因素”或“意志因素”之一為標準劃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都是不全面的,他們認為兩種故意的區分是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共同決定。這也是目前犯罪故意的分類標準的主流理論。此時的直接故意在認識因素上應當認識到危害社會的結果有發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在意志因素上是積極希望結果發生。間接故意在認識因素上僅僅認識到了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意志因素是放任結果發生。筆者支持雙重標準說。那么根據這種分類標準,無論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都無法囊括“明知必然而放任”的故意類型,因此必然故意就成為了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中間形態。
四、犯罪故意之再思考
前面我們討論了必然故意無法被囊括在目前中國內地對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劃分理論中,討論了澳門刑法典中區分三種故意的歷史原因和立法原因,那么是否意味著我國也可以引進第三種故意的理論?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澳門刑法典雖然規定了必然故意的內容,但經過筆者搜索澳門刑法的判決中并未發現直接明確地評價為必然故意的案例,往往以“至少為必然故意”這樣的形式不與直接故意進行區分,或者是在法官斷定行為人認識到犯罪結果“極有可能”發生時也認定為是或然故意。可以看出實踐中必然故意的可操作空間較小,引入必然故意這個概念的意義不大。其次,實際上不同的故意之間雖有區別,但并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換言之,應當注重不同故意類型之間的統一性,只要認定了行為人有犯罪故意,并且區分過失,就能對行為人準確定罪,而對他主觀上有無認識到結果發生的必然性,有無“放任”或“希望”這可以由法官在量刑中酌定,無需將這種司法事實判斷置換成立法推定。最后,相較于引入一個作用不大的法律概念,刑法作為調整公民行為的、涉及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等權益的社會規范,保持其相對穩定性有更重要的意義。
既然我國內地的法律沒有必要引入一個新的犯罪故意的模式,那么該如何解決某些案件中存在“明知必然而放任”的情況呢?首先,立法上不需要單獨規定必然故意的內容,但理論上我們仍然可以對故意理論進行討論研究,豐富犯罪故意的內涵。在理論上可以擴大直接故意的范疇,將“明知必然而放任”納入直接故意的內涵之中,并參照德國刑法典,將“明知且希望”作為一級直接故意,將“明知必然而放任”作為主觀惡性低于“明知且希望”的二級故意。同時,實踐中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必須明確還有一種主觀惡性低于直接故意,而高于間接故意的第三種故意類型。在司法實踐中考察犯罪人主觀方面的時候,法官需要更細致地進行定罪量刑,對持不同故意程度的犯罪人“區別對待”,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
五、總結
筆者認為對于我國內地刑法來說,引入一個新的故意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刑法犯罪故意理論的逐步豐富與發展。因此筆者的觀點是:因為“明知必然而放任”這一故意心態對于法益有了直接的危險性,在內容上更貼近直接故意,因此可以將其解釋為直接故意的一種特殊類型,納入目前內地犯罪故意理論中直接故意的范疇,但必須注意與直接故意中的“明知且希望”這一故意類型相區分。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賈? 宇:《罪與刑的思辨》,法律出版社。
3.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5.姜? 偉:《論間接故意》,《煙臺大學學報》,1995年第8期。
6.楊? 波、王元建:《準直接故意的生命空間——論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中間形態》,《湖南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7.張? 彥:《對“明知必然發生而放任”的思考》,《經濟視角》,2011年第1 期。
8.李曉蘭:《簡述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中間形態》,《法制與經濟》,2012年第3期。
9.楊? 紅:《對直接故意特殊形態的探究》,《東方論壇》,2003年第5期。
10.周一心:《對必然性間接故意之否定》,《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11.林亞剛:《對“明知必然發生而放任發生”的再認識》,《法學評論(雙月刊)》,1995年第2期。
12.王雨田:《明知必然發生能否放任?》,《中國刑事法雜志》,2004年第4期。
13.趙秉志:《論澳門刑法典中犯罪構成規范的完善》,《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9期。
14.趙國強:《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故意犯罪階段形態之比較研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2期
15.馮? 濤:《犯罪故意基本理論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16.朱志闖:《犯罪故意意志因素比較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