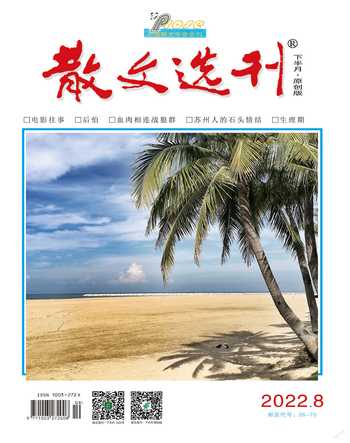后怕
馮積岐

這是2002年春天里的事。
那天,因搭錯(cuò)了車,才到了東新街。下了車,去找702路的站牌子,抬眼一看,馬路東面圍了許多人,耳朵里鉆進(jìn)去的是刀刃一般的叫聲,出于好奇,就圍過去了。撥開里三層外三層的人群,到跟前去看,叫聲發(fā)自躺在地上翻滾著的一個(gè)人的口腔。他的頭被上身的灰色夾克服罩著,不見面目。從不斷喊叫的聲音和毫無款式的姿勢(shì)上看,年齡在三十四五歲左右,不知是什么時(shí)候開打的,我目擊的只是打人的一個(gè)片段。一個(gè)四十左右的男子掄起小圓凳子的鐵腿在躺在地上的男人身上毫無節(jié)奏地亂捶。凳子的座面已被打飛,躺在被打者的身旁。還有一張凳子的座面和失去體面的凳子腿亂七八糟地撂在被打者的身旁。我估計(jì),這張凳子也是招架不住人的肉體而被打得魂飛魄散了。可見,那具活生生的肉體是很能挨得起人的擊打的。那個(gè)掄著凳子腿的男人氣喘吁吁,站在他旁邊的一個(gè)瘦高個(gè)子可能是他的同伙,不時(shí)地用腳在地上的男人身上亂踢。凳子腿擊打肉體的聲音越來越燦爛,而人的喊叫聲越來越蒼白了。周圍圍著的大約一百號(hào)男人和女人都屏聲斂氣似的,悄無聲息。這鏡頭,比影視劇中施暴的場(chǎng)面真實(shí)得多,可怖得多,殘酷得多。我再也無法忍受了,當(dāng)那男人舉起凳子腿要向被打者的頭上猛擊過去的那一刻,我抓住了他的胳膊,那男人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他將舉在空中的凳子腿慢慢地落下來,然后,撂在了地下。這時(shí)候,有兩三個(gè)女人走過來,勸那男人不要再打了。兩個(gè)男人拍拍手,罵罵咧咧地走了。我連一眼也沒再看躺在地上微弱地呻吟著的被打者,急忙去趕車了。
坐在車上,我只是想,那男人為什么在我攔住他以后,不再打了?他是不是把我當(dāng)作了派出所的便衣?抑或是,他打的程度恰到好處,我一攔,正符合了他的意愿。有一點(diǎn),我是明白的,人家絕不是怕我。我沒有任何威懾人的氣質(zhì),也沒有使人懼怕的外貌和年齡優(yōu)勢(shì)。因?yàn)樗麤]有打下去,被打者的頭顱才保住了,不然,那狠狠的一擊,他的腦袋非被打成米飯不可。說實(shí)話,我沒有見義勇為的崇高想法,我只是覺得憤慨,覺得殘忍,覺得憎恨,覺得人對(duì)同類不能施以暴力。于是,就上前去毫不猶豫地?cái)r住了一個(gè)施暴者。
回到家,妻問我為什么回來得這么晚。我將在途中發(fā)生的事情給她敘說了一遍。妻聽罷,嚇得臉色蒼白了。她說,如果那個(gè)人把鐵腿掄過來,蓋頭朝你打下去,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了。我一想,不是沒有這種可能。因?yàn)槭┍┱吣艽驂膬蓚€(gè)凳子,足以說明,他已失去了理智,或者說,他是一個(gè)生性十分殘忍的人,一個(gè)嗜血如命的人,一個(gè)亡命之徒。面對(duì)這樣的人,我不后怕才算是怪事。
我將同情、憐憫、善心、愛心以及人的尊嚴(yán)作為做人的底線,因此,也就極力去這樣做。可是,現(xiàn)實(shí)生活迫使我不得不承認(rèn),人的良知良能、人的尊嚴(yán)和自尊隨時(shí)有失去的可能。要保證人的尊貴性不喪失必須有一個(gè)最起碼的支撐,這就是社會(huì)氛圍和社會(huì)環(huán)境。這樣的氛圍和環(huán)境,僅僅靠老百姓去創(chuàng)造是不行的。因此,我不能說,面對(duì)施暴者,那些圍觀的人就麻木不仁了,也許,他們的心也在狂跳,熱血也在沸騰,理智告訴他們,不能去“見義勇為”。也許,那一板凳腿下去,由于一時(shí)的沖動(dòng),一個(gè)好端端的家庭將失去一個(gè)好丈夫或好父親。他們不明不白地倒下去未必能有好報(bào),我們的媒體披露的這樣的事情還少嗎?一些見義勇為者被被救者反咬一口的事例也曾見于報(bào)端。我想,沒有出面阻攔的這些人大概是“前怕”吧。
其實(shí),“后怕”和“前怕”的心理狀態(tài)是一樣的。我祈求的是,我們當(dāng)中的每一個(gè),什么時(shí)候能活到既不“前怕”又不“后怕”的份兒上,那就好了。面對(duì)暴力,面對(duì)威懾,面對(duì)一切不公正,能夠大義凜然,一身正氣,有幾分英雄氣概,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就能純凈一些,寬松一些。
美術(shù)插圖:曲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