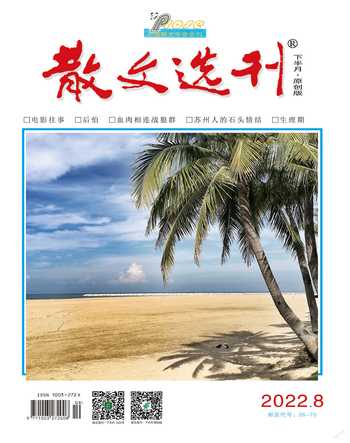半個月亮在燃燒
楊立英

月亮爬上樹梢時,父親倒下了。
83歲的父親,骨質疏松、房顫、冠心病,預示著各路零件都在老化。骨科手術就像木工活,鑿、鋸、鉗子、錘子、螺絲、釘子……樣樣都不少。卸下斷裂的股骨頭,換上人工股骨頭,手術不復雜,對父親孱弱的身體來說仍是個不小的考驗。父親說:“只要能走,多大的罪我也能受。”
為父親請來省醫院的專家,手術很順利,醫生輕描淡寫地叮囑:“兩天練坐,五天練站,一周練走,爭取一個月扔掉拐杖。”我把醫生的話加大分貝翻譯給父親,父親連連點頭。
半個月是時間,也是希望,父親咬著牙堅持鍛煉。那些被疼痛喚醒的汗珠子紛紛鉆出來,大滴大滴地滾落下來,把我的心浸軟了。“咱歇歇吧,先不練了!”我加大分貝的話語仿如被空氣隔絕,父親理都沒理,緊緊地抓住床欄移動著笨拙的傷腿。父親想要做的事,十頭牛也難阻攔,真猜不透他瘦弱的軀體內,究竟藏有多大的能量。
記得我八九歲時,黃河發大水把我家的房屋沖塌了,重新劃分的宅基地位于黃河大壩以北,坑坑洼洼的有一米多深,只填土一項就耗盡了家里可憐的積蓄,三間土坯屋蓋好后,天井窄得只有一步之距。母親說:“再借點錢,雇人墊墊天井吧。”父親一言未發,貧窮讓他選擇了出賣自己的氣力。周末休息,父親買來兩個大柳條簍子,借上小推車,他要自己推土墊天井。以父親瘦弱的身板,身高不足一米六七,體重一百來斤,又沒經歷過重活的磨煉,別說推土墊天井,就是一擔水也會壓得搖搖晃晃,母親嘴角一下撇到了耳梢,一副不屑的表情。鄰居大申哥推著兩大筐土,看起來玩一樣輕松,父親卻把那些行云流水的動作,分解成了一個個滑稽的慢鏡頭。沉重的車襻掛在脖子上,壓得他抬不起頭。車頭前端兩根拉車的繩子,一根掛在我肩頭,一根掛在姐的肩頭。那情景,似乎不是父親在推車,而是我和姐拖著車和父親在走。到了陡坡處,父親先用力頂住車子,深吸兩口氣,然后把脊背彎成弓,用盡全身氣力蹬著地往前拱,有時我們爺仨的力量都抵不住后退的車輪。那時,我最怕過周末,最怕父親回家。這樣的日子,從我上小學二年級,一直持續到我初中畢業。那時上語文課讀到《愚公移山》一文,我真希望天帝知道我家的事,也派兩個力大無窮的神仙,幫助我家把天井用土填平,讓父親這一宏大的工程快些畫上句號。
四十年后,父親再次發揮了他的犟勁,白天不停歇,晚上披星戴月練,躺在床上掛吊瓶還不忘晃動搖擺腳趾頭。做陪練的日子,父親把手臂搭在我肩背,雖是他在走,身子一半的重量卻壓在我身上。這一場景重疊著記憶中父女一起推土的畫面,心底便會叢叢簇簇地生長出許多的感慨與溫暖。
父親生日那天,恰好手術后一百天,是個月圓的日子。那天,父親真的扔了拐杖,用力擺動著雙臂,像兩個劃動的槳,劃著歲月的希望和痛,一步一步。這對一個體弱多病的老人來說,是多么的不容易。父親興奮地說:“以后你們都安心上班,不用老往家跑了,我自己行了。”
歡喜的心情還沒來得及收藏,父親又出現了第二次骨折。那天說起來有些詭異,明晃晃的太陽,一下被大朵烏云裹藏起來,天色變得陰沉沉的。父親吃完早飯坐在桌子旁喝茶,母親去拿搭在椅子上的衣服,就那么輕輕一拽,父親如一片弱不禁風的樹葉,歪歪斜斜地從椅子上滑落到了地上,父親的右側股骨頭也摔斷了。他無奈地躺在床上,一言不發,用擔憂的目光追逐著我們的表情,猜測我們在說什么。我趴在他耳邊大聲問:“還愿意做手術嗎?”說實話,這句話我問得很矛盾,既希望父親說做,又擔心他承受不住再次重創。最終,父親給了我希望的答案:“做手術!”
父親的信任和堅持,讓一家人在前行的路上,一直不敢輕言放棄。
經歷過再次骨折和手術重創,我斷定父親很難再自己行走了。即使這樣,我的父親至少還能坐,不至于天天躺在床上數天花板。父親卻又一次發揮了他的犟勁,天天要求我和弟弟架著他鍛煉。“再有半個月,我就差不多好了。”父親的這句話,像一句夢語,我猜不透他是在給自己打氣還是在給我們希望。到了半個月,他似乎像個不識數的孩子,又會重新計算時長。以父親的聰明,他哪會忘記呢?躺在床上的父親,時常在漆黑的夜里盯著窗外的月亮發呆。他是在一個又一個的半月里,在燃燒和煎熬中,等待奇跡。
歷經無數個暮暮朝朝、月圓月缺,父親扶著助行器真的又能走了。他挪步至陽臺,皎潔的月色把夜空清洗得遙遠而透明,月光灑在身上,我感嘆月色的美麗,也敬佩父親的毅力。不服輸的父親又能自己如廁,自己穿衣脫衣了,每次我回家,父親都要展示一下他鍛煉的成果。他爬樓梯的樣子像極了拽著繩索在懸崖峭壁上的攀巖者,整個身體的重量幾乎都壓到了瘦弱的手臂上。時日一長,樓梯扶手被父親拽扶得顯出一層油亮的光。終于,父親扔掉助行器,能走了。
但一夜之間,命運再次和父親開了個大玩笑:肌肉僵直,皮雖連著,大腦卻無法指揮,父親的腦神經又出了問題,這次真的不能走了。我把父親扶起來,他整個身子直愣愣的,無法彎曲。以前父親推土時,我多希望他的腰板是挺直的,如今父親僵直的腰板,卻無法讓他坐和走。
不能動的父親有時糊涂,有時清醒。“我再有半個月就好了!”父親說這句話時,涎水滴落出很長。我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喊:“爸!”他條件反射般的開始鍛煉,把手指伸開,合上,這是他唯一能完成的肢體運動了。
半個月,是父親的堅持,也是父親的希望。而我更喜歡看這一字面的意思,它讓我想到的不僅僅是時間,還有月亮的圓缺。再有半個月,那不就是一個圓滿的月了嗎?
我多希望真的可以創造出一個奇跡的滿月!可我再也尋找不到了,因為我的眼睛開始模糊,淚水遮住了視線。
責任編輯:青芒果
美術插圖:吳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