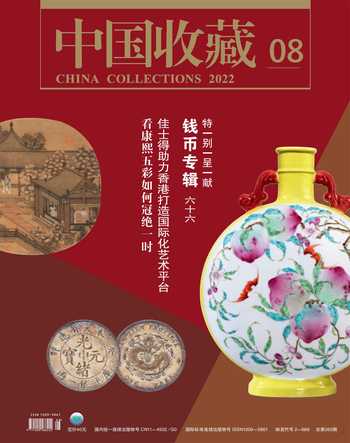稀有“崇禎四手”展露云南貨幣史變遷
羅維巍

云南貝幣,其源自自然界產物海貝,俗稱“貝子”。
海貝俗稱“貝子”,是一種自然界產物,我國歷史上商、周兩代都曾將它作為貨幣使用。云南的用貝歷史可追溯至戰國末年。公元前3世紀,作為楚莊王之苗裔,莊蹻在滇地稱王,建立滇國,此時海貝已經作為中介物進入交換市場。秦統一中國后統一幣制,外圓內方半兩錢大行天下,但云南并未推行秦朝歷法、度量衡、貨幣等,仍然使用天然貝幣,此后延續了近2000年時間。直至“崇禎四手”錢的出現,成為了一個鮮明的時代烙印,對后世研究中國古代貨幣體系及云南明末社會經濟變遷與政策推行,有著重要意義。
貝幣:曾經盛極一時
云南海貝貨幣在歷朝文獻資料中屢見不鮮。最早有《新唐書·南詔傳》載:“以繒帛及貝交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覓。”宋代政和《證類本草·海藥》也注有:“貝子,云南極多,用為錢貨交易。”明代萬歷末年,云南參政謝肇淛則在《滇略·俗略》中提到:“海內貿易皆用銀錢,而滇中獨用貝。貝又用小者,產于閩廣。近則老撾等海中不云南貝幣,其源自自然界產物海貝,俗稱“貝子”。遠數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日‘貝巴。其用以一枚為一莊,四莊為一手,四手為一緡,亦謂之苗。五緡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僅值銀六厘耳。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其民便之。”
元明時期云南貝幣流通可謂盛極一時,民間交易借貸、官府征收租賦商稅、官吏俸給、土司納貢等都使用海貝。如《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十三年正月丁亥,云南貿易與中州不同,鈔法實所未諳,莫若以交會,巴子公私通行,庶為民便。并從之。”“至元十九年九月己巳,定云南賦稅,用金為則,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還有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戶部奏明:“云南俸米兼收海‘貝巴,舊時每石折海‘貝巴七十索,今米貴,宜增三十索”。
到明萬歷末年至天啟、崇禎時期,貝幣開始進入衰落階段。康熙《云南通志》記載:“至明啟、禎間,貴銀錢,‘貝巴遂滯不行。本朝錢法疏通,民稱便宜,久不用貝。”可見,云南海貝在明末清初已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廢貝行錢:多重原因導致
至于云南“廢貝行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以金屬鑄幣的銅錢取代微賤的海貝貨幣合情合理。作為西南邊疆地區,云南歷史上長期受羈縻之治,政策有異于中原內地。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南后,政區上實行內外分野,“外夷”同“直隸”劃分管理。
萬歷年間,云南巡撫周嘉謨認識到西南邊政是“全滇藩籬”“中國藩籬”,認為“宣慰之官,豈容虛位”,故以“國朝編制宣慰、宣撫、長官、安撫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級”,加強中央集權的管理。與此同時,大量漢人入滇,帶來了諸多新興事物。據云南方志記載:明代中晚期,云南出現了許多商品交換的市鎮。昆明、大理等大城鎮“百貨匯聚,人煙輳集”,貿易頻繁;一些較小的府、州、縣治所,有定期集市,本地和外地商人運來各種商品,貿易活躍。
二是政府強力推行提高銀價,壓低貝幣價值。明中葉后,白銀使用普遍。盡管白銀在內地“朝野皆用”,但在云南只是用來折納租稅或發放官俸,流通有限。政府要加大云南與內地經濟的互通往來,規范財政收支,就需要推動白銀在經濟中的地位提升。
一方面,明朝后期,政府持續提高銀價,壓低貝幣價值。據云南方志記載:至元十九年,大理地區一兩銀子值貝三十三索;明初值貝一百索,嘉靖十九年值貝五十索,萬歷末年值貝一百六十六索,天啟年間至二百二十四索……海貝貶值速度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在白銀還不能大量引入市場流通的情況下,銅錢作為介于海貝與白銀之間的一種小額單位貨幣,更適合云南市場的交換需要。再者,對于經營礦業生產的礦頭、販運轉賣金屬產品的商人,以及廣大手工業生產者來講,銅錢都是更適合的等價中介物,滿足了他們日常小額的交易與供給需求,因此特別受歡迎。
三是礦冶業、鑄造業在云南的日益發展成熟。云南銅礦的采冶由來已久。明中葉以后,官營銅礦日趨沒落,而國家對銅的需求量又與日俱增,明政府只能放寬禁令,允許民間采銅。明嘉靖、萬歷年間,政府為了廉價買銅,“屢開云南諸處銅場”,長期以來被封閉的銅礦由私人紛紛開采起來。當時礦山雖屬國家,但產品僅四分之一歸官府礦課,四分之一歸生產工人,四分之二歸硐頭(即礦頭)。這種高利潤買賣自然也吸引了眾多商人,云南豐富的銅產品經由商人銷售于省內外,甚至形成了貴州思南和四川涪陵兩大“商販銅、鉛畢集”的集散地。

圖1、圖2為天啟單點通云版光背(正、背面),圖3、圖4為崇禎單點通云版光背小平錢(正、背面),它們均為云南地區常見且風格相同的錢。此類制錢應為云南直隸省府的主要鑄錢。
而政府為了造錢,也向民營銅礦場買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四十四年(1565年),云南開局鑄錢,政府用鹽課銀2萬兩收購銅、錫,額派造錢3301萬2000文;萬歷四年(1576年)至八年(1580年),政府在云南重開造錢,“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一時“銅價騰躍”。天啟六年(1626年),以巡撫閔洪學為首的官吏湊集六千兩白銀購買銅、錫原料,造錢600萬文,并在《條答錢法疏》中稱:“滇中鑄錢,不患無子(原料),而患無母(經費)。不患無銅,而患無匠”,此次制錢發放與民,成效勝過以往。
關于貝幣的缺點,明代謝肇淛曾在《滇略》中提出:“海貝其數多,既不勝荷挈,而又易于破壞,緣其值甚輕,故亦不惜。”到了明朝末年,云南的“廢貝行錢”已乃大勢所趨。而正是在這關鍵的歷史節點,“崇禎四手”錢適時登上歷史舞臺,助推了歷史進程。
“崇禎四手”:意義重大的發現
就錢文不難解釋,“四手”為折貝或記值,即“崇禎四手”的一文制錢相當于16枚海貝。
關于此錢的出處,我們不妨來綜合判定。目前可以確定為云南制錢的有天啟背云,其存世量大、最為常見。比較云南地區常見的、相同風格的天啟單點通云版光背與崇禎單點通云版光背,無論材質、文字還是鑄造風格,皆系一脈相傳,這類版式與京師北直中央制錢也不盡相似,屬于依中央京版演化而得,故可將這類制錢歸為云南直隸省府的主要鑄錢。
根據抽樣分析,云版崇禎錢為一錢重(即3.7克至3.8克)左右的小平一文錢制式。而“崇禎四手”錢,雖直徑規格較大,但材質、文字、形制、工藝風格等特征,均與云版崇禎小平錢相符,屬于一個體系,即云南直隸省府所轄鑄錢局所出。
“崇禎四手”錢存世極罕,迄今為止,公開已知的實物僅有5枚,其中1枚母錢,4枚子錢均屬樣錢,且皆為傳世熟舊之品。其中的版式也可分兩種:一種叫降手版,錢徑約2.8厘米,重約3.3克(流通磨損較重),現藏于上海博物館,也是舊譜資料原物,舊時曾被誤讀為“舊平”;另一種叫昂手版,目前總共發現4枚。關于昂手版,筆者收藏有1枚母錢與1枚子錢,母錢直徑約為2.85厘米至2.88厘米、重5.08克,子錢直徑約為2.74厘米至2.76厘米、重4.33克。另外2枚子錢則分別由國內藏家與海外藏家收藏,直徑均在2.75厘米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手中的這枚母錢為近年于云南宜良地區發現,即舊時云南省府轄地。此錢與3枚同版子錢有著明顯的同模印記特征,可見之間的直接關聯。這枚母錢砂型細膩、工藝精湛,應屬雕母直接翻鑄的一級鑄母,即原母,雕母為軟材(如鉛錫類)的可能性大。筆者分析,這枚母錢極有可能就是鑄造這3枚子錢批次的直接母錢,出自云南,再度佐證了“崇禎四手”錢為云南鑄錢,意義重大。

明末京師北直中央制錢

降手版“崇禎四手”錢上海博物館藏
云南制錢:水準穩定鮮有私劣
據《續文獻通考·錢幣考五》記載,天啟七年十二月:“戶工二部進崇禎新錢式,帝令每錢一文重一錢三分,務令寶色精采,不必刊戶工字樣。”侯恂《鼓鑄事宜》又道:“崇禎元年從錢法侍郎孫君相識,每文改為重一錢二分五厘,體質堅厚,磨镕莫拖,人情便之。”這是京師北直地區即中央制錢標準。筆者曾抽樣實測,顯示4.6克左右的重量與所載相符。
崇禎三年(1630年),除京師北直地區保持一錢二分五厘制式之外,其余地區多為一錢制,南錢(包括南直、湖廣部分等地)為八分。相較其他地區,不考慮鑄造工藝的個體差異,云南崇禎制錢的品種與版式相對單一,且鮮有惡錢。作為主要銅產地,天啟五年(1625年)開始在云南推行的第三次行鑄錢事,至崇禎朝幾乎未有中斷。明末畢自嚴《度支奏議》中多次提及云南省鑄錢,表示省府未停,四年又開新局,所出錢息充做新餉。由此可知,云南地區的崇禎制錢水準是相對穩定的。
事實上,當時政府規定的銀錢折兌,在民間實際交易時往往有所差異。比如崇禎初年,政府規定五十五文當銀一錢,民間交易卻常以六十五文至七十文折算。到了后期,由于私濫混雜、社會動蕩、物價上揚等原因,銅錢貶值嚴重。直至明末,京錢百文值銀五分、外省錢(也叫皮錢)百文則值銀四分。
而且明末私錢名目繁多,天啟時有寬邊、大版、金燈,崇禎初有胖頭、歪脖、尖腳等,私鑄盜鑄猖獗的現象也充斥了制錢領域,直接導致市場上銅錢的加劇貶值。根據現有實物,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明末劣質小錢,特別是南直、湖廣、四川等地的版式,質地濫惡、極其輕薄,更有甚者重量僅零點幾克一枚,這也難怪為何當時甚至出現了百姓拒絕使用崇禎錢的情況。但私劣情形在云南制錢中卻鮮有發現。
推測:為“惠民”而出現
有了制錢標準,結合銀錢、銀貝比價關系與“廢貝行錢”原因,筆者得出以下分析與結論。
以一錢制一文銅錢為例。崇禎初時,一錢銀子最多折兌銅錢百文;而天啟年間,一兩銀子可折兌海貝二百二十四索,即17920枚(理論上該數據崇禎時期更高),由此換算,崇禎年間一文銅錢至少可折兌18枚以上的海貝。若以一錢三分或一錢二分五厘的京錢標準計算,五十五文至七十文折銀一錢,則可折兌的海貝數量更多。
所以,比一錢制標準更高的“崇禎四手”錢,其實際價值已高出可折兌的海貝價值,即理論上說,制“崇禎四手”錢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對當時百姓而言,用海貝兌換“崇禎四手”錢屬于“超值買賣”,而對政府卻是“折本生意”。但為何此錢卻出現了?雖缺乏直接的史料解答,我們仍可通過現有資料進行分析。
關于天啟六年鑄錢,《滇志》有載:“成錢七十余萬文,業于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矣。錢之將行,市間尚噴噴偶語,臣等酌行錢便益,條為十一款,刊布簡明告示,又編為歌謠,誘導愚俗。七月之朝,則集省城官吏、師生、鄉約、木鐸人等而申告之日:錢非他,乃‘天啟通寶也。滇雖荒服,同廩正朔,寧敢獨處化外!眾皆唯唯……半月來,持銀換錢者肩摩于局之門,憾無多錢以應之耳。蓋滇之有錢,自今天啟六年始矣。”有明以來,云南城市或市鎮上一直存在著銀貝兌換的情況,包括相關的“巴行”,可理解為我們常說的錢莊。既然有銀貝兌換、銀錢兌換,錢貝兌換也是順理成章的。
“崇禎四手”母子錢一對(正、背面),上圖為母錢。
政府之所以推出這種于己不利的“崇禎四手”錢,有一種合理解釋,就是當成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區,用來激勵百姓以貝換錢的惠民政策。明末,海貝雖然貶值嚴重,但云南地域廣袤,邊地百姓對于朝廷政策缺乏認知與敏銳度,尤其是相對閉塞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要改變“用貝”這種延續千年的舊習,亟須“利益”作為誘因,“崇禎四手”錢恰好充當了這一角色。政府以這種“惠民”政策詔告民眾,用超值的銅錢激勵百姓換出手中貶值的海貝,政策推行也就更容易實現。
至于“崇禎四手”錢的性質,筆者認為它只是一種樣錢。為何這么說?因為明末海貝加速貶值,對于錢文刊有海貝等價定義的銅錢,其價值等同于海貝,顯而易見會隨海貝的貶值同樣貶值。還未發行就已注定貶值的貨幣,無論是政府還是百姓都不會接受,也不可行。既然政府發行制錢目的是替換海貝、“廢貝行錢”,再把跟海貝一樣的銅錢發給百姓缺乏實際意義。
因此“崇禎四手”錢只是一個范本展示,其意義在于通告百姓用16枚海貝即可兌換1枚銅錢,而真正參與兌換的則是與“崇禎四手”錢相似的云南版崇禎小平制錢。可以推測,“崇禎四手”錢僅出現于政府設立或指定的兌換機構,例如“巴行”,作為詔告或公示用的樣本,亦即樣錢,且限于機構使用,并不參與實際流通。這既能解釋“崇禎四手”錢鑄量有限、存世稀罕的客觀事實,也解答了其未在大批云南流通錢中被發現,而只是個別流轉傳世的疑問。

“崇禎四手”錢以實物資料補充了史料失載與缺佚,不愧為云南貨幣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