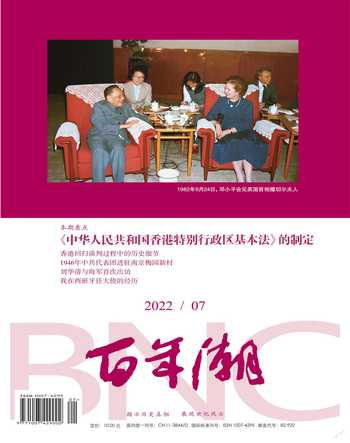任弼時(shí)與保密工作的開展
王斌斐 董一冰

任弼時(shí)
保密工作的開展伴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從小到大、由弱至強(qiáng)的發(fā)展軌跡,貫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歷程。任弼時(sh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黨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之一,長期指導(dǎo)黨團(tuán)組織在反動勢力統(tǒng)治區(qū)開展保密工作,積極探索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guān)系,推動黨領(lǐng)導(dǎo)下的群眾運(yùn)動逐步走向復(fù)蘇,對黨的機(jī)要工作隊(duì)伍培養(yǎng)和保密制度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為黨的保密工作開展作出了突出貢獻(xiàn)。
在共青團(tuán)中央指導(dǎo)秘密工作
1925年1月26日,共青團(tuán)三大在上海召開。此次大會確定了團(tuán)中央局由張?zhí)住⑷五鰰r(shí)、惲代英、賀昌、張秋人五人組成。張?zhí)兹慰倳洠五鰰r(shí)任組織部主任。此時(shí),北洋軍閥統(tǒng)治下的反動當(dāng)局嚴(yán)酷鎮(zhèn)壓革命運(yùn)動,共青團(tuán)的許多工作很大程度上還處于秘密環(huán)境下。開展秘密工作必須重視的一個(gè)重要方面是涉密資料的管理與保存。任弼時(shí)高度重視這一點(diǎn),對涉密資料的保管工作制定了嚴(yán)格的規(guī)定。

《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tuán)第三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
1925年3月11日,任弼時(shí)與張?zhí)坠餐灠l(fā)了共青團(tuán)中央通告(第二十六號),對秘書、檔案、日常組織工作的手續(xù)作出具體規(guī)定,要求切實(shí)整頓。3月20日,任弼時(shí)與張?zhí)自俅魏灠l(fā)了共青團(tuán)中央關(guān)于保密問題的通告(第三十二號),通告指出:“現(xiàn)值反動時(shí)期,必須注意秘密工作”。針對文件、刊物、住址等涉及組織機(jī)密的資料信息,“務(wù)須格外謹(jǐn)慎”,防止受到敵人追蹤;對于各地機(jī)關(guān)的通信地點(diǎn)有存在風(fēng)險(xiǎn)的情況,要求盡快更換安全地點(diǎn);在向中央局匯報(bào)情況時(shí)應(yīng)注意“來信所用各種名詞,均用譯號代替”,防止機(jī)密信息被敵方所得。這些規(guī)定有力保障了涉密資料的安全性,使團(tuán)組織工作得以在規(guī)范有序中秘密安全地開展。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yùn)動在上海爆發(fā),隨即便席卷全國,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愛國熱潮,但反動勢力的反撲也很快隨之而來。6月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jié)下,上海的斗爭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奉系軍閥派兵進(jìn)入上海,宣布全城戒嚴(yán),禁止游行示威和罷工,并占據(jù)了工會機(jī)關(guān)。隨著敵人的壓迫愈來愈緊,任弼時(shí)預(yù)感到更大的風(fēng)暴正在醞釀,應(yīng)當(dāng)未雨綢繆,轉(zhuǎn)變斗爭方式,減少團(tuán)組織的損失。
1925年7月21日,共青團(tuán)中央局會議決定由任弼時(shí)任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任弼時(shí)通過分析敵我力量對比,清晰地認(rèn)識到開展秘密工作是團(tuán)組織得以存續(xù)的必要方法。8月19日,共青團(tuán)中央發(fā)出通告(第七十三號):“我們[的]敵人是有武裝的,他們立時(shí)可以封禁、捕捉、屠殺我們。因此,在取得政權(quán)以前,無論何時(shí)何地都有秘密組織的必要”。但他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進(jìn)行秘密工作不是要縮小工作范圍,更不是停止活動”,而是要在保證組織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更為審慎的方式方法完成黨的任務(wù)安排。
任弼時(shí)認(rèn)為組織成員在秘密工作的環(huán)境下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減少接觸,需要進(jìn)行指示傳達(dá)時(shí)也要謹(jǐn)慎精簡、安全高效地完成。“盡可能不在執(zhí)行機(jī)關(guān)內(nèi)召開會議,無重要事務(wù)減少和機(jī)關(guān)的接觸”,避免引起敵人注意導(dǎo)致機(jī)關(guān)地點(diǎn)暴露在敵方視線之中。此外,信件、便箋等書面指示固然細(xì)致清晰,但也容易留下可尋蹤跡,口頭傳達(dá)則更為隱秘、便捷。因此“上級對下級的指示以口頭傳達(dá)為妥,減少文字來往”。
1925年9月18日,上海總工會被奉軍解散,革命斗爭被迫徹底轉(zhuǎn)入地下。為保護(hù)團(tuán)組織安全,任弼時(shí)特別指示要增強(qiáng)組織工作的保密性,并強(qiáng)調(diào)涉密資料的管理工作要專人專辦。1925年11月18日,共青團(tuán)中央發(fā)出加強(qiáng)保密技術(shù)的通告(第一〇八號),要求各級組織擬定保密“技術(shù)工作計(jì)劃”,根據(jù)組織大小指定負(fù)責(zé)人,“組織較小之處,可由干事或委員兼任;組織較大之地方或區(qū)委會,應(yīng)有技術(shù)書記”,對各機(jī)關(guān)的涉密資料酌情進(jìn)行保管、毀棄或轉(zhuǎn)移,最大限度地保守組織機(jī)密。
適應(yīng)秘密環(huán)境,解決黨的組織問題
國民大革命失敗后,國內(nèi)革命形勢發(fā)生劇變,由于未能及時(shí)作出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導(dǎo)致“黨組織曾遭幾次重大的破壞”,損失嚴(yán)重。1928年4月,國內(nèi)正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濃濃陰霾之下,黨的活動受到極大限制,計(jì)劃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也在緊張的籌備中。在這樣嚴(yán)峻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下,任弼時(shí)臨危受命,留守國內(nèi)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面對時(shí)局的變換和愈發(fā)嚴(yán)峻的革命形勢,任弼時(shí)從黨外黨內(nèi)兩方面分析黨組織遭受重創(chuàng)的原因。一方面,“反動統(tǒng)治向我們猛烈的進(jìn)攻”是造成黨組織受損的外部因素;但另一方面,黨的組織結(jié)構(gòu)、黨內(nèi)部分同志的自身素質(zhì)等內(nèi)部因素也存在很大的問題。最后他得出結(jié)論“本黨組織不適用于秘密工作的環(huán)境,以及黨內(nèi)同志的反動告密,實(shí)為破壞的重大關(guān)鍵”。任弼時(shí)深刻地認(rèn)識到黨內(nèi)產(chǎn)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黨組織“沒有能按照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數(shù)還是依著國共合作時(shí)代的舊方式去應(yīng)付秘密環(huán)境下的新工作”,這樣勢必導(dǎo)致不良結(jié)果的產(chǎn)生,甚至危及黨的存續(xù)發(fā)展。其產(chǎn)生的主要現(xiàn)象就是:“(一)沒有健全的支部組織,所以不能領(lǐng)導(dǎo)群眾的斗爭;(二)沒有注意秘密工作的技術(shù),極容易被敵人探悉。”為了扭轉(zhuǎn)這一不利局面,任弼時(shí)把解決“黨的組織問題”作為工作調(diào)整的重點(diǎn)。1928年5月18日,任弼時(shí)發(fā)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九號》,他在這份通告中明確指出,“嚴(yán)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黨必須有更嚴(yán)密的組織”,并根據(jù)黨這一段時(shí)間來取得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在組織結(jié)構(gòu)和組織工作上提出了一系列規(guī)定要求。
在組織結(jié)構(gòu)方面,任弼時(shí)高度重視黨支部的基礎(chǔ)性意義,強(qiáng)調(diào)“務(wù)必堅(jiān)決地采用適當(dāng)?shù)慕M織形式保持黨的組織與干部,鞏固下層組織基礎(chǔ)—支部”,并規(guī)定“以后凡超過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須按職業(yè)或工作部門分成支分部”,且“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即使一部分支部遭受了打擊,黨組織也不至于遭到徹底破壞,從而增強(qiáng)了黨的生命力,使黨的組織在困苦的環(huán)境下得以存續(xù)。同時(shí),任弼時(shí)還十分重視黨員素質(zhì)的培養(yǎng)。他認(rèn)為,每個(gè)黨員作為黨組織的基本構(gòu)成要素“必須編入支部”,承擔(dān)黨組織的工作責(zé)任,遵守黨的紀(jì)律原則,且應(yīng)當(dāng)具備某一具體工作,“成為群眾中積極活動的分子”。“不遵守或是故意違犯這些條件的分子應(yīng)當(dāng)驅(qū)逐出黨”“對于違反決議抗命不行的同志應(yīng)嚴(yán)格執(zhí)行紀(jì)律加以制裁”。這種嚴(yán)厲的要求體現(xiàn)了任弼時(shí)對待紀(jì)律執(zhí)行的堅(jiān)定態(tài)度,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黨的組織真正嚴(yán)密起來,使黨組織在高壓環(huán)境下持續(xù)推進(jìn)秘密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化裝掩護(hù)身份工作的任弼時(shí)
在組織工作方面,任弼時(shí)也作出了相應(yīng)規(guī)定。首先,他要求支部書記和干事會設(shè)置候補(bǔ)人選,作為緊急事態(tài)下的應(yīng)急準(zhǔn)備,以保證機(jī)關(guān)遭受破壞時(shí)組織工作仍能繼續(xù)運(yùn)行。在割據(jù)區(qū)域的黨組織,也應(yīng)盡量保持謹(jǐn)慎態(tài)度,保留一部分秘密機(jī)關(guān)和負(fù)責(zé)同志,以防意外的發(fā)生。其次,任弼時(shí)強(qiáng)調(diào)“開會時(shí)務(wù)須特別注意秘密技術(shù)”,防止敵人竊聽、追蹤,威脅整個(gè)組織的安全。此外“除指定收藏文件之機(jī)關(guān)外,其他機(jī)關(guān)與負(fù)責(zé)同志居住處所不應(yīng)儲藏文件,無論任何機(jī)關(guān)不應(yīng)保存同志名單與地址”。既保證組織機(jī)密文件得到嚴(yán)密管理,降低了泄密風(fēng)險(xiǎn),也使從事秘密工作的機(jī)要人員得到了安全保護(hù)。最后,任弼時(shí)深刻認(rèn)識到“黨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黨領(lǐng)導(dǎo)廣大群眾斗爭時(shí)才有意義”。他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中指出,“秘密工作之意義不是縮小黨的活動范圍,脫離群眾去求黨的安全,隱密黨的政治主張”,如果為了確保絕對安全而過分追求秘密活動,就會逐漸與群眾脫離,難以取得群眾的信任,也無法有效地調(diào)動起群眾的力量。黨的各級支部必須“利用一切公開及半公開的機(jī)會去團(tuán)結(jié)工農(nóng)群眾”,不斷擴(kuò)大黨的影響。因此,任弼時(shí)把秘密工作環(huán)境下黨組織的最重要任務(wù)歸結(jié)為:“運(yùn)用公開機(jī)會去團(tuán)結(jié)廣大群眾”。這樣才能在需要發(fā)動群眾時(shí)更好地凝聚力量,在需要保存實(shí)力時(shí)更好地實(shí)現(xiàn)自我防護(hù)。這些規(guī)定使黨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組織工作制度日趨完備,幫助黨組織快速適應(yīng)了秘密工作環(huán)境,黨組織的自身安全也得到了極大保障。
在中共江蘇省委指導(dǎo)秘密工作
192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改組中共江蘇省委。不久后,任弼時(shí)被任命為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任弼時(shí)主持省委宣傳工作后,首要任務(wù)是深入宣傳六大的政治路線和斗爭策略,激發(fā)群眾的斗爭熱情,指導(dǎo)群眾斗爭。為此他主抓了革命報(bào)刊的出版發(fā)行工作。創(chuàng)辦了《白話日報(bào)》《教育周刊》《每日新聞》三種報(bào)刊,分別以工人群眾、各支部、省委機(jī)關(guān)為主要受眾對象,在宣傳黨的思想、指導(dǎo)支部工作,介紹斗爭經(jīng)驗(yàn)等方面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白話日報(bào)》因面向公眾揭露反動派的種種陰謀而被屢屢查封,歷經(jīng)多次改名,如“上海報(bào)”“天聲”“晨光”“滬江日報(bào)”等,后采取秘密出版的方式,通過黨的組織系統(tǒng)發(fā)放到工人手中。
6月底,任弼時(shí)出席了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全會肯定了江蘇省委“在組織上把秘密的黨組織和公開的群眾組織結(jié)合起來,盡可能采用公開名義組織群眾斗爭”的做法,并在《政治決議案》中指出,“要加強(qiáng)黨的秘密工作,使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親密地聯(lián)系起來”。須知一個(gè)秘密的革命政黨,想要在群眾中樹立它的政治領(lǐng)導(dǎo)作用,必須使其政治主張深入廣大群眾。這決定了黨的一切工作都要緊緊依靠群眾。任弼時(shí)在理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二者關(guān)系的同時(shí),更看重如何利用公開的、半公開的,合法的、非合法的機(jī)會來加強(qiáng)中國共產(chǎn)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影響,以此實(shí)現(xiàn)黨的政治主張。
1929年7月,任弼時(shí)在《教育周刊》第二期發(fā)表的《爭取公開機(jī)會的意義與教訓(xùn)》一文中表示,在群眾革命熱情日漸高漲的形勢下,正是黨為廣大群眾指引正確方向,擴(kuò)大黨對群眾影響力的好時(shí)機(jī)。如果黨的工作僅限于“狹隘的秘密路線”,必然趕不上群眾的需要。因此,黨必須把握時(shí)機(jī),積極“調(diào)動指揮廣大群眾的行動”“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結(jié)合起來,善于運(yùn)用公開半公開機(jī)會,去擴(kuò)大自己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任弼時(shí)認(rèn)真籌備了組建“上海工會聯(lián)合會”(簡稱“工聯(lián)會”)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兩個(gè)公開性群眾組織的工作計(jì)劃,力求充分利用公開的機(jī)會來擴(kuò)大宣傳,以實(shí)現(xiàn)盡可能發(fā)動更多群眾的目標(biāo)。
1929年6月17日,任弼時(shí)在參與討論“工聯(lián)會”工作大綱時(shí)提出,“‘工聯(lián)會應(yīng)爭取在下層群眾中公開活動”,密切聯(lián)系各工會群眾并指導(dǎo)群眾斗爭。7月4日,江蘇省委常委會議通過了任弼時(shí)起草的《關(guān)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大綱》。大綱規(guī)定,同盟的“一切工作都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采取公開活動的方式”。據(jù)此,7月14日,同盟組織了一次公開性的露天反帝群眾大會。此次大會的召開極大鼓舞了廣大群眾的士氣,在擴(kuò)大同盟影響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由于工作部署上的不足和所處環(huán)境的壓力,仍有群眾宣傳力度不夠、群眾之間信息傳遞不暢等問題產(chǎn)生。7月22日,任弼時(shí)針對本次反帝群眾大會的意義和教訓(xùn)作出總結(jié),認(rèn)為此次運(yùn)動的主要缺點(diǎn)在于,各區(qū)在發(fā)動群眾過程中“多數(shù)還只是經(jīng)過秘密路線,沒有能夠盡量利用公開工會或團(tuán)體名義號召群眾參加”,缺乏公開性質(zhì)的工作形式。使本次大會未能完全沖破秘密集會的桎梏,導(dǎo)致大會的影響力、發(fā)動群眾的廣泛性受到了限制。“工聯(lián)會”和反帝大同盟的組建和運(yùn)動開展,使處在秘密環(huán)境下的黨組織密切了與群眾的聯(lián)系,也使公開性質(zhì)的群眾斗爭在組織上有了依托,讓更多同志認(rèn)識到,“只有使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密切聯(lián)系起來,才能夠強(qiáng)固黨在群眾中的作用”。
在延安錘煉機(jī)要工作隊(duì)伍
1941年7月2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由任弼時(shí)擔(dān)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不久后又將中央秘書處和書記處的業(yè)務(wù)工作機(jī)構(gòu)合并,由任弼時(shí)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在延安協(xié)助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任弼時(shí)充分認(rèn)識到在機(jī)關(guān)內(nèi)部運(yùn)作的涉密工作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事業(yè)的重要性。他把這些工作比作人身上的血管,“掌握了黨的生命”,一旦因工作失誤導(dǎo)致機(jī)密外泄,“會使我們的工作失敗”,“革命失敗”,使黨的革命事業(yè)陷入難以挽回的境地。對于從事機(jī)要工作的同志來說,高度涉密的工作性質(zhì)決定了對他們的審核和培養(yǎng)要有更高的要求。
1943年1月31日,中央書記處發(fā)出《中央關(guān)于審查機(jī)要人員的指示》,要求各根據(jù)地黨政軍負(fù)責(zé)同志“對全部機(jī)要人員從思想、歷史、工作等方面進(jìn)行徹底審查,使每個(gè)機(jī)要人員能夠從政治、思想、工作上保障黨的機(jī)密”。隨著這項(xiàng)工作的展開,整個(gè)黨政軍機(jī)關(guān)得到了一次洗禮和凈化,保證了機(jī)要隊(duì)伍的純潔性,使中央內(nèi)部的工作風(fēng)貌煥然一新。
除此之外,任弼時(shí)還十分注重對機(jī)要人員素質(zhì)的全面培養(yǎng)。1943年7月2日,任弼時(shí)在延安機(jī)要人員會議上發(fā)表演講,鄭重地說:“機(jī)要人員要具備下列品質(zhì):(一)對黨無限忠誠,嚴(yán)守秘密。(二)埋頭苦干,細(xì)致負(fù)責(zé)。(三)改進(jìn)技術(shù),精益求精。(四)努力學(xué)習(xí),不甘落后。”既要堅(jiān)定對黨忠誠的信念,又要不斷提升專業(yè)技能,還要在工作和學(xué)習(xí)上保持責(zé)任心和上進(jìn)心,以此來激勵(lì)機(jī)要人員全方位提升個(gè)人素質(zhì)。
任弼時(shí)不僅對機(jī)要人員的工作素養(yǎng)有著嚴(yán)格要求,還特別看重他們的意志力和對黨的忠誠性。在延安整風(fēng)運(yùn)動中,任弼時(shí)曾向同志們講道:“不管是在秘密環(huán)境中工作也好,在根據(jù)地建設(shè)的環(huán)境中也好”,都要抱有堅(jiān)定的階級立場,“堅(jiān)決勇敢犧牲個(gè)人利益,必要時(shí)甚至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了個(gè)人的生命”,這就是無產(chǎn)階級黨性所應(yīng)有的表現(xiàn)。只有不斷提高機(jī)要人員的黨性修養(yǎng),才能使之在各種復(fù)雜環(huán)境中不退卻、不變色,最終克服重重困難,完成黨的任務(wù)。周子健在《憶弼時(shí)同志領(lǐng)導(dǎo)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斗爭》中回憶道:“遵照中央和任弼時(shí)同志的指示精神,辦事處始終注意加強(qiáng)思想政治工作”,“經(jīng)常進(jìn)行階級斗爭教育,保密教育”。反復(fù)提醒辦事處同志們要“提高警惕,堅(jiān)持斗爭,注意保密,堅(jiān)持革命的氣節(jié)”。這大大增強(qiáng)了他們的精神斗志,同志們一致在內(nèi)心立下誓言:“在任何情況下也要堅(jiān)決保守黨的秘密”。
任弼時(shí)對機(jī)要人員自身素質(zhì)、黨性修養(yǎng)、階級立場等方面的嚴(yán)格要求和悉心培養(yǎng),鍛造出了一批專業(yè)素質(zhì)過硬、精神意志堅(jiān)定的機(jī)要工作隊(duì)伍,為保守黨的機(jī)密,推進(jìn)革命事業(yè)作出了極大貢獻(xiàn)。
采取特殊措施保護(hù)黨的機(jī)密
1943年5月15日,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tuán)發(fā)表了關(guān)于解散第三國際的決定。蔣介石趁此一邊大造反共輿論,要求中國共產(chǎn)黨“解散”,“取消邊區(qū)割據(jù)”,一邊密電胡宗南“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qū)”。國民黨頑固派在輿論上的咄咄逼人和在軍事上的接連調(diào)動引起了任弼時(shí)等黨中央領(lǐng)導(dǎo)的警覺,提前做出了應(yīng)對措施。1943年7月6日,負(fù)責(zé)管理西安辦事處的任弼時(shí)致電周子健稱:“蔣、胡進(jìn)攻邊區(qū)似具決心,西安辦事處應(yīng)將一切機(jī)密文件即行銷毀,免遭查抄”。后來,中共中央通過召開示威大會,公開發(fā)表社論等方式,向國民黨當(dāng)局施壓。雖然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但任弼時(shí)已然看穿蔣介石的陰謀。他預(yù)言道:日本趕出中國后,中國內(nèi)戰(zhàn)必起。

1943 年,任弼時(shí)在楊家?guī)X
1946年8月,國共談判陷于停頓,蔣介石調(diào)動起最大限度兵力向解放區(qū)發(fā)起全面進(jìn)攻。1946年8月23日,任弼時(shí)在對周子健的電報(bào)中指示:“在戰(zhàn)爭范圍擴(kuò)大的情況下,國方很可能襲擊以至封閉西辦。請作一切必要準(zhǔn)備,秘密文件應(yīng)毀去”,“準(zhǔn)備應(yīng)付一切可能到來的突然事變”。任弼時(shí)料敵先機(jī)地采取防范措施,確保了辦事處機(jī)密未被敵方查獲。不僅如此,他還指示西安辦事處及時(shí)準(zhǔn)備“秘密收報(bào)機(jī)”,通過收聽延安黨務(wù)廣播臺的廣播進(jìn)行聯(lián)絡(luò),以保持在國共關(guān)系緊張時(shí)期西安辦事處與延安的穩(wěn)定聯(lián)系。由于任弼時(shí)的一系列提前部署,直到1946年西安辦事處撤退,在電臺及與黨中央電訊聯(lián)絡(luò)上,沒有出現(xiàn)大的問題,完成了黨的任務(wù)。
1947年4月,胡宗南率部進(jìn)入延安,后在瓦窯堡發(fā)現(xiàn)了幾箱書報(bào)刊物等文獻(xiàn),這加大了黨中央對留存在敵占區(qū)文獻(xiàn)資料安全問題的重視。4月7日任弼時(shí)專門致電曹力如(時(shí)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書長、黨的后方委員會委員),特別強(qiáng)調(diào):“在目前敵人亂竄情況下,請對安條嶺十五箱文件負(fù)絕對保管責(zé)任,在危急時(shí)徹底燒毀”,體現(xiàn)了他對涉密文件的看重和面對特殊情況時(shí)決意采取特殊措施的果斷,這批中央機(jī)密文件也因此未落敵手。
轉(zhuǎn)戰(zhàn)陜北,制定電訊和密碼保密制度
電報(bào)通訊是一項(xiàng)精密細(xì)致而又高度機(jī)密的工作,且時(shí)常需要面對敵方通訊干擾、電訊密碼保密等技術(shù)問題,因此更需要嚴(yán)密的制度支撐。1947年3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離開延安,轉(zhuǎn)戰(zhàn)陜北。但中央與各地方之間卻難以保持迅捷的溝通,急需建立有效的聯(lián)絡(luò)機(jī)制,恢復(fù)中央與地方的聯(lián)絡(luò)。

中共七大前后的任弼時(shí)
1947年5月12日,任弼時(shí)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軍區(qū)負(fù)責(zé)人的電報(bào)中明確了電臺聯(lián)絡(luò)方法,即“在葉劍英、楊尚昆領(lǐng)導(dǎo)下在晉綏建立中央后方大臺,負(fù)責(zé)收轉(zhuǎn)中央與各地來往電報(bào)”。任弼時(shí)特別強(qiáng)調(diào)“批定等級要嚴(yán)格,注意緊縮電文”“注意分清使用密本”等。電文篇幅的縮減既可以減少收發(fā)難度,也可以在被截獲時(shí)有效地迷惑敵人,密本的使用同樣為我方機(jī)密訊息安上了一道“保險(xiǎn)鎖”。這些規(guī)定大大提高了電臺通訊、指令傳達(dá)的執(zhí)行效率和安全系數(shù),使中央對各軍區(qū)的指揮可以更加安全高效地進(jìn)行。1947年7月,任弼時(shí)協(xié)助周恩來在陜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集機(jī)要業(yè)務(wù)會議時(shí),根據(jù)當(dāng)時(shí)敵我電訊、密碼斗爭中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認(rèn)真研究制定了正確的密碼方針和通訊聯(lián)絡(luò)方案以及嚴(yán)格的保密制度。1947年9月底,任弼時(shí)和周恩來又召集相關(guān)部門負(fù)責(zé)同志開會,研究通信、機(jī)要、情報(bào)等秘密工作,著重就“通訊機(jī)要工作中密碼編制、使用、保管等問題”進(jìn)行了商討,確定要嚴(yán)密把好密碼和電報(bào)從編制到銷毀的各個(gè)關(guān)口,做到每一環(huán)節(jié)無紕漏,嚴(yán)防敵人對我方電訊情報(bào)的監(jiān)聽截獲。任弼時(shí)建立的電訊密碼保密制度大大提高了黨組織工作的保密層級,使黨的機(jī)密訊息得以安全傳輸,為解放戰(zhàn)爭時(shí)期的電訊斗爭奠定了勝利的基礎(chǔ)。
(責(zé)任編輯?崔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