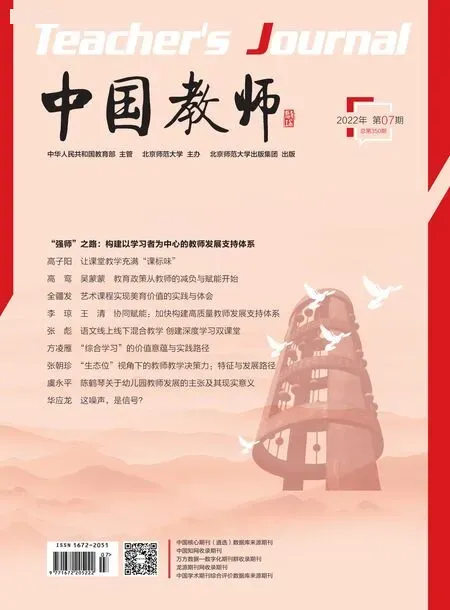教育政策從教師的減負與賦能開始
高鸞?吳蒙蒙
【摘 要】重視教師是教育以學生為中心的系統路徑。為了改進教育中的問題,教師需要成為更好的教育倡導者,在教育政策中發出更大的聲音。但現實中教師對于教育政策有很大的疏離感,絕大多數教師不關注教育政策也難以落實教育政策。研究發現,要實現教師與教育政策的有效互動,目前至少遭遇了兩重困境:工作時間稀缺導致的教師發聲意愿不足和體制機制障礙導致的教師發聲通道受限,因此教育發展需要關注教師的減負,把一部分自由時間和自由心智還給教師,減負后教師才有可能成為教育政策的主體參與者,也只有這樣教師才有機會積極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使教育政策有理、有力地落實,切實推進教育發展。
【關鍵詞】教師減負 教師主體性 教育政策
“教師很重要(Teacher Matters)”是近年來教育界乃至全社會日益強化的共識[1],教師對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促進學生發展至關重要,重視教師是教育以學生為中心的系統路徑。為了改進教育中的問題,教師需要成為更好的教育的倡導者,發出他們的聲音,讓決策者聽到“來自前線的炮火聲”,使教育改革有的放矢。當然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關注教師是我們創建以學生為中心教育的最有力杠桿,因為教育工作者天生就是倡導者,調查顯示大多數教師成為教師就是因為他們想改變學生的生活[2]。然而,對于要將其影響力擴大到課堂之外的教師來說,目前至少遭遇了兩重困境:工作時間過長導致的發聲意愿不足和體制機制障礙導致的發聲通道受限,要實現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亟須為教師減負與賦能。
一、教師減負:把自由時間與自由心智還給教師
教師減負涉及實際工作量的減負和心智感受的減負兩個層面。教師們的“精疲力竭”既有實際工作不斷加碼的壓力,也受到教師自身在現代化環境中的心智焦慮影響。在教師實際工作時間增加方面,“雙減”及相應的教育改革可作為近期的一個例證。研究顯示,“雙減”在一定程度上把學生從沉重的課外負擔中解放出來了,但作為“雙減”工作主要執行者、落實者的一線教師,身上的負擔卻更重了。2022年3月2日在京發布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雙減”進一步落地仍面臨挑戰,比如,74.3%的受訪教師表示,“雙減”后“作業設計要求更高了”;47.2%的受訪教師每周純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60.3%的受訪教師認為實行課后服務后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訪教師呼吁減輕非教學負擔[3]。對教師工作的“質”與“量”的要求都不斷提升,致使很多教師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教師開展教科研等活動的時間被壓縮,專業發展受到影響。
教師近年來的心智焦慮主要表現為日益加劇的現代性焦慮。作為現代學校系統中的靈魂,在時代車輪奔涌向前的過程中,在現代化和信息化的浪潮里,面對不斷升級的外部要求,教師產生了“時不我待”的時間稀缺感,這種稀缺感讓他們只能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當下緊急的任務,無力在教育改革的大系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我國,以教師發展政策為例,2018年以來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推進教師隊伍建設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政策,但很多一線教師因為忙于“埋頭趕路”而無暇關注課堂外的信息,認為高高在上的教育政策“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而表現出“與我無關”的態度,對政策有明顯的疏離感……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近年來我國推進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努力和一線教師之間失去了良性互動,政策支持在現實中演化為一種單純的“外在干預”,本應是教師自身生存目的與基本方式[4]的教師發展成為政策要求下“由外向內”的“被動行為”,教師發展從主體性行動異化為客體性行動,甚至在一些教師看來,國家對教師的各種支持政策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任務”,來爭奪他們本就稀缺的時間。政策失去了教師的主體性參與往往收效甚微,很多教師專業發展項目淪為形式化的“走過場”,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
1. 警惕理性邏輯下的“簡單化”效率追求
學校系統中基于理性邏輯的績效追求與“標準化”思潮消解了教師的文化身份和對教師人生的終極關懷,遮蔽了教師的主體性和教師發展的內在價值,這種“標準化”的浪潮始于20世紀的美國。1981年,美國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上臺,任命了國家卓越教育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83年編寫了一份題為《處于危險中的國家: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的報告,報告對當時美國學校教育系統的有效性發起了全面的攻擊,之后美國教育系統在各個領域展開了全面的基于標準的改革,包括學生的標準化測試、教師職業的標準化、學校管理的標準化,等等①。“標準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簡單化”,背后是西方國家的理性邏輯。西方學者認為理性邏輯的特點就是控制,今天各種考試和標準控制著我們的教師和學生甚至家長,決定人生價值和存在的是無情的標準,而不是人自身。當教師與學生過于專注各種考試和標準時,也逐漸喪失了主體性。教育日趨簡單化的過程就是教育被技術理性不斷扭曲和異化的過程,教育的整體性、豐富性、藝術性、人文性不見了,因而日漸機械僵化、蒼白而貧困[5]。
這種教育簡單化會讓教師陷入追求績效的管窺之中。管窺(tunneling)指人們的視野會因資源稀缺感變得狹窄,只能透過管子的孔洞看清少量物體,而不是管外的一切。研究發現,當稀缺感俘獲大腦時,人們的注意力會集中在緊急的事情上,將其他事物排除在外,這在短期內會讓人們獲得專注紅利,但專注也會導致管窺變窄從而使主體付出沉重代價[6]。因此,各種外部績效要求和控制會俘獲教師的注意力,帶來時間的稀缺感,令教師只能專注于各種考試和標準。這可能帶來一點點好處,使教師能夠在應對迫切需求時做得更好,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教師的損失更大,會忽視需要關注的重要事項,在生活的其他方面變得不那么有成效。當時間的稀缺成為教師認知的負擔時,教師就無法有效規劃未來,這樣一來,向前看的能力就會因為管窺而喪失,發展就會停滯。同時,由稀缺感造成的管窺會讓教師在平時只關注工作中緊急且具體的任務,在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教師往往需要獨立處理所有的問題,很難獲得外部的幫助,這些工作會讓教師形成一種習得性無助感,而這種無助感又會進一步加劇教師對于外部信息(如教育政策)的疏離感。簡單化的教育和學校系統必然會造就系統內的主體即教師乃至學生的“簡單化”,教育的“簡單化”,也會不斷加劇社會的“簡單化”,這是需要今天的教育者們警惕的。
2. 雙重減負讓教師實現主體性回歸
今天學校系統中的教師在高效率和“標準化”的控制之下,常常陷入時間的稀缺陷阱—持續從一項緊要任務快速轉移到另一項緊要任務,只顧“埋頭趕路”,無暇“仰望星空”,這是管窺所引發的后果。教師在當下已盡己所能,但這樣的做法將大大削弱教師的潛能,對教育未來的發展造成損害。這種損害主要源于教師們將本可預期的事件當作突如其來的事件處理,導致前期準備的缺乏和處理事情時精力與能力的不足。避免進入稀缺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擁有“余閑”,即擁有(部分)自由的時間和自由的心智。余閑是西方學者在行為經濟學和發展心理學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指我們的擁有大于所需,也是我們在資源豐富時進行資源管理的特定方式。如果教師的時間安排總是很滿,沒有余閑,他們就只會專注于當下必須完成的工作,預測不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和可能到來的機遇與挑戰。同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會不自覺地產生權衡式思維,這種權衡不僅會帶有明顯的現時偏見(present bias),即人們會將未來的利益作為代價,過高地估計即刻的利益,而且還會持續消耗人的精力,占用人的認知帶寬。研究發現,權衡式思維對人認知帶寬的占用,會造成認知帶寬負擔,導致人智力下降,這種智力下降又會進一步導致能力的下降。當認知帶寬不足時,教師的認知能力和執行能力都會減弱,就會無暇也無力再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做教師工作的難度就會加倍。例如,他們面對學生時常常沒有辦法表現出足夠的耐心。
因此,只有擁有余閑才能讓教師在工作之余有機會停下來進行學習與反思,超越“標準化”“簡單化”的外部要求,完成心靈的豐富,并有能力思考關于發展、本質、聯結、關系等教育和生活情境內更重要的本質問題,完成主體性的回歸。當主體性回歸后,教師才能與各種外部系統如教育政策等進行良性互動,實現自身的持續成長并推動其所在教育系統的發展。
“雙減”以及近年來很多教育政策都對學校教育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校教育質量的提高,離不開教師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關注教師的減負,把一部分自由時間和自由心智還給教師,給教師留出一定的認知帶寬去從事課堂外的重要事務。教師減負,最終受益的是學生;教師減負,是充分尊重教師職業專業化的體現;教師減負,可以讓教師在忙碌的教育教學工作之余感受教書育人特有的幸福感和美好;教師減負,可以讓教師有更多時間研究教育、研究學生,提升教育質量。減負后輕裝上路的教師才有可能成為教育政策的主體參與者,也只有這樣,教師才有機會積極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使教育政策有理、有力地落實,切實推進教育發展。
二、教育高質量發展之路:鼓勵教師參與教育政策
西方學者研究發現,教師們的“精疲力竭”既是教師們無力發出自己聲音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教師在教育政策過程中未能發出自己聲音的結果。大衛(David Stieber)在文章中提出“我們必須讓教師在教育改進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強調了教師必須參與教育政策的原因:“避免教師被迫在運行不正常的系統中工作,這會讓教師感到士氣低落、氣餒和不知所措。”“讓教師成為領導者和倡導者可以解決教師不滿和短缺等關鍵問題。”在美國“關于教育最重要的決定,往往是由沒有任何課堂經驗的人做出的”,“這種模式在教育政策領域并非獨一無二,需要明確的是缺乏教師參與并不是教育工作者的錯,有許多結構性障礙,包括無意的和有意的,阻礙了教師參與決策”[7]。研究發現,這種現象在美國教育系統內非常普遍,以得克薩斯州州長(Greg Abbott)的教師短缺特別工作組為例,在該工作組的28個席位中,教師只占2席。“當教師在這一過程中的發言權如此之小時,我們無法充分解決教學短缺危機。”調查表明,許多州政府和州教育委員會、州立法機構等許多管理機構的設置,使得教師幾乎不可能參與決策過程[2]。
加拿大教育學者邁克爾·富蘭對教育發展與變革有著深入的研究,富蘭指出,除非讓教師參與發展新知識、新技能和新理解的過程,并改變教育基礎設施,否則教育變革就會一直失敗[8]。因此,將教師的影響力擴大到課堂之外可以帶來變革。教師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一項基本公民權利,還是我國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教師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滲透著以人為本的思想,將實現政府與教師的有效溝通[9]。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作為與學校、與學生、與教育都密切相關的教師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將教師納入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主體隊伍是十分必要的。而這不僅需要教育主管部門以及學校提供各種平臺讓教師能主動且有效地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還須給其提供必要的條件能有效踐行教育政策的內容[10]。
在我國,教師在教育系統中處于核心的位置,隨著民主進程的不斷推進,在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應鼓勵教師成為更重要的參與者。從主體需求來講,教師參與既是教師的利益訴求,也是教師的義務擔當;從客體需求來講,教師參與可以提高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促進其專業化發展,提高政策的制定質量,有效避免政策失真[11]。在保證教師參與時間的基礎上,應包括教師主體參與意識的培養與教師參與政策體制機制的建設兩個方面。從意識方面來說,要提高教師參與教育政策決策的權利意識和義務意識,通過權利意識的提高來影響并促進一種持續而有生命力的參與文化的形成,通過義務意識的提高來增強教師參與教育政策決策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主性。從體制方面來說,要改革教師參與教育政策決策的主體構成和制度規范。主體構成的改革一方面在橫向上要通過擴大參與教師主體范圍來提高利益表達的廣泛性,另一方面在縱向上要通過培育行業式教育政策咨詢組織來達到表達力量的凝聚[12]。在教育領域推進教師參與教育政策的制定,體現了一種全新的教師責任、權利以及教育管理觀念,不僅有助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教育政策科學化、民主化,而且是保證教育政策順利實施、減少教育政策實施阻力的重要舉措[13]。
建構教師參與的教育改進共同體,邀請教師全面參與教育政策過程,是克服目前教育公共政策諸多障礙的一條可行的路徑。教育改進共同體的建設目的是為了解決教育系統中個體難以或無法獨立改進的復雜問題,促進教育系統的整體改進,有效賦能教師,使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過程與教師形成共同的愿景、目的、規則和利益,并在此基礎上相互協作[14]。
參考文獻
[1] LOVEWELL K. Every teacher matters:Inspiring well-being through mindfulness[M].St Albans:Ecademy Press,2012:1.
[2] CARLISLE G.Teachers can positively impact education policy,we just have to use our teacher voice[EB/OL].(2022-03-24)[2022-04-12].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2-03-24-teachers-can-positively-impact-education-policy-we-just-have-to-use-our-teacher-voice.
[3] 全國“雙減”成效調查顯示:超七成受訪教師呼吁減輕非教學負擔[EB/OL].(2022-03-03)[2022-04-12].https://news.eol.cn/yaowen/202203/t20220303_2212555.shtml.
[4] 伍葉琴,李森,戴宏才.教師發展的客體性異化與主體性回歸[J]. 教育研究,2013,34(1):119-125.
[5] 杰恩·弗利納. 課程動態學 再造心靈[M].呂聯芳,邵華,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3:1-7.
[6] 塞德希爾·穆來納森,埃爾德·沙菲爾.稀缺 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忙碌的[M].魏薇,龍志勇,譯.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1-21.
[7] STIEBER D. Americas teachers arent burned out. We are demoralized[EB/OL].(2022-02-14)[2022-04-12].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2-02-14-america-s-teachers-aren-t-burned-out-we-are-demoralized.
[8] FULLAN M.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5th edition)[M].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5:18-38.
[9] 侯佛鋼,張振改. 教師參與教育政策制定的價值與困境分析[J]. 教育探索,2013(6):32-33.
[10] 鄭盛娜. 教師參與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的路徑探析[J]. 中國成人教育,2015(20):21-23.
[11] 侯佛鋼.我國中小學教師參與教育政策制定的路徑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2014:1.
[12] 李騰達.關于教師參與教育政策決策的研究[D].沈陽:沈陽師范大學,2011:1.
[13] 侯佛鋼,張振改.教師參與教育政策制定的困境分析及路徑探索[J]. 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33(31):17-20.
[14] 李茂菊,修旗,李軍. 教育改進學的創建與中國探索:專業改進共同體[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41(4):18-27.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 2020 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項目號:BHA200146)“縣域教師教育者發展的制度困境與政策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湖州師范學院)
責任編輯: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