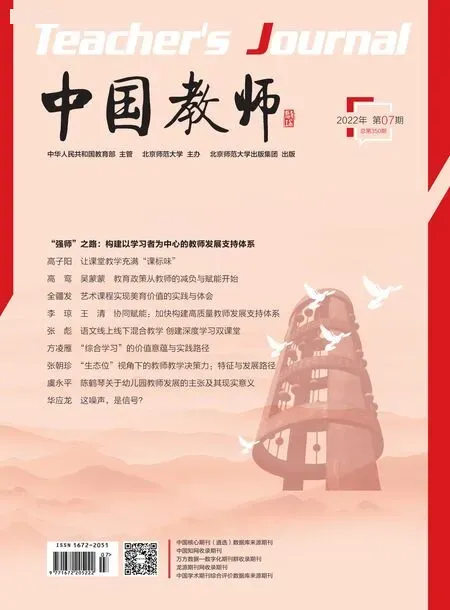“生態(tài)位”視角下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特征與發(fā)展路徑
張朝珍
【摘 要】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是衡量教學(xué)專業(yè)化的重要尺度,是指面對(duì)各種復(fù)雜教學(xué)問(wèn)題時(shí),教師能夠做出專業(yè)判斷與選擇的能力。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生態(tài)位特征表現(xiàn)為決策水平的“態(tài)”與“勢(shì)”之間的互動(dòng)與演化;教師個(gè)體生態(tài)位寬度受其經(jīng)驗(yàn)邊界制約;教師群體生態(tài)位演化具有重疊、競(jìng)爭(zhēng)與協(xié)同性。提升教師的教學(xué)決策力需要通過(guò)教學(xué)變革回報(bào)遞增的制度化,實(shí)現(xiàn)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勢(shì)”與“態(tài)”的循環(huán)上升;謀求教師教學(xué)決策經(jīng)驗(yàn)的“理性化”,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位的寬度拓展;基于差異化管理,對(duì)決策力生態(tài)位進(jìn)行調(diào)控,促進(jìn)教師群體生態(tài)位的有序分化和結(jié)構(gòu)優(yōu)化。
【關(guān)鍵詞】教師專業(yè)發(fā)展 生態(tài)位 教學(xué)決策力 教學(xué)專業(yè)化
教學(xué)活動(dòng)是在教師決策的主導(dǎo)、引領(lǐng)下開(kāi)展的,教學(xué)質(zhì)量直接取決于教師決策的質(zhì)量,教學(xué)決策力屬于教師應(yīng)具備的專業(yè)能力,是判斷教師教學(xué)專業(yè)化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從教師專業(yè)成長(zhǎng)的實(shí)踐看,教師群體中的不同個(gè)體以及同一教師的教學(xué)決策力提升并非是一個(gè)簡(jiǎn)單的線性過(guò)程,而是具有多元表征、多路徑演化、多主體競(jìng)爭(zhēng)的復(fù)雜性。這種復(fù)雜性是在特定的學(xué)校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發(fā)生、發(fā)展的,具有內(nèi)在生態(tài)特性。
一、生態(tài)位理論與教師的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
1. 生態(tài)位理論的有關(guān)觀點(diǎn)
生態(tài)位理論屬于生態(tài)學(xué)研究范疇,是由美國(guó)生態(tài)學(xué)家瑞林內(nèi)爾(Joseph Grinnell,1917)首次提出。對(duì)于這一理論,雖然學(xué)界存在各種不同觀點(diǎn)的爭(zhēng)執(zhí)和碰撞,但基本理念都認(rèn)為,生態(tài)位是生物群落的生存特征,作為群落中的每一個(gè)生物要獲得最大程度的生存與發(fā)展,必須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尋找適合的生態(tài)位來(lái)趨利避害、超越他者。生態(tài)位是生物單元在特定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與環(huán)境中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所獲得的相對(duì)地位與作用[1]。這種相互作用既可以是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也可以是協(xié)作關(guān)系。生物單元之間力量發(fā)展的不平衡性,表現(xiàn)為生態(tài)位的“態(tài)”與“勢(shì)”的差異。生態(tài)單元的“態(tài)”指生物單元在長(zhǎng)期的生長(zhǎng)、發(fā)展過(guò)程中,通過(guò)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不斷累積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和資源優(yōu)勢(shì),是其現(xiàn)有能力狀態(tài)的標(biāo)志;“勢(shì)”指生物單元利用所在環(huán)境中的優(yōu)勢(shì)資源產(chǎn)生的長(zhǎng)遠(yuǎn)影響力,標(biāo)志著生物個(gè)體和群落未來(lái)的發(fā)展?jié)摿ΑN锓N的生態(tài)位“態(tài)”“勢(shì)”的不同,直接影響其生態(tài)位的寬度。生態(tài)位寬度指的是物種通過(guò)利用各種可以獲得的資源,從而減少種群內(nèi)部個(gè)體競(jìng)爭(zhēng)的程度或范圍[2]。生態(tài)位寬度反映了生態(tài)物種在生態(tài)位演化過(guò)程中的影響力和擴(kuò)張力。生態(tài)位的演化是在由若干生態(tài)因子構(gòu)成的復(fù)雜生態(tài)系統(tǒng)中進(jìn)行的。生態(tài)因子是影響生態(tài)位形成的各種因素,包括資源、需求、文化、制度等,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構(gòu)成了生態(tài)位競(jìng)爭(zhēng)與協(xié)同、生態(tài)系統(tǒng)演化的運(yùn)行機(jī)制。
隨著生態(tài)位理論的影響不斷擴(kuò)大,其觀點(diǎn)開(kāi)始延伸到社會(huì)生活過(guò)程中,用于討論社會(huì)生活中的復(fù)雜生態(tài)系統(tǒng)。美國(guó)教育家克雷明于1976年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態(tài)學(xué)”一詞,將生態(tài)位理論引入了教育領(lǐng)域。學(xué)校是教師開(kāi)展教學(xué)工作的重要場(chǎng)域,也是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核心依托,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提升與學(xué)校的教學(xué)改革現(xiàn)狀、教師管理的制度要求、學(xué)科教師的話語(yǔ)溝通方式及其滲透的教室文化、專業(yè)規(guī)范及學(xué)生學(xué)業(yè)成就等生態(tài)因子密切相關(guān)。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提升既是教師個(gè)體不斷努力的結(jié)果,也是在專業(yè)共同體中彼此協(xié)同、不斷遞進(jìn)的過(guò)程。從這個(gè)意義看,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本質(zhì)可視作教師在學(xué)校教育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所處的生態(tài)位置、占據(jù)的資源以及發(fā)揮的專業(yè)影響力,是教師在學(xué)校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中不斷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水平提升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
2. 作為教師核心素養(yǎng)的教學(xué)決策力
目前,學(xué)界對(duì)“決策力”一詞的解釋也沒(méi)有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大致可以分為兩類:①以心理學(xué)的“個(gè)性心理特征”來(lái)解釋。如決策力指的是希望成功完成某項(xiàng)工作的欲望,包括諸如進(jìn)取心、毅力、支配力和控制力等特征[3]。②作為管理學(xué)的能力概念加以界定。如決策力是決策者所具有的參與決策活動(dòng)、進(jìn)行方案選擇的技能和本領(lǐng),是根據(jù)既定目標(biāo)認(rèn)識(shí)現(xiàn)狀,預(yù)測(cè)未來(lái),決定最優(yōu)行動(dòng)方案的能力[4]。具體而言,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包含三個(gè)層面的內(nèi)涵:一是在教學(xué)活動(dòng)中體現(xiàn)出來(lái)的教師決策力的水平和效果;二是教師提升教學(xué)決策力的自覺(jué)程度;三是教師擁有作為自主教學(xué)決策者的專業(yè)權(quán)力。
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是指教師核心素養(yǎng)在漸進(jìn)的、變化著的過(guò)程中所達(dá)到的境界或水平。借鑒日本學(xué)者森敏昭的分類,可以將教師教學(xué)所需的核心素養(yǎng)分為教學(xué)基礎(chǔ)力、教學(xué)思考力和教學(xué)實(shí)踐力三層[5]。其中,“教學(xué)基礎(chǔ)力”作為教師的基本職業(yè)能力,是教師教學(xué)思考力的基礎(chǔ)。教學(xué)基礎(chǔ)力包括教師人文與科學(xué)知識(shí)的掌握、表達(dá)能力;對(duì)學(xué)科基本知識(shí)的加工與整合能力;獲取和利用多元信息的信息能力。“教學(xué)思考力”指教師的問(wèn)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元認(rèn)知能力等,這種不斷發(fā)現(xiàn)、反思創(chuàng)造與適應(yīng)的思考力成為教師開(kāi)展教學(xué)活動(dòng)、提高實(shí)踐力的主體保障。“教學(xué)實(shí)踐力”是教學(xué)基礎(chǔ)力和教學(xué)思考力的綜合體現(xiàn),教學(xué)基礎(chǔ)力和教學(xué)思考力通過(guò)認(rèn)知性、倫理性和社會(huì)性這三類教學(xué)實(shí)踐得以發(fā)揮作用,體現(xiàn)了教師教學(xué)的專業(yè)化水平。教師決策是有效教學(xué)的前提。教師的教學(xué)決策力即教學(xué)思考力,是教師對(duì)各種教學(xué)問(wèn)題進(jìn)行判斷和創(chuàng)造性解決的高階認(rèn)識(shí)能力。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發(fā)展不是將教育教學(xué)理論直接運(yùn)用和過(guò)渡到實(shí)踐中,而是教師在實(shí)際的教育情境中,在面對(duì)解決復(fù)雜而具體的實(shí)際問(wèn)題過(guò)程中,經(jīng)過(guò)觀摩、領(lǐng)悟、反思和不斷體悟,逐漸獲得在復(fù)雜教學(xué)情境中的卓越教學(xué)能力。
第一,教學(xué)決策力的本質(zhì)是教師對(duì)各類教學(xué)問(wèn)題的識(shí)別和處理水平,從教學(xué)活動(dòng)的問(wèn)題系統(tǒng)看,包括基本教學(xué)問(wèn)題和擴(kuò)展性教學(xué)問(wèn)題。基本教學(xué)問(wèn)題在性質(zhì)上是結(jié)構(gòu)良好問(wèn)題,在內(nèi)容上以基礎(chǔ)知識(shí)和基本能力為核心的問(wèn)題系統(tǒng)。擴(kuò)展性教學(xué)問(wèn)題在性質(zhì)上是結(jié)構(gòu)不良問(wèn)題,在內(nèi)容上則是基本教學(xué)問(wèn)題的拓展或加深。結(jié)構(gòu)良好問(wèn)題的表征清晰、有相對(duì)固定或者明確的解決方法,屬于常規(guī)、程序性問(wèn)題決策;結(jié)構(gòu)不良的問(wèn)題屬于非程序性、偶發(fā)的復(fù)雜問(wèn)題,沒(méi)有明確的解決辦法,屬于非程序性問(wèn)題決策。對(duì)基本教學(xué)問(wèn)題的教學(xué)決策體現(xiàn)了教師的“基準(zhǔn)性勝任力”。
第二,教學(xué)決策力體現(xiàn)了教師對(duì)教學(xué)要素系統(tǒng)的聯(lián)結(jié)能力。從時(shí)間維度看,教師決策由課前的教學(xué)計(jì)劃決策、課中的互動(dòng)性教學(xué)決策、課后的教學(xué)評(píng)價(jià)與反思性決策三個(gè)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教學(xué)決策力是教師在教學(xué)活動(dòng)中形成與發(fā)展起來(lái)的、多謀善斷的“能手品質(zhì)”,包括多維教學(xué)目標(biāo)的選擇能力、教學(xué)設(shè)計(jì)與即時(shí)判斷能力、診斷教學(xué)問(wèn)題和元教學(xué)決策的能力等方面[6]。教師對(duì)這些教學(xué)要素的判斷、選擇和加工往往采取不同處理方式,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是在這些系統(tǒng)的邏輯聯(lián)結(jié)中形成和發(fā)展起來(lái)的。
第三,教學(xué)決策力體現(xiàn)了教師對(duì)教學(xué)情境的適應(yīng)與超越能力。教師對(duì)教學(xué)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分為結(jié)果適應(yīng)與過(guò)程適應(yīng)。結(jié)果適應(yīng)是教師對(duì)學(xué)校教學(xué)管理要求和社會(huì)期待的滿足,教師以教學(xué)目標(biāo)為決策基點(diǎn),選擇并實(shí)施能夠最大限度實(shí)現(xiàn)既定目標(biāo)的決策方案,它反映了外在目的對(duì)教師教學(xué)決策的控制。過(guò)程適應(yīng)遵循決策對(duì)特定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邏輯,教師根據(jù)具體教學(xué)問(wèn)題和教育教學(xué)的基本規(guī)則,實(shí)施一種生成中的決策,決策的目的是謀求整個(gè)教學(xué)活動(dòng)對(duì)學(xué)生學(xué)習(xí)和成長(zhǎng)狀態(tài)的適應(yīng)與促進(jìn)。這兩種適應(yīng)模式的區(qū)分是相對(duì)的,教育實(shí)踐中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往往是這兩種模式的交織,教師在預(yù)定教學(xué)任務(wù)的框架內(nèi),實(shí)施一定范圍內(nèi)的教學(xué)決策創(chuàng)造和生成。
二、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生態(tài)位特征
在教育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不斷發(fā)展起來(lái)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具有內(nèi)隱的生態(tài)位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gè)方面。
1. 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是“態(tài)”與“勢(shì)”之間的互動(dòng)與演化
任何生物單元都包含“態(tài)”和“勢(shì)”兩方面的生態(tài)位屬性。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態(tài)”指教師教學(xué)水平的現(xiàn)有狀態(tài),表現(xiàn)為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起點(diǎn)或結(jié)果;“勢(shì)”指在學(xué)校內(nèi)部或者區(qū)域教育組織的群體生態(tài)鏈條中,教師個(gè)體所占據(jù)的專業(yè)位置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對(duì)所處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現(xiàn)實(shí)影響力或支配力,代表教師向外的輻射能力和未來(lái)的發(fā)展?jié)摿Α!皯B(tài)”作為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起點(diǎn)和結(jié)果,具有相對(duì)靜止的特點(diǎn);“勢(shì)”則體現(xiàn)了教師對(duì)有助于自身發(fā)展的各類專業(yè)資源的占有和運(yùn)用能力,反映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從一般意義上講,教師群體的教學(xué)決策發(fā)展具有大致相同的階段性規(guī)律,會(huì)歷經(jīng)從新手教師、有經(jīng)驗(yàn)的教師到專家教師的發(fā)展過(guò)程。但對(duì)教師個(gè)體的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而言,則有著明顯的生態(tài)位特征,例如,發(fā)展起點(diǎn)相同的新手教師群體,因?yàn)椤皠?shì)”的不同,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態(tài)”,發(fā)展結(jié)果反過(guò)來(lái)又成為新的專業(yè)起點(diǎn),起點(diǎn)高低則影響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方向和速度。因此,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態(tài)”與“勢(shì)”是相互生成、不斷循環(huán)的關(guān)系。這種“態(tài)”與“勢(shì)”之間的關(guān)系使得教師專業(yè)成長(zhǎng)具有共性與差異共存的復(fù)雜性。
2. 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生態(tài)位寬度受到經(jīng)驗(yàn)邊界的制約
生態(tài)位寬度是指一個(gè)生態(tài)單元所能控制和利用的各種資源總量或幅度。生態(tài)位越寬,生態(tài)單元的競(jìng)爭(zhēng)力越強(qiáng)。雖然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是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但是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本身有著難以避免的作用邊界。在學(xué)校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教師個(gè)體尋找最佳專業(yè)位置往往經(jīng)歷生態(tài)位占有、生態(tài)位適應(yīng)和生態(tài)位拓展三個(gè)階段。當(dāng)教師入職并掌握了基本的教學(xué)決策技能之后,就從生態(tài)位占有階段進(jìn)入適應(yīng)階段,進(jìn)入適應(yīng)階段的教師會(huì)出現(xiàn)明顯的分化狀態(tài)。
3. 教師群體教學(xué)決策力的生態(tài)位演化具有重疊、競(jìng)爭(zhēng)與協(xié)同性
生態(tài)位重疊是指生態(tài)位相似的多個(gè)生態(tài)單元同時(shí)生活于同一空間,對(duì)有限資源進(jìn)行競(jìng)爭(zhēng)或分享共同資源的現(xiàn)象[7]。目前,中小學(xué)教師的教師職業(yè)發(fā)展路徑有兩個(gè)序列:一是教學(xué)序列,二是教育行政序列。對(duì)特定群體而言,這些選擇是在同一學(xué)校空間、面對(duì)共同的有限教育資源展開(kāi)的,這就導(dǎo)致教師群體生態(tài)位的重疊。美國(guó)的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提出學(xué)校存在“個(gè)人主義、派別主義、自然合作和人為合作”四種類型的教師文化。雖然教師之間容易出現(xiàn)的狹隘競(jìng)爭(zhēng)心理,對(duì)合作缺乏深刻認(rèn)識(shí),理性不足,欲多獲取少付出;在合作中過(guò)于算計(jì),不肯真誠(chéng)合作;教師合作能力低等問(wèn)題,從深層次上反映了教師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8]。但是近年來(lái),合作文化已經(jīng)逐漸成為我國(guó)中小學(xué)教師文化的發(fā)展方向。
三、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提升策略
從決策主體的角度,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發(fā)展有著共性與個(gè)性之分。教師共性的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是一般意義上對(duì)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訴求。個(gè)性的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是在共性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框架內(nèi),由于教師在能力維度上的發(fā)展不均衡導(dǎo)致教學(xué)決策力發(fā)展的差異,表現(xiàn)為教師個(gè)體在專業(yè)發(fā)展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的教學(xué)決策力個(gè)體差異,也表現(xiàn)為包括處于不同專業(yè)發(fā)展階段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的階段性差異。這些差異構(gòu)成了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提升的多元“生態(tài)位結(jié)構(gòu)”。
1. 通過(guò)教學(xué)變革回報(bào)遞增的制度化,實(shí)現(xiàn)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在“態(tài)”與“勢(shì)”之間的循環(huán)上升
有效的教師專業(yè)發(fā)展有著以下原則:①發(fā)展目標(biāo)以個(gè)人和組織的變革為重點(diǎn),對(duì)自身所處的實(shí)踐背景有著相當(dāng)?shù)拿舾行?②發(fā)展活動(dòng)以學(xué)習(xí)和學(xué)習(xí)者為焦點(diǎn);③發(fā)展方式是參與、合作和持續(xù)反思的過(guò)程[9]。決策力增強(qiáng)的實(shí)質(zhì)是決策“寬裕區(qū)間”的出現(xiàn)和擴(kuò)大,它是決策者在已有成功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寬裕決策”狀態(tài)[10]。但是“寬裕決策”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寬裕區(qū)間的出現(xiàn)既可以減輕教師參與教學(xué)變革的壓力,有助于形成體現(xiàn)個(gè)性的教學(xué)決策偏好,做出質(zhì)量更高的決策;另一方面,寬裕區(qū)間也可以使教師滿足既有的業(yè)績(jī),缺乏不斷提升的動(dòng)力,導(dǎo)致教學(xué)決策水平的徘徊不前甚至降低。當(dāng)新手教師度過(guò)職業(yè)生涯初期后,教學(xué)決策力逐漸強(qiáng)化,充足的專業(yè)信心使他們?cè)敢鈬L試各種教學(xué)策略,開(kāi)發(fā)各種課程資源,形成教師個(gè)體主導(dǎo)的小范圍教學(xué)改革,改革獲得的初步成功和改革中得以培養(yǎng)起來(lái)的能力,會(huì)進(jìn)一步拓寬教師教學(xué)決策的寬裕區(qū)間。
學(xué)校變革理念、環(huán)境與教師在長(zhǎng)期的教學(xué)經(jīng)歷中不斷積累和沉淀的教育視野、信念、知識(shí)和變革勇氣共同成為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提升的基本條件。學(xué)校作為教學(xué)變革的客觀環(huán)境對(duì)風(fēng)險(xiǎn)成本的接受程度與教師的變革投入直接相關(guān),影響教師對(duì)教學(xué)變革的性質(zhì)、價(jià)值和意義的理解、對(duì)教學(xué)變革的成本詮釋和投入積極性。有遠(yuǎn)見(jiàn)的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者能以專業(yè)的眼光與判斷力,支持教師開(kāi)展有教育意義的變革性決策,并在變革的早期提供理念、政策和資源支持。這種變革性決策的成功會(huì)帶動(dòng)其他人的變革積極性,形成教學(xué)變革的連片效應(yīng)和有活力的教師文化。這種文化其實(shí)是一種組織承擔(dān)變革風(fēng)險(xiǎn)的信號(hào)釋放,它能夠容忍和消化小部分的變革失敗,消除教師實(shí)施變革的疑慮。因此,我們除了注重對(duì)教師專業(yè)“態(tài)”的認(rèn)定和評(píng)價(jià)外,更要關(guān)注教師專業(yè)“勢(shì)”的變化方向、內(nèi)容和速度,通過(guò)正反饋的變革回報(bào)遞增幫助教師群體基于自身職業(yè)優(yōu)勢(shì)與局限性以及所處學(xué)校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資源條件與制約,聚焦不同專業(yè)類別和專業(yè)層級(jí)進(jìn)行生態(tài)位規(guī)劃,從而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位的良性演變和優(yōu)化。
2. 謀求教師教學(xué)決策經(jīng)驗(yàn)的“理性化”,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位的寬度拓展
教師教學(xué)的“理性化”是借助嚴(yán)格定義的概念或范疇,對(duì)于種種的教學(xué)觀念、制度、行為以及時(shí)間和空間的配置等進(jìn)行系統(tǒng)的分析、檢驗(yàn)、批判與重構(gòu),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教學(xué)認(rèn)識(shí)和實(shí)踐過(guò)程中非理性成分的過(guò)程及其結(jié)果,使得整個(gè)教學(xué)活動(dòng)真正成為一種理性的思考或探險(xiǎn)活動(dòng)[11]。教師決策經(jīng)驗(yàn)的形成與發(fā)展分為兩個(gè)階段:一是隨著教學(xué)實(shí)踐積累起來(lái)的感性經(jīng)驗(yàn)或片段知識(shí);二是教師對(duì)感性經(jīng)驗(yàn)自覺(jué)提煉、反思后形成的理性認(rèn)識(shí)。前者屬于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量”的積累階段,后者屬于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質(zhì)”的飛躍階段,這種飛躍即經(jīng)驗(yàn)“理性化”的過(guò)程。
教師決策經(jīng)驗(yàn)的“理性化”既需要個(gè)體層面的整合性學(xué)習(xí)和反思性學(xué)習(xí),也離不開(kāi)群體層面的超越性學(xué)習(xí)。整合性和反思性學(xué)習(xí)是教師對(duì)自身和他人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理解和融會(huì)貫通;超越性學(xué)習(xí)是在教師群體決策活動(dòng)中,通過(guò)集體備課、聽(tīng)評(píng)課、校本教研、校際互助教研等組織形式,實(shí)現(xiàn)不同教師群體的差異互補(bǔ)、相互啟發(fā)、協(xié)同發(fā)展,突破自我的決策經(jīng)驗(yàn)邊界,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決策力生態(tài)位的寬度拓展。
3. 基于差異化管理對(duì)決策力生態(tài)位進(jìn)行調(diào)控,促進(jìn)教師群體生態(tài)位的有序分化和結(jié)構(gòu)優(yōu)化
教學(xué)決策力的生態(tài)位形成過(guò)程體現(xiàn)了教師之間既合作又競(jìng)爭(zhēng)的關(guān)系,自發(fā)、缺乏調(diào)控的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提升往往會(huì)帶來(lái)生態(tài)位的重疊與競(jìng)爭(zhēng)。要促進(jìn)教師群體的有序分化和共同發(fā)展,需要基于教師的發(fā)展階段、層次和類別差異,促進(jìn)教師在既有基礎(chǔ)上有差異地發(fā)展。第一,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具有發(fā)展速度的差異。學(xué)校管理者要尊重教師個(gè)體素質(zhì)的獨(dú)特性,基于不同教師群體的個(gè)性化特征實(shí)施精準(zhǔn)指導(dǎo),避免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提升的“內(nèi)卷”和惡性競(jìng)爭(zhēng),在教學(xué)管理、教師培訓(xùn)、教師專業(yè)生涯制約規(guī)劃等方面實(shí)現(xiàn)不同專業(yè)層次教師生態(tài)位的協(xié)同發(fā)展。第二,教師教學(xué)決策力具有發(fā)展方向的差異。在共同的職業(yè)活動(dòng)基礎(chǔ)上引導(dǎo)教師群體有序分化,謀求多樣化的發(fā)展方向,幫助教師打造自身的教學(xué)特色和優(yōu)勢(shì)。教師可以在課堂教學(xué)、課程開(kāi)發(fā)、班級(jí)管理、學(xué)生指導(dǎo)等不同專業(yè)領(lǐng)域,凸顯自身的專業(yè)特長(zhǎng)。
參考文獻(xiàn)
[1] 朱春全.生態(tài)位態(tài)勢(shì)理論與擴(kuò)充假說(shuō)[J].生態(tài)學(xué)報(bào),1997,17(3):324-332.
[2] HURLBERT S H. The Measurement of niche overlap and some relatives[J]. Ecology,1978,52(2):59-67.
[3] PETER G N.卓越領(lǐng)導(dǎo)力——十種經(jīng)典領(lǐng)導(dǎo)模式[M].王力行,譯,北京:中國(guó)輕工業(yè)出版社,2003:14.
[4] 袁世全.公共關(guān)系詞典[Z].上海:漢語(yǔ)大詞典出版社,2003:335.
[5] 鐘啟泉.基于核心素養(yǎng)的課程發(fā)展:挑戰(zhàn)與課題[J].全球教育展望,2016,45(1):3-25.
[6] WESTERMAN D A. Expert and novice teacher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1991,42(4):292-305.
[7] 王剛,趙松嶺,張鵬云,等.關(guān)于生態(tài)位定義的探討及生態(tài)位重疊計(jì)測(cè)公式改進(jìn)的研究[J].生態(tài)學(xué)報(bào),1984(2):119-127.
[8] 吳振利,饒從滿.關(guān)于教師合作問(wèn)題的理性思考[J].課程·教材·教法,2009,29(11):69-75.
[9] 王建軍.課程變革與教師專業(yè)發(fā)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103.
[10] 詹姆斯·馬奇.決策是如何產(chǎn)生的[M].王元歌,等,譯.北京:機(jī)械工業(yè)出版社,2013:23.
[11] 石中英.理性的教化與教學(xué)的理性化[J].高教探索,2002(4):7-10.
本文系山東省研究生教育質(zhì)量提升計(jì)劃重點(diǎn)培育項(xiàng)目“基于EBE的全日制教育碩士教學(xué)能力培養(yǎng)模式研究與實(shí)踐”(項(xiàng)目編號(hào):SDYJG19211)、臨沂大學(xué)2020年度課程思政教學(xué)改革研究項(xiàng)目“師范類專業(yè)課程思政建設(shè)標(biāo)準(zhǔn)與評(píng)價(jià)體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臨沂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教授)
責(zé)任編輯: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