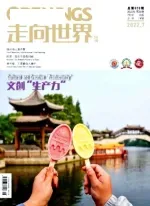一個“棚菜村”的華麗蛻變
王婧

發展訣竅在土地上
2002年,耿遵珠干了11年的糧食收購生意中斷了:全村620位選民、27名黨員,以接近全票的結果,把耿遵珠硬推到村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的位置。當時,他的個體經營一年收入六七萬元,村支書兼村委會主任全年工資才兩三千元。
“這么多人投票選咱,咱再推辭對不住他們!”耿遵珠是做通了親友的工作才挑起了這副擔子。他至今記得,剛上任那會兒,老支書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們耿店村是好村,別弄亂了,得把事干好了。”簡單的幾句話,對耿遵珠觸動很大。多年來在村里干活、經商的經驗,也使耿遵珠更加關注思路、眼光等問題。
到2021年5月,耿遵珠又添了新頭銜——耿店新村黨委書記,從之前一個村的書記,變成了11個村的書記。“新村”的成立,讓“耿店”的范圍更大了,同時,耿遵珠的擔子也更重了。對于村莊未來的發展,耿遵珠說,村里的富民產業是大棚,關鍵在于提高土地效益,今后發展的訣竅,還是在土地上。
曾經,像耿店這樣的自然村在魯西平原上比比皆是,無水可依,無山可傍,何況耿店村距茌平城區30多公里,在整個茌平區都屬于“偏遠村鎮”。“除了土地,幾乎沒有其他優勢資源。”耿遵珠說,這是平原地區最大的現實。“耿店沒有區位優勢,走工業的路子對耿店來說不現實,我們還是決定走農商并舉的路子。”耿遵珠上任伊始便敲定了發展方向。
堅定不移種棚菜
從20世紀90年代起,魯西平原上建起了很多蔬菜大棚,耿店和周圍村莊也嘗到了設施農業的甜頭。但到了2000年左右,情況變了,耿店村的棚菜也走到“十字路口”:種了5年的106個蕓豆棚因重茬出現大面積死秧,村里人戲謔“早晨拉晚上拽,一天賠進幾十塊”“孟姜女哭長城,耿店人哭大棚”。很多人覺得,在村里種大棚真不如外出打工。
“我就想讓大家看看,不是大棚產業不行了,而是我們沒有技術,不敢改茬,不敢跟進,造成耿店的產業越來越萎縮。你看人家壽光,一個大棚能掙好幾萬塊錢,這就是差距。”為了讓大家解放思想,耿遵珠帶著村民去壽光“取經”,一年去了8次。他還從壽光聘來了技術員,指導改茬工作,改種黃瓜、辣椒、西紅柿。
這一改茬,效益直接翻了一番。還是50米長的老棚,一年種菜的收益卻達到一萬五千多元。大棚產業對村民的吸引力立刻回來了。從2002年開始,耿店徹底邁上了產業振興的快車道。2003年耿店村建設蔬菜批發市場,解決農民賣菜難問題;2008年成立茌平縣綠冠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蔬菜成功打入超市;2010年又建設占地100畝、年育苗能力達3000萬株的高標準智能育苗基地、試種基地,結束了從壽光進苗的歷史。

再看如今的耿店,蔬菜大棚已經形成“一條龍”產業模式:育苗基地、合作社、蔬菜批發市場等配套設施和服務齊全,全鏈條式產業模式讓大家在村里就能賺到錢。
“棚二代”回村創業
2006年,耿遵珠通過引入卷簾機大棚,實現了滴灌水肥一體化。這時,新問題又來了,由于村里缺少年輕人,即使有了新技術,如何運用也讓村民們犯了難。這時,耿遵珠開始將目光轉向了外出打工的年輕人。
耿付建作為耿店村外出務工的年輕人之一,收到了耿書記的電話。“2010年之前,我在深圳打工,在外面一年能掙2萬多塊錢。那時候耿書記對我說,在村里種大棚一年能收入4萬塊錢,我開始還不太相信。”耿付建說,他回村后,一下子投資幾十萬元搞了5個大棚。村“兩委”也幫著他做好修路、架電、排水等工作,連大棚用地也是村里幫忙整合的。2020年,經過多年積累,經營11個大棚的他,年收入達到了40多萬元。
在耿遵珠的努力下,先后有100多名青年返鄉,700多個高標準蔬菜大棚拔地而起,這群人也成了名副其實的“棚二代”。現如今,從事大棚蔬菜種植的70后、80后、90后占到八九成,僅棚菜一項人均純收入就超過了4.5萬元。此時的耿遵珠并沒有閑下來,每天琢磨著,怎么把自己村的經驗,傳授給更多的人。
耿遵珠說:“在我們村旁邊建了一個聊城市鄉村實用人才培訓學院,也叫‘棚二代大學,通過看我們村20年的發展歷程,教育學員們怎么更好地發展并掌握技術,搞現代農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