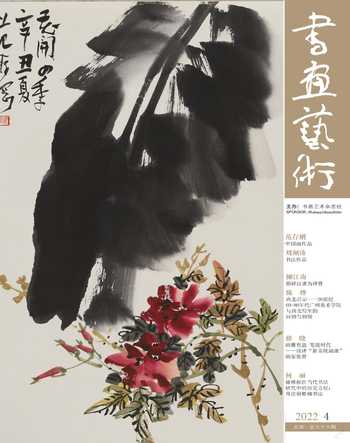金勒馬嘶芳草地 玉樓人醉杏花天
季燕
清代后期的揚州畫家王素,是一位藝術才能全面,既有傳統功力又善于吸收外來經驗的畫家。乾、嘉以后,西方繪畫之風廣泛傳播,國內的一些畫家拓寬了視野,開始在作品中探索光、形、色的表現手法,王素是這一時期將傳統繪畫與西洋繪畫結合得較好的一位。
王素,字小梅,小某,號竹里主人,晚號遜之。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卒于光緒三年(1877年),揚州甘泉人。《清畫家詩史》《墨林今話續編》《廣印人傳》等均有載:道光初年(1821年),他與魏小眠、王應祥齊名,被推為“揚州十小”之首,晚清海派六十家之一。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入揚州時,遷居邵伯、郭村,逾年重返揚州。約在清同治、光緒間寓南通曹家埠任家庭教師,教小姐畫仕女。
汪研山《揚州畫苑錄》記載,王素“幼師鮑君薺田,以其拙,而日夕臨摹新羅山人至再至三,凡人物花鳥以及走獸魚蟲,無不入妙。早年即有聲譽……當道光初年,若魏小眠、王古靈昆仲皆一時高手,先生掉臂其間,悉與并駕”。
王素的畫造型準確,栩栩如生。《揚州畫苑錄》又載:“有倩畫南北星君者像,苦無根據,乃躬詣蕃厘觀,圖其塑像為稿本。其虛心若此。”說明他的畫系經過嚴格的寫生而來。正是由于這種執著與認真,王素成為一名藝術才能較為全面的畫家,凡人物、花鳥、走獸、蟲魚,無不入妙。
王素兼能篆刻,效法漢印,但為畫名所掩。據《蕪城懷舊錄》記:王小某“畫宗新羅,為海內所重,常住觀音庵。當時士大夫皆非王畫吳書不足相配。若不得其一,即以為減色。”吳者,指道光、同治年間著名書畫篆刻家吳讓之。王小某與吳讓之書畫聲名并重。當時,達官貴人都以擁有吳讓之的字、王素的畫為榮,并以此作為身份的象征。
董玉書《蕪城懷舊錄》還記:“揚州畫師初推小某,小某以后又推若木,若木以后當推石湖。”石湖為王小某的再傳弟子。王素是晚清揚州畫壇的領軍人物,在結合傳統繪畫、吸納西畫技巧方面頗為成功,作畫手法多樣,既能小筆勾描,又能大筆揮寫。在生宣上畫仕女、人物,擅長一種小筆寫意,則是他的顯著特點。
南通博物苑收藏的《馬上郊游圖》《玉樓人醉圖》是極具抒情性和戲劇性的清代佳作,縱89厘米、橫20.8厘米,為紙本立軸。其創作靈感來源于明代長篇世情小說《金瓶梅》,王素采用全景式構圖,以“金勒、玉樓”詩意工筆繪制富豪權貴生活悠閑,男女之間傳情達意的情景。畫卷布局流暢和諧,格調清新高雅。
《馬上郊游圖》繪江南早春二月,疏柳遠山,淡冶如笑,綠茵溪流,桃杏爭芳,相映成趣。主騎馬仆隨后,觀賞沿途景致。男子身著圓領袍,頭戴黑帽,腰扎錦帶,白色玉扣,腳穿方靴。乘騎行進中,身軀微微右傾,左手握韁繩,右手持馬鞭,回首張望,神采奕奕。侍童手持團扇,緊隨其后。馬匹略帶裝飾,張口嘶鳴,軀干粗實,臀尻圓壯,四肢修長,馬蹄輕舉緩步,通過視覺似乎可感受到敲擊地面的“嘚嘚”聲,作品洋溢著生命之氣。全卷景致錯落,筆法細膩,設色妍麗。人馬用鐵線描,略帶轉折方碩筆觸,線條細勁有力。樹石細筆勾勒輪廓,輕重頓挫,樸拙勁朗,充滿變化。畫山水更是一絲不茍,平緩連綿的山巒映帶著無邊的江流,壯闊沉靜,柔美流暢。山巒、橋欄、人馬、林木用色墨、朱砂、石青等色彩渲染。上題七言絕句:“金勒馬嘶芳草地。”署款:“漢卿先生大人屬臨顧西某畫本。即以就正。王素。”鈐印“小梅”朱文。
《玉樓人醉圖》畫面一派春光,山清水秀,楊柳吐綠,桃杏盛放,主仆倆縱情于山水樓閣間,整幅畫浸透著一股陽光般的暖意。王素通過藝術手法將遠景、近景一同向中景聚攏,使倚闌而坐的仕女——孟玉樓備受矚目。她是《金瓶梅》中貫穿全書的人物,有著傳統與悖道共存的雙重特征和精明狠辣、溫柔圓滑相結合的多元性格特點。孟玉樓經歷了三次婚姻,第一次嫁給販布商人楊宗錫,可惜正當生意興隆時,丈夫死于販布途中。守寡一年多后,孟玉樓帶著豐厚的嫁妝做西門慶第三房妾。在西門慶病逝后,孟玉樓與知縣兒子李衙內相遇,二人一見鐘情,結為夫妻。就這樣孟玉樓從普通商販的妻子——五品提刑官的寵妾——官二代的妻子,一次比一次嫁得好,“在人欲與禮法的矛盾中,既滿足了人欲,又無傷于禮法”。“離經叛道”卻“圓滿安定”[1]。
孟玉樓在中國古典小說人物的畫廊中,具有“典型”意義[2]。王素對其描繪細致入微,在形象塑造上,采用面部的四分之三側描,黛眉杏眼,玉鼻挺直,櫻桃小嘴,淺然一笑,貌若芙蓉。窈窕身材,以圓潤勁健的線條勾勒,身著雞心領粉裙,右手拿著紈扇,左手搭在右臂上,淹然百媚。在王素的筆下,玉樓細膩、含蓄、復雜的內心情愫隨著彎曲靈動的線條呼之欲出,尤其是眉目間傳神達意的描繪,將其對榮華富貴的企慕展現得淋漓盡致,折射出晚清女性對自身解放的合理追求。陪伴在側的侍女裝束簡樸,眼眉低傾,嘴角含笑。畫卷中的每一段線條行云流水般自然,巧用景致烘托人物,園林的亭臺樓閣、欄桿臺基、花卉樹木不僅賦予畫作勃勃生機,還襯托出這個自尊自強又身懷巨財的玉樓,只有自由自在的天地才是她的容身之所。這種靜中有動的藝術效果,遵循了形貌刻畫的規律,讓人心醉于“杏花天”,是畫家對孟玉樓享受生活、追求幸福指向的認同。畫面中無論是人物還是景觀的描繪都帶有一種典雅的神韻。應景畫題:“玉樓人醉杏花天。”署款:“癸亥夏日寫于竹里舊館。小某王素。”鈐印“小某”朱文。
縱觀《馬上郊游圖》《玉樓人醉圖》,通俗化與文學性兼容,王素巧妙地將山水、人物、鞍馬、花木等畫科技藝融于一體。全卷凝然如思、含情不語,在盡顯古時畫作“細密精致而臻麗”風韻的同時,頌揚了孟玉樓憑借自己的智慧,主宰自身命運。這是畫家對女性精神的謳歌,亦是其內心情感的抒發。
人以畫傳,這是對美術家成就最公允的肯定。生活于清代后期的王素在我國繪畫發展的進程中是一位卓有成效的人物、山水、花鳥畫家,是清代“揚州畫派”中晚出的后起之秀。早在晚清、民國年間,王素的作品就編成多種畫冊,印成各種畫稿,廣為流傳。由于他章法嚴謹,造型準確,常作習畫者范本,他的藝術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很好繼承的。
(作者單位:南通博物苑)
注釋:
[1]黃霖.黃霖說金瓶梅[M].北京:中華書局,2005:74.
[2]孔繁華.金瓶梅的女性世界[M]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