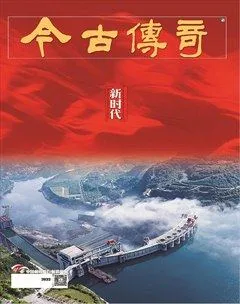一封來自345信箱9分箱的信
鄧淑文
親愛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
你們好!
我5月18日在武昌坐上去成都的火車,一路輾轉,終于在22日的日落時分回到了家。一打開門,就看到單位同事給我送來的加急電報,它正靜靜地躺在我家的門縫里,距離它發出的時間卻已經過去了整整3天。
看到電報,得知母親在我離家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撒手人寰,前塵往事如繁星點點,一并涌上心頭。我禁不住肝腸寸斷,淚如雨下。
母親出生于辛亥首義前夕,正是國家戰亂頻仍之時。她家境尚可,從小略讀詩文,通曉禮義。奈何時運不濟,命途多舛。20世紀30年代,盧溝槍聲,驚醒神州曉月;日寇鐵蹄,踏破鄂南山村。民無寧日,顛沛流離。日軍強行占領了汀泗古鎮,并逼迫父親做維持會長。父親不愿做日本人的走狗,偕同全家流亡。母親懷抱8個月的弟弟也一同踏上了逃亡之路。
逃亡路上大家忍饑挨餓、風餐露宿,本已苦不堪言,偏又遭土匪劫掠,財物被搶,父親和弟弟被害。父親死時年僅32歲,祖父、祖母年邁體弱,一家七口全系于母親一人。寒蟬凄切,流水嗚咽,我雖年幼,但此情此景仍記憶猶新。
疾風起而識勁草,嚴霜降而知紅梅。母親擦干淚水,結茅廬于廢墟,賣茶水于車站,開小店于街市,攝影像于鄉間。為生計之所迫,歷人世之磨難,飽受欺凌,含辛茹苦,艱難度日。
在如此艱苦且戰火不斷的年月里,特別是身在“女子無才便是德”意識仍然濃厚的舊中國,母親堅持送我們到學堂讀書。有人勸母親,家里困難,兩個女孩子就不用送去讀書了。母親不為所動,說女孩子也要讀書識禮,知道天下大事。
黃河九曲,滔滔東去;磨難千種,苦盡甜來。1949年,解放軍來到了汀泗,古鎮煥發新的生機。母親深感共產黨的恩情,經常教育我們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當年,我從武漢醫學院畢業后,本已分配到北京工作。我想著,終于可以一解幾年的相思之苦,好好和男友浩南團聚。到北京報到半月后,我才得知浩南被核工業部分配到甘肅去工作。當時,我國已經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作為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的畢業生,為了我國國防工業的強大,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不再遭受戰亂分離之苦,他應該擔負起這個光榮的使命。戰場在哪里,他就應該在哪里。我雖然不是科研技術人員,但那里也需要醫生。更何況我不想和他兩地分居,于公于私都應隨他一起去邊疆。來不及和家里請示,我立馬給單位寫了請愿書,堅決要求到邊遠地區去工作。就這樣,我和浩南在甘肅的戈壁灘上成了家。母親事后得知我去了那么遠的地方,而且是一個連通訊地址都保密的地方,雖然心里很掛念,但想著我們都是國家的人,是黨的人,黨讓我們到那里去,那就一定要支持,再難也要去。
去邊疆之前,在我的心目中,西部是那樣的神秘,那樣令人向往。明朗的天空,無邊的綠毯。羊兒悠閑地吃著草,駿馬在肆意地奔馳。草原上五顏六色的野花星星點點,生機勃勃。這種情境是多么美麗,如一首綺麗的小詩,又似一幅美麗的畫卷。
然而,我并不知道迷人的西部還有著猙獰的一面——大戈壁。那兒沒有山,沒有水,也沒有人煙,天和地的界限渾黃一體。住的是地窩子,睡的是自己用木板釘的床,吃的是窩窩頭,但大家生活都過得很充實,工作熱情極為飽滿,人人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兒。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一心只為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為中國核工業能夠自力更生而努力工作。
1968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小軍出生了。當時,母親已是近60歲的人了。得知我工作和家庭無法兼顧,她執意要到甘肅來幫我帶孩子。一個小腳老太太獨自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車,從汀泗到武昌到西安再到蘭州,又坐了三天汽車,才到我們所在的基地——戈壁深處的一個小綠洲。
一到我們的宿舍,母親來不及休息,就抱孩子、換尿布、煮米糊,忙個不停。從此,在這大漠深處,我們有了穩固的后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緊張繁忙的工作中。無論多晚回家,總有一盞明燈在我們心中閃爍,那就是母親帶來的溫情。
母親是一個非常和善且好學的人。我的同事們來自天南海北,說著南腔北調的普通話。而母親則是一個說著咸寧方言的老太太,但她很快就學會了普通話,和左鄰右舍毫無障礙地溝通、交流。她甚至還向其他家屬學會了做四川泡菜、山東煎餅。閑暇時,她會做棉襪、納鞋底。因為識字,有一些文化,家里訂的報刊雜志她期期都看,好的文章還讀給孩子們聽,督促他們學習。
就這樣,母親陪伴我們在戈壁灘上呆了整整10年。直到1978年,浩南奉調到四川,母親又隨同我們一起到了四川。這里仍然是人煙稀少,只有一座又一座連綿不絕的青山,但相比甘肅,無論是氣候環境還是居住條件已經好了很多。母親在四川只住了一年就決定回湖北,一是看我這里條件已經改善了很多,不需要再擔心;二是年事已高,思鄉情切;三是在外10多年,家里其他子女孫輩都沒有親自照顧,希望能夠回家再續親情。
母親返鄉這幾年,日常的生活起居等都有賴于大哥、大嫂和姐姐、姐夫照料,我雖有書信問候和生活資助,但山高水遠,無能為力,心中常懷愧疚之情。前年小軍高考,在我的要求下,他考上了華中理工大學。我希望他畢業以后能夠留在湖北,代我為母親盡孝。
今年年初,我從大哥的來信中得知母親病重,就計劃著今年暑假帶孩子們回咸寧一趟,到時候如果浩南工作不忙,也一起回去。但沒有想到母親病情變化太快,浩南身為項目技術負責人,工作丟不下。我請了15天的假,一個人趕到了咸寧。
母親看到遠方的女兒回家了,強打起精神,用干瘦的雙手緊握住我的手,一邊喘一邊說:“你回來了,聽說浩南前段時間體檢查出肝不好,要注意啊!”我病中的母親啊,哪怕是病得起不了床,心中牽掛著的仍然是兒女。
15天的假,去掉路途時間,只有短短的5天。這5天,我日夜侍奉在母親床前,眼看著母親的生命之火越來越弱,我心如刀絞。但我的假期已滿,縱有萬分不舍,也到了不得不分離的時候。
18日早上,我坐在母親床頭,久久不愿離去。因為疾病的折磨,母親已沒有力氣再多說一句話。但她仍然努力向我微笑著,用手示意我趕緊走,不要誤了火車,就像以往無數次我離家趕火車的時候一樣。但這一次,母親再也無法送我到車站,只有女兒帶著無限的思念和哀傷踏上漫長的路程。
母親已逝,但親情仍在。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母親一生坎坷,歷經磨難。但她始終樂觀、堅韌,恪守古訓,奉養公婆,養育兒女,以柔弱之軀堅強地面對家庭變故,以一己之力撐起了風雨飄搖的家庭。子女孫輩都成了新中國的建設者,她的優良品質代代相傳,融入到了我們的家風中。
路途阻隔,加之天氣炎熱,電話得知母親已葬,隨信附上現金500元,以補償母親喪儀所需。有勞哥哥、嫂子、姐姐和姐夫了。明年清明我們全家會回湖北為母親掃墓。到時再見,一敘親情。
妹新惠及浩南敬上
198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