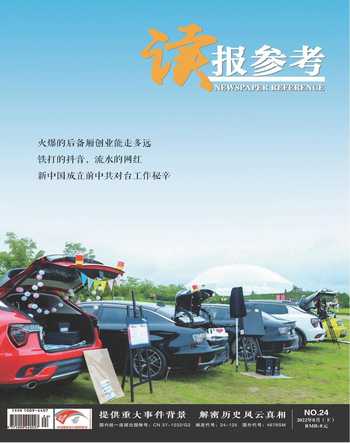半個世紀的抗癌馬拉松
從1970年代開始,云南宣威的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居全國前列,直到現在,宣威依然是肺癌高發區。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團隊奔赴到云南省曲靖市下屬的這個縣級市里,尋找肺癌高發的病因。截至今天,謎底仍沒有被完全揭開。
一
肺癌在劉斌的家庭繞了一圈:2002年他母親查出肺癌晚期后,熬了半年就去世了;前幾年,他的父親、大姐,先后查出肺癌早期,及時手術后,如今,他們都健康地活著。“也許在外地人看來,肺癌是不得了的病,但在我們這里,它太常見,太稀松平常了。”劉斌說。母親的病逝促使劉斌選擇當一名胸外科醫生,盡管在當時,愿意做胸外科醫生的極少,因為在當地,這是個“看不到生命曙光”的科室,得了這個病,“很快就沒命了”。
這名1976年出生于曲靖的胸外科醫生見過許多罹患肺癌的家庭,“前不久,我們醫院一個護士,作了CT檢查懷疑是肺癌,才31歲”。這些年,他見過年紀最小的肺癌患者,只有18歲左右。有個21歲的女大學生,剛剛大學畢業,檢查出早期肺癌。他在臨床上接診過一些晚期病例,窮盡了他能應用的治療方法,也留不住患者的生命。
在宣威,肺癌是困擾著許多人的難題。1970年代初,衛生部腫瘤防治辦公室公布調查結果,1973-1975年間,曲靖市的宣威縣是肺癌高發地,其中,女性肺癌死亡率居全國之首。吊詭的是,吸煙、職業暴露、空氣污染、電離輻射等這些公認的致肺癌因素,似乎都不是宣威肺癌發病率高的主要原因。劉斌的母親不吸煙,也不是宣威人,沒有在煤礦上工作過;他的父親和大姐,都是公務員,幾乎從沒接觸過肺癌的致病因素。
2017年,劉斌調職到曲靖市中醫院,成為這家三甲醫院新成立的胸外科的主任。“別說在曲靖了,在醫院內部都沒有名氣”,他回憶,科室剛剛成立時,醫護人員的能力不足,患者也少,大多曲靖的肺癌患者不信任本地醫院,更愿意去昆明的云南省腫瘤醫院看病。正當他苦惱于如何發展這個新科室時,一個同行提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的胸外科主任趙曉菁在為相對貧窮的地區作肺癌早篩早診的項目。曲靖市中醫院幾乎派了一個代表團去上海找趙曉菁。
二
上海仁濟醫院的趙曉菁此前從沒去過曲靖,也沒接診過來自曲靖的患者,但他知道,宣威是世界肺癌最高發的地方之一,“國內胸外科的醫生,都知道宣威”。坐在仁濟醫院的餐廳里,聽著曲靖醫生講那些家庭的故事,他有些感動,他能從對方的眼神里,讀到“想做點事的決心”。
他一直在為這個項目尋找合適的地點。從2013年到2018年,趙曉菁逐漸摸索到,要把項目落地,需要什么條件:要找到一個肺癌高發的地區;相對貧窮的群體;當地醫護有迫切性、積極性,想降低肺癌死亡率。而曲靖市中醫院似乎正是合適的合作對象。
他們共同的敵人肺癌是一個摸不透的、難纏的對手。目前,肺癌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疾病。趙曉菁也一直在和這個對手纏斗。 2016年,上海女性的肺癌發病率超過了乳腺癌,成為女性發病最高的惡性腫瘤疾病,且至今位列第一,“說不清為什么”。
他很清楚,降低死亡率的一個重要的臨床手段是,使用低劑量螺旋CT篩查患者,找到早期肺癌患者。他嘗試過許多方法,把早篩早診推廣出去。浙江一個胸外科大夫找過趙曉菁,說醫院的胸外科沒發展起來,沒患者。趙曉菁出主意:先給醫院50歲以上的職工作CT體檢,找到肺癌患者,再給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作篩查,讓官員也開始重視肺癌早篩早診,慢慢地,把理念推廣到全市。
2018年12月29日,趙曉菁第一次抵達曲靖,給18個早期肺癌患者免費作手術。這18個人,是劉斌花了3個多月,組織醫護人員去村子里動員498人接受免費篩查,慢慢找到的。趙曉菁終于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劉斌執行力強,熟悉當地的醫療系統和政府部門,負責對接政府官員和基層衛生工作者;而趙曉菁外向健談,有專業背景,讓村民們產生信任感,“上海的大專家真的來了”。
劉斌下決心要在曲靖推廣早篩早診。他的父親和大姐,得益于早篩早手術,如今安穩地活著。劉斌說,在這個不愁吃穿的年代,他這一生能做成這件事就可以了。
三
宣威從來不缺解謎的人,至少最近50年是這樣。1979年,100多個多學科的專家扎進宣威,想找到答案——這個山清水秀的縣城,為什么是全國肺癌發病率最高的地區?他們和當地醫療單位合作,成立宣威肺癌病因學研究項目組。項目組的負責人叫何興舟,時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環境衛生與衛生工作研究所環境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此后,他花了27年的時間在宣威解謎,想要“保護百余萬農民”。
這個謎題太難了。何興舟在回憶文章里寫到,按照以往經驗,肺癌一般是城市高發、吸煙人群高發、男性高發。但在宣威,男女肺癌患者數量持平,一些地方甚至女多男少,而且有明顯的家庭聚集性、鄉鎮聚集性。他最終找到的謎底,是當地每家每戶都有的“火塘”這種在室內燒煤的開放式爐灶,是全家人的生活活動中心,一家人聚在火塘旁,借光、取暖、生火做飯。火塘太常見了,以致于村民忽略了,室內空氣無法流通,靠近火塘做家務的家庭婦女,就成了最容易吸入大量煙塵的家庭成員。
這個發現為宣威肺癌的后續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何興舟說,參與解謎的,既包括了9個單位169個人,也包括了當地“成千衛生工作者,幾代人工作所得”。國際室內空氣質量科學技術學會2005年向何興舟頒發了“終身成就獎”,這是中國人首次在該領域獲得的獎勵。
改爐改灶多年,如今宣威依然是全球肺癌高發的地區之一,當地有個家庭,6個兄弟姐妹,有4人罹患肺癌。可見,“火塘”并不是宣威肺癌高發的唯一一個謎底。有研究者提出猜想,一些家庭的基因出了問題,才會出現家庭聚集性發病。劉斌嘗試用最本土的話打比方,“咱們這里的抑癌基因睡大覺了,跑到月亮上去都沒用”。
他接受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至少在他這一代,這種無法逃脫肺癌的故事還會延續,“總不能讓人都搬到北上廣”。但他仍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延遲肺癌發生:母親逝世后,他再也不吃以往最愛吃的鹵豆腐了,雖然吃它大概率不會引起肺癌,但他還是戒了;他把家里原先的煤都送人了,完全改用電器;煙早就不抽了;酒,直到這幾年作肺癌早篩早診之后應酬變多,他才喝一點。
在后所鎮一個村子的衛生室里,他和同事李繼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王蘭在桌子上攤開曲靖的地圖,地圖上有許多紅點,那是李繼華干了大半輩子收集的高發地區。他們計劃,合理地規劃早篩項目的篩查區域,不再蜻蜓點水地跑許多村子動員,而是聚焦在一個高發村子,作所有人群的篩查。趙曉菁分析,早篩早診項目已經落地4年了,包攬了篩查、治療、手術一條龍;相比起只作免費篩查不作治療的其他肺癌基金,為患者提供免費治療的團隊更容易取得村民信任,降低流調難度。
王蘭離開曲靖后,利用專業知識,在原有的健康調查表上,新增了“居住環境”的一欄,調查村民住房的建造年代、建筑材料,具體到堂屋、臥室、廚房有幾扇窗戶,開窗后有沒有穿堂風。她還發現,在宣威等地,除了住房通風問題外,工礦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幾何距離與風向和水文交互作用,也影響了肺癌發病率。
這場耗時近50年的抗癌馬拉松,在一代代人反復努力下已有些成果。調查發現,宣威肺癌死亡率正在逐漸變緩:1970年代到90年代是快速期,標化死亡率(按標準人口年齡構成計算的死亡率)上升了179.6%;1990年到2000年是慢速期,上升了35.3%;而2000年至今,得益于肺癌治療方法的更新,已經步入了平穩期。
(摘自《中國青年報》魏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