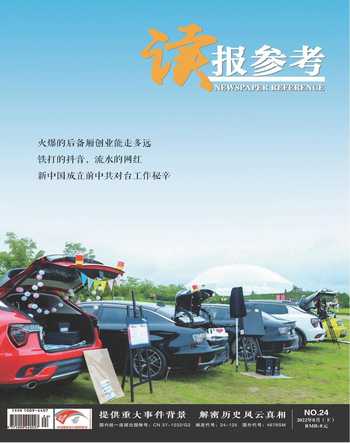當文科生遇上人工智能
有這樣一群人,純文科背景的他們行至半路才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他們中,有人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認知科學博士學位;也有人艱難適應,差點放棄……每個人的轉型之路都不平坦,但他們的經歷也證明了,人生不是非要在既定的賽道上奔跑。
從中文系本科生到認知科學博士
10年前,當一位中文系教授向黃萱菁推薦本系一名學生,說他立志考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時,這位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教授以為自己聽錯了。
雖然黃萱菁研究的領域自然語言處理與中文不無關系,但一個純文科背景的學生想要轉到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深造并非易事,況且,10年前人工智能在國內尚且算不上一個熱門學科。究竟是什么讓他這樣選擇?黃萱菁很想知道答案。
幾天后,這個名叫錢鵬的學生坐進了黃萱菁的辦公室。從傳統意義上看,他是個典型的“學霸”,從小成績優異,高中選讀理科,卻始終對文史哲興趣濃厚。高三時,他報名參加了復旦大學“博雅杯”人文學科體驗營。錢鵬從全國各地的考生中脫穎而出,順利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就讀。
錢鵬告訴黃萱菁,大一、大二的通識教育讓他有機會涉獵本專業以外的諸多學科,啟發了他用跨學科的新視角來看待傳統問題,尤其是通過計算的方法了解語言的本質、信息的處理,激發了他對人工智能領域的興趣。這次談話讓黃萱菁印象深刻,她贊賞錢鵬的勇氣,也立刻感受到“這是一個非常有靈氣的學生”。但是,在她的實驗室里,跨專業來的學生幾乎都是理工科背景,純文科背景的考生“前無古人”。黃萱菁不敢貿然應允,而是默默開始了對錢鵬的考察。這一考察,就是兩年。
大三時,錢鵬赴香港中文大學交換學習,接觸到了神經語言學。“我就像走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錢鵬轉考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的決心更加堅定,“未來,學科交叉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錢鵬回到復旦后,黃萱菁開始嘗試給他布置一些實驗室的工作,從最基礎 的標注到更加進階的內容,錢鵬的完成度總會超出她的預期。他的勤奮也讓人印象深刻,甚至在錢鵬畢業多年后,黃萱菁和同事交談時提起他,隔壁辦公室的老師還記得,“他就是你們實驗室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10點走的那個學生”……
2015年,本科畢業的錢鵬通過考核,順利進入黃萱菁的自然語言處理實驗室攻讀碩士研究生。2017年,他又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今年,錢鵬終于取得認知科學博士學位,攀到了這一領域的金字塔頂端。
高等教育中的專業“鄙視鏈”由來已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主修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學生被稱為“文藝呆”,主修工程學或計算機科學的是“技術宅”,講的也是一種以專業來區分人的“標簽”。“但文科和理科之間真的是對立的嗎?我的個人感受是,社會的專門化凸顯了文理之間的差異,卻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它們的共性。”錢鵬說。
真正的挑戰“上岸”之后才開始
相比于許多文轉理的同學,錢鵬無疑是幸運的。
當錢鵬攻讀博士學位時,他的同系學妹、剛剛結束大二上學期課程的季雨秋也對自己的未來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跨專業深造。
當年,季雨秋因為全國中學生作文競賽得獎,通過自主招生進了復旦。可她進了大學才發現,“原來中文系并不培養作家,畢業后真正靠寫作謀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她在學校寫新聞稿,去雜志社實習,為學生組織作自媒體宣傳……然而,每嘗試一次,她就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雖然擅長寫作,卻并不習慣按照范式要求寫作,更不喜歡根據別人的意見修改自己的作品,這讓她對寫作的興趣和熱情喪失殆盡。反倒是大一學生必修的編程課讓她興趣盎然——把自己的想法按照一定的邏輯,用代碼串連起來去實現,她喜歡這樣有快速反饋的學習和工作。
她給自己規劃了三條路徑——保研、考研、出國留學。其中,保研是最早進行的。要怎樣達到跨專業保研的目標呢?首先要保證中文系課程的成績名列前茅,才能拿到保研資格,這在高手云集的復旦中文系并不容易。更困難的是,她要在決定跨專業深造和保研考試到來之間的一年里,補上計算機專業學生三年要學的課程。光是這兩點,就足以擊退大部分萌生過跨專業深造想法的人了。
在選修相關課程和查閱資料時,季雨秋又發現,大多數課程設計和問題答疑對跨專業學習的學生并不友好,就像被“知識詛咒”了一樣。因為這些課程往往默認接受知識的人有非常扎實的專業基礎,并不適合像她這樣的“小白”。她就去找適合初學者的學習資源,從零開始,反復啃、反復練,確保自己能夠吃準吃透。幾乎每一個從純文科轉考理工科的人都經歷過這樣痛苦的過程。最終,季雨秋被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計算與信息檢索研究中心錄取,拿到了文轉理的入場券。
歷經千難萬險,付出數倍努力后,鳳毛麟角的跨專業學子終于“上岸”。可當這些文科背景的學生真正成為一名理工科專業的研究生時,或許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剛進大學時,季雨秋就很快認清并接受了“自己在復旦只是一個凡人”的定位,對她來講幾乎不存在心理落差。可進入哈工大社會計算與信息檢索研究中心這樣國內一流的實驗室繼續深造,還來不及享受升學的快樂,迎面而來的壓力就讓她喘不過氣來。
難度進階的課程讓她經常擔心自己會有掛科的風險,有段時間她甚至會焦慮到失眠。在這樣高手如云的工科強校,她覺得自己最多只能算是“地板水平”。剛進項目組時,她甚至還需要師弟的幫助。
一次,季雨秋苦思冥想、廢寢忘食,終于作出了一個模型的雛形,她非常興奮,甚至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可師弟卻開玩笑地告訴她:“師姐,你就像一個專業運動員,其實才剛剛學會撿球而已。”這句話就像往她頭上狠狠澆下的一盆涼水,“不,不僅是涼,還有冰塊”。往后的日子里,季雨秋總會想起這個“撿球”的比喻。“現在想來,其實是一種身份上的復雜性讓我沒有安全感,放大了實力上的差距,倒逼我必須更加努力取得成果,才能獲得認同。”
那時正逢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暴發,季雨秋常常改代碼改到深夜,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睡醒了就繼續修改代碼、參加評測,幾乎每天24小時連軸轉。她知道自己必須作出一些成績,才能在即將到來的秋招中謀得一份心儀的工作。
然而從夏天開始準備的秋招卻讓她屢屢受挫,她險些要放棄。事情在2021年4月才出現轉機,某大型互聯網公司需要補錄一批軟件開發崗位的應屆生,季雨秋背水一戰,終于實現了多年來的理想,成為了一名算法工程師。
“你要做的只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選擇,相信自己的潛力。這條路即使孤單,但只要是自己感興趣的,就要一直堅持下去。”季雨秋說,“無論什么時候改變其實都不晚,一次改變并不能真正左右你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要畏懼作出選擇和努力。”
(摘自《解放日報》雷冊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