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見證大英帝國跌落神壇
李珂

福爾摩斯的締造者柯南·道爾
2019年1月,我在倫敦。當我去貝克街221b號探訪福爾摩斯紀念館時,看到外面排起了長長的隊伍,而隔壁的披頭士紀念商店卻門可羅雀—唱片、吉他和滿墻的舊照片,被從商店櫥窗過濾進來的陽光一照,處處昏黃,更顯凄涼。
披頭士樂隊在上世紀紅極一時,如今卻熱度不復當年。相反,在21世紀,大偵探仍然魅力不減。
創造福爾摩斯的人
福爾摩斯紀念館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市民住宅,又高又窄。在狹小的樓梯上,成群結隊的游客幾乎無法轉圜。因此,博物館規定,每次只允許20人參觀。
在排隊時,我觀察到大多數參觀者是女性。我用英語與排在前面的女生聊了幾句。她來自日本,這次她們一行有四人,因為喜愛推理小說,特地前來“朝圣”。
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成功,在于他沒有循規蹈矩地遵循警方的規則。但福爾摩斯故事不僅是一項智力游戲,更是一種歷史的回溯。在19世紀晚期,老牌西方文明發展到頂峰,人類第一次了解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每一處陌生的國家和種族。
創造福爾摩斯故事的柯南·道爾,其成名作《四簽名》是最完美體現維多利亞時期世情百態的一部小說。從印度殖民地到國際大都市倫敦,從倫敦西區寧靜的貝克街到倫敦東區港口的貧民窟,再到安達曼群島的沼澤地,有多少人是因為福爾摩斯而喜歡上維多利亞時代的?

倫敦福爾摩斯紀念館
閱讀阿瑟·柯南·道爾的傳記,就像是進入一次探險。多種多樣的經歷,不同項目的體育成績,從足球到高爾夫,從滑雪到賽車,從自行車到板球—當然,小說家首先是個英國人,他參與各種為了榮耀的戰斗,并且熱衷于出席社會活動。
他在1897年支持一個救助印度饑荒的基金會成立,1916年支持英國隊加入奧運會,1909年支持離婚改革運動。他尤其對1890年結核桿菌的發現充滿熱情∶“我應該去柏林,去看論證演示。但到底是為了什么確切的原因,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可能,他不想要錯過任何一個與醫學同行比武的機會。他為了這些理由寫作、寫信、寫論戰小冊子、寫傳單。
除了《白衣軍團》《奈杰爾爵士》等歷史小說,我們還看到他色彩豐富的自傳敘事,有時候以書信的形式寫成,有時候以具有時代氣息的短篇小說呈現。在《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中,他嘗試了各種各樣的表達方式(歷史記敘、描述、會議、報紙節選)。
抨擊比利時國王
在現實里,柯南·道爾也是“大偵探”。“在任何一次將福爾摩斯的探案方法具體施行出來的嘗試中,我從來沒失敗過。”他這樣保證。
因為柯南·道爾的介入,兩個冤案被部分地糾正。1903年被判死刑的喬治·艾達吉,得以洗刷清白,于1906年得到釋放。1909年,奧斯卡·斯萊特因為一起他沒有犯下的謀殺罪含冤被捕。柯南道爾以福爾摩斯之名發表了《奧斯卡·斯萊特事件》。不過直到1927年,主人公才得到釋放。
1909年,柯南·道爾向一個權勢更煊赫的對手發起挑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在殖民地剛果橫征暴斂,犯下累累罪行。1909年,柯南·道爾發表了《剛果罪行》,稱會與之斗爭到底。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及其后繼者們對剛果犯下的罪行,是人類史上從未見到過的殘忍罪行。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系統的剝奪加屠殺。所有這些都是出于卑鄙的動機,在慈善事業的卑鄙外表下進行。這一可鄙的理由和虛偽的好意,讓罪行的恐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比利時國王對剛果的入侵,令柯南·道爾難以接受,因為這是一個國王對榮耀的背叛。利奧波德二世打著反對奴隸貿易的旗號,入侵并征服了剛果,但在比利時人的橡膠產業里,無數黑人勞工淪為了實質性的勞務奴隸。
雖然柯南·道爾是一個開明的紳士,但看不見的騎士才是他的精神祖先。他積極地介入政治。猛烈地攻擊不公正,為被定罪的無辜者辯護。騎士精神是柯南·道爾魅力長存的核心。
福爾摩斯故事不僅是一項智力游戲,更是一種歷史的回溯。
大英帝國跌落神壇
在柯南·道爾的醫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活動是參與了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年,又稱英布戰爭)。這次經歷為他帶來了爵士的殊榮,也使他對于這場戰爭的反思姍姍來遲。
在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的1900年3月至6月,柯南·道爾在南非的野戰醫院擔任志愿醫師。那年晚些時候,他寫了一本關于戰爭的書《偉大的布爾戰爭》,以及一部名為《南非戰爭:它的起因和行為》的短篇作品,為英國發動的這場戰爭辯護,并稱其作用是合理的。《偉大的布爾戰爭》于1900年首次出版,到1902年戰爭結束時,已出版了16個版本。
與之相對的,是德蘭士瓦共和國領導人史末茲的小冊子《百年不公》—把1806年以來的英國在南部非洲的統治描繪成血腥的暴政。它指責,英國人對布爾人步步緊逼,是礦業資本家和英國政府之間的陰謀,目的是攫取德蘭士瓦的金礦。“盡管我們微不足道,但如果命中注定我們應該是所有民族中第一個開始反對資本主義新世界暴政的人,那么我們準備這樣做,即使這種暴政被金戈主義(英帝國主義)的力量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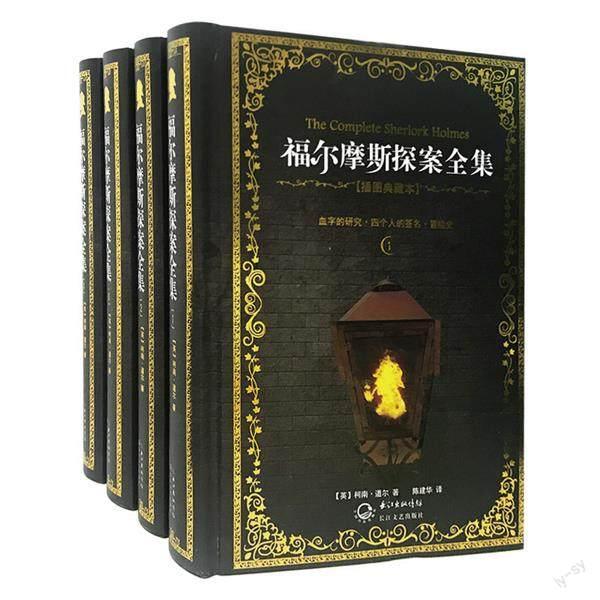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
英國人付出了巨大代價,投入35萬兵力,耗費2.17億英鎊,與布爾人打了將近三年的消耗戰。英國為了鎮壓布爾游擊隊,不惜采取焦土政策,焚毀約3萬個布爾農場,將數十萬婦孺投入現代意義上的“集中營”。這場仗,讓大英帝國跌落神壇。
即使在戰后,布爾人也未屈服,他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種族主義。正如他們的自稱“阿非利卡人”那樣,他們相信自身是一群獨一無二的人,由上帝之手創造,為了在南非完成一項特殊使命而生;他們相信,英國和黑人都想消滅他們,只是由于上帝的干預才未能得逞。這成為日后在南非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濫觴。
在柯南·道爾的小說《皮膚變白的軍人》里,從南非歸來的軍人,誤以為自己感染了麻風病,被迫隔離。殘酷的布爾戰爭,就像是一種精神夢魘,縈繞在曾參戰的柯南·道爾心頭。
騎士從未跳下他的戰馬,然而,時代已經變得不同。對于他筆下的福爾摩斯來說,一切都是可以憑借智慧掌握的,可以用觀察、推理來解決;現實卻是不同的,也許每個人都沒有撒謊,都在說著真相,也都在為自己所堅持的“真理”而戰。
責任編輯謝奕秋 xyq@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