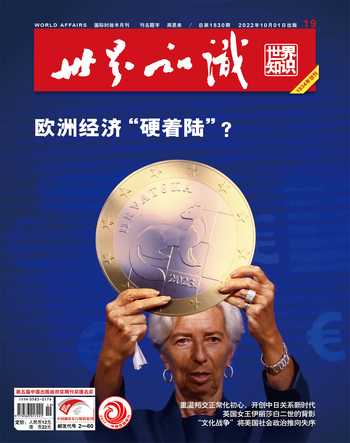“文化戰爭”將美國社會政治推向失序
林玲

2022年7月9日,上千名示威者在白宮外舉行集會,抗議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抗議者將集會標識系在白宮柵欄門上。
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對“多布斯訴杰克遜女性健康組織案”的裁決中,以6∶3的表決結果推翻了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當年羅案判決的核心內容是:墮胎權為憲法授予,各州不得擅自頒布法令限制女性墮胎權。新的裁決意味著美最高法院將墮胎立法權交還各州。英國廣播公司(BBC)評稱,最高法院向美國業已白熱化的“文化戰爭”投下一枚“憲法炸彈”。
“文化戰爭”的興起
“文化戰爭”概念最早由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家詹姆斯·亨特在其1991年出版的《文化戰爭:界定美國的一場斗爭》一書中提出。亨特認為,“文化戰爭”根植于“不同理解體系的政治與文化仇恨”,對抗雙方都力圖爭奪主導權。“文化戰爭論”將美國社會分為“正統派”和“進步派”兩大對立陣營,前者信奉傳統的宗教與道德價值觀,反對墮胎及同性婚姻,倡導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后者強調多元化和個人選擇權,支持墮胎、同性戀權益與同性婚姻。根據“文化戰爭論”,當代美國社會在文化和宗教道德價值觀上已分化成兩個陣營,斗爭愈演愈烈。
“文化戰爭”概念一經提出,即被保守派政客大加利用,成為政治動員中的一面旗幟。在1992年美國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保守派人士布欽南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使用“文化戰爭”概念指涉墮胎權、同性婚姻、胚胎干細胞研究、公立學校宗教教育、槍支管控、大麻合法化等社會議題,宣稱“一場為美國靈魂而戰的宗教戰爭正在這個國家展開”。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第二波女權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反正統文化運動”的展開,圍繞墮胎權、同性戀權益等問題的“文化戰爭”在美國興起,并在選舉政治驅動下迅速上升為政治議題。共和黨從20世紀初支持墮胎權到70年代反墮胎立場的根本性轉變,直接驅動力即來自于政黨與右翼宗教力量的“聯姻”。1973年羅伊案的判決激起宗教右翼強烈反彈,聲勢浩大的“生命權運動”應運而生,在基督教福音派等宗教右翼最集中的南部地區(“圣經地帶”)尤甚。共和黨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轉變在其南部政治力量重組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后逐步確立了反對同性婚姻、擁有槍支權等“道德傳統主義”立場,與民主黨的“文化自由主義”標簽針鋒相對。
“新文化戰爭”
進入21世紀,美國社會分裂與政治極化現象日趨嚴重,“戰火”從墮胎權、同性婚姻等議題蔓延至種族、移民與身份政治問題,超越了宗教與道德價值觀的對立,逐步演化為國家認同層面的沖突,保守派心目中的“美國故事”被調包了。保守派也從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中感受到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面臨的“危機”。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白人人口占比持續下降,現已低于60%,同時美國傳統制造業的“空心化”使許多中下層白人陷入經濟困境,2008年金融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白人身份焦慮的底色。2016年大選,以反少數族裔平權、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義為訴求的“白人身份政治”浮出水面,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被賦予“讓美國重新白起來”的潛臺詞,白人民族主義沉渣泛起。
種族矛盾引發的文化認同沖突成為“文化戰爭”轉向的重要標識。2020年5月白人警察跪殺黑人弗洛伊德的事件引發席卷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抗議浪潮不僅延續了2014年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基調,更呈現出超越反種族主義抗爭的發展態勢。在新一波運動的“倒像”潮中,不僅是作為蓄奴制象征的南部邦聯塑像和標志物成為矛頭所指,其他涉及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人物的雕像也被涂鴉或推倒——包括哥倫布,以及喬治·華盛頓、托馬斯·杰弗遜等“建國之父”。旨在重新定義美國歷史的“1619項目”成為運動的標志性項目,該項目由《紐約時報雜志》黑人記者漢娜·瓊斯發起,核心理念為:美國歷史的開端應以第一批黑奴抵達美國的1619年來定義,而非以《獨立宣言》發表的1776年為開端。該項目匯編了以奴隸制與種族主義對當代美國社會影響為主題的系列文章,以及由當代黑人作者創作的基于歷史事件的文學作品,并制作了學校歷史課程材料,試圖顛覆白人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構建以多元文化為基石的國家認同。
左翼“文化革命”引發右翼激烈反彈。每當美國社會出現大規模黑白種族沖突,移除邦聯紀念物的呼聲就會應聲而起。然而,對于白人民族主義者和許多南部社會保守派人士而言,南部邦聯塑像承載著其集體記憶中的內戰前“舊南部”的文化情結,因而“倒像”運動在其眼中無異于意圖顛覆南部的歷史文化根基。2017年8月,數千名白人民族主義者集結于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舉行“團結右翼”集會,高呼“把美國奪回來”,力圖抵制市政府擬拆除南部邦聯統帥羅伯特·李將軍塑像的決定,與在場支持拆除塑像的人士發生激烈沖突,白人極端分子制造了震驚全美的暴力事件。在2020年的“獨立日”慶典中,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南達科他州的總統山下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說,稱推倒塑像的行為“對美國政治體系的基礎產生了威脅”,并宣布將建立“美國英雄國家花園”。
“1619項目”自誕生起就爭議不斷,遭到保守陣營的強烈抵制,右翼社交媒體將其支持者定義為“仇國左派”。愛荷華、南達科塔、密蘇里、阿肯色、密西西比、愛達荷州、俄克拉荷馬州等共和黨控制州的議會相繼明令禁止使用包括“1619項目課程”在內的與種族主義相關課程資源。特朗普于2020年11月簽署行政令,成立“1776委員會”,以在美國學校中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并通過督導聯邦政府對各州教學計劃的控制,實現“去種族主義教育”。次年1月,拜登出任總統后不久便撤銷了該委員會,隨后全國性右翼團體創建“1776項目”,致力于廢除公立學校課程中任何涉及“1619項目”和“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內容。
愈演愈烈的校園“文化戰爭”
“批判性種族理論”原本只是個鮮為人知的學術理論,它試圖通過承認美國體制中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來尋求解決社會不公,但隨著“1619項目”的推廣,不少州的公立學校在美國歷史和公民課程中加入“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內容,一些大學、私立學校、大公司也相繼開設相關課程或培訓項目,該理論隨之發展成為思想運動,圍繞“批判性種族理論”教學的紛爭演化成“文化戰爭”的新戰場。在保守派反對者看來,該理論意圖將有色人種與白人對立起來,宣揚仇恨與分裂,構成“對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嚴重威脅”,甚至給其貼上“新種族主義”標簽。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公布了總額530萬美元的歷史與公民教育撥款優先標準,明確要求教育部在全國歷史和公民教育課堂上推廣“1619項目”及“批判性種族理論”。這一新政策很快激發了右翼的抵制,2021年5月至今美國已有七個州出臺禁止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法案或政策,另有21個州正在商討類似法案。被視為共和黨政治新星、2024大選總統候選人熱門人選的佛羅里達州長德桑蒂斯于2021年12月簽署了“停止覺醒”法案,允許州內家長起訴將“批判性種族理論”納入中小學基礎課程的學區,這意味著教師如果被舉報,將面臨被辭退甚至吊銷教師資格證的風險。
共和黨正把抵制“批判性種族理論”作為重要的政治動員手段。以捍衛“家長教育權”為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教學進行反擊,正是共和黨人楊金贏得2021年11月弗吉尼亞州長選舉的關鍵戰略。此前,弗州勞登郡的公立學校家長組織了名為“為學校而戰”的請愿行動,要求罷免校董會。勞登郡的教育問題隨之成為新一屆弗州州長競選的中心議題,楊金堅定支持家長訴求,承諾在學校禁止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自此,抵制“批判性種族理論”教學成為共和黨人開展“右翼文化戰爭”的重要“試金石”。
與此同時,一場涵蓋種族問題、性少數群體身份認同與多元文化價值觀問題的“禁書運動”也在美國校園掀起。在多州的學校校董會上,都有憤怒家長要求學校禁止包涵種族主義歷史、多元文化主義、性別與性取向等內容的圖書。據美國筆會2022年4月公布的一項調查,全美學區從2021年7月到今年3月共下達了逾1500項書籍禁令,其中得克薩斯州發布了713次,其次是賓夕法尼亞和佛羅里達州。至少40%的圖書禁令與州立法相關聯,例如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在2022年3月簽署法案,禁止在幼兒園至小學三年級課堂談論性取向與性別認同問題。以“為自由而戰的母親”“捍衛教育家長聯盟”“教育不左轉”等為代表的保守派倡議團體也對這股校園“禁書潮”起了推動作用。右翼政治力量通過大力渲染左翼“文化革命”和所謂“覺醒教化”對美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和民族認同的威脅,激發保守派民眾恐慌,進而在文化反擊中構建保守派聯盟。
總之,相對于20世紀70至90年代基于宗教與道德政治的“文化戰爭”,如今“文化戰爭”的關鍵問題已被種族問題所取代。隨著白人身份政治將各種少數族群都納入反對陣營,白人民族主義與基督教民族主義開始在反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聯手。在此背景下,墮胎權與性少數群體權益之爭超越道德政治內涵,儼然上升到“我們是誰”“誰代表美國”的高度,釀成國家認同危機。而美國兩黨政治精英在選舉政治動員中,通過將經濟議題種族化、政治化,鞏固各自的選民基礎,族群認同沖突不可避免地升級為“新文化戰爭”,推動美國社會與政治加速走向失序。